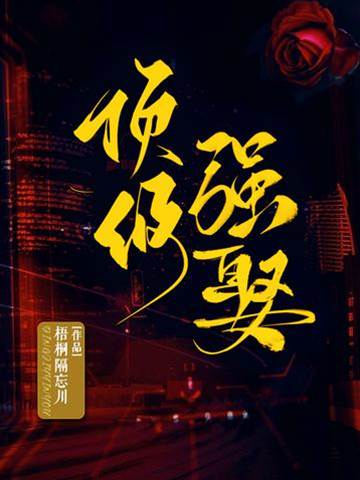《一生一世,江南老》 第八章 終是輪回意(2)
昭昭一進休息室,此起彼伏的全是“小姨,小姑姑”,年紀大的,小的全都有。人剛坐到沙發上,沈衍不到兩歲的兒子更爬到上,地了句:“小姨,”咬著的領口,“小舅爺爺,小舅爺爺……”
剛學說話的娃娃,問不全乎,意思是問沈策在哪,找不到還委屈,委屈了還要哭。于是昭昭抱著沈衍的小娃,盡著一個輩的職責,哄……侄孫子。
等沈策再面,長裹住了上的傷,短袖下出來的還有大片的青,額頭上也有破的印。他看到昭昭和侄孫子抱了一對樹袋熊母子,直接問責沈衍:“帶來又不哄?”沈衍訕笑,將兒子接到懷里,先抱去睡了。
沈策挨著,落座,手臂搭到后頭的沙發靠背上。
如此時間,梁錦華早被趕走。沈衍再一走,這里年歲大的就剩下沈策和。
“小舅舅,我給你上藥。”攔過轎車的男孩子到他邊,舉著傷藥。
“小舅讓你打電話給小姨,你都不肯,現在要討好了?”有孩說,正是方才電話里昭昭來的人。
小孩子斗,毫不覺有何不妥。
說者無心,可聽者有意。
昭昭目走,在想,做點什麼好。
“有小姨在,不用你們,”沈策把傷藥順理章遞過來,“隔壁沒人。”
言罷起。
昭昭在小外甥的失落里,跟上他。經過一室的歡鬧,去了隔壁的小房間,小小的茶室,有沙發,還有飄著裊裊青煙的香爐。木刻畫的屏風,擋住了門口的視線。
里頭倒是靜,耳的全是屏風外的稚笑聲。
昭昭把圓盒子打開,手指沾了明的膏,抬眼,正對上他的眸子。
“你要用手?”
Advertisement
“用手效果好。”故作鎮定,竟然忘了問有沒有棉簽之類的東西。
沈策本想喚人送溫熱的小巾,過去他自己上藥,嫌藥膏粘膩,從不用手,都是如此做。不過現在沒必要了。
他將短袖掉。方才在拳臺上的沈策也是赤著膊,著背,只顧得上擔心他的安危,而現在,他的在直面,從肩到前腰腹的盡收眼底。前,長上系扣的細帶子垂在那,腰很低。
茶杯渥著手,他啜了口:“看著來。”
昭昭把藥抹到掌心里,呵了口氣:“先肩上?”
他靜了一瞬。房間忽然暗沉了。
有噔噔噔噔的腳步聲,一個小影從遮天蔽日的暗里跑出來,抱到他腰上,小手在他后打個結,再不肯松。他低頭想看那張臉,那張小小年紀就驚艷了街坊四鄰的臉。不肯,在他懷里左右擺頭,問說,哥你不要我了,哥你去哪了,哥我沒你會死你知不知道,哥我已經死了三十九日了你知不知道。他想哄,可也想聽說,于是任在懷里哭鬧到后頭,任見自己手上臂間的傷。
百死一生,險些尸骨無存,他顧不上其他,迫不及待想聽妹思念的哭鬧,任把袖管往上卷。
小人兒驚哭連連,跑走了,再回來抱了滿懷的傷藥和布帶,手上竟還抓著一紙袋的紅糖塊。紅糖塞到他齒間,手指挖出大塊的藥膏,小口微張,在掌心呵著氣,隨后兩手輕著,像是要先烘熱那藥。怕涼,涼到他……
殘冬臘月,急景凋年,炭火盆里的暖都不及的手,稚的一雙手。
“就肩上。”沈策從黑暗里到現實的。
昭昭兩手輕了,落在他上。
掌心下的繃了。
Advertisement
手一。
“你可以一。”他冷不丁冒出一句。
手心里有火,燒的是自己,臉也在發熱,倉促劃拉兩圈要收手,沈策恰到好提點:“到熱,淤才能散。”
“怎麼才算熱?”問,不自覺調整著坐姿。方才全心在兩人黏連,沒顧上,被自己給麻了。麻意,像看到脈在自己上如何流淌。
“熱了告訴你。”
昭昭暗自腹誹。
沈策恰瞥了一眼,似聽到的心聲。
“沈齊,”他問外頭,“每次你抹藥,是不是要熱?”
“對,對,”男孩子的聲音回說,“小姨你用力,到發熱!”
“小姨用力!”外邊孩子跟著起哄。
沈策再看,睫下的那雙眼微挑著瞧,像在笑想太多。
昭昭不吭聲了,一門心思著那塊淤青,等到真發熱了,涌起了一種莫名的就。“差不多,換個地方。”沈策低聲說。
這回是腰后。
也不知是不是位置特別,昭昭這回也沒那麼鎮定了,手一覆上那塊瘀青,像全孔被迫打開來,上一時熱一時冷的……
“真想我哥哥?”背對的男人突然問。
停住。
剛才那兩聲哥,是口而出,不帶任何的目的。不知如何解釋。
“以后在外人面前,名字,”他在屬于兩人的寧靜里,對說,“私底下,我都隨你。”
昭昭“嗯”了聲,想逃走。
沈策忽然背過手臂,措手不及,被他鎖住了手腕。昭昭心驚跳,手腕間的灼熱上去,裹上的手背……因為藥膏的潤,兩人的手指都如同泥鰍,一個是想盡一切辦法要留,一個費盡心機要走。
他連回頭都沒有,一手握著早空了的茶杯,一手制住。
Advertisement
他在用溫渥著。
直到屏風外有人問要不要添水,這一縷曖昧黏連應聲而斷。
昭昭見人提壺進來,離開他遠遠的,立到屏風旁,瞧那香爐的裊裊白煙。雙手倒背在后,還在因為剛剛的事在恍惚。沈策也不語,了紙巾,一寸寸著手。
“這是什麼香?” 怕添水的人覺出詭異,主問。
“登流眉沉香。”他說。
昭昭“哦”了聲,一聽就是據典取的,多溜了那香爐一眼,回,沈策已經在眼前,還是打著赤膊。
添水的人走了。
時辰已晚,孩子們在外邊大呼小喝道別。屏風,沈策應答自如,直到人走了干凈,仍和面對著面。
想著鬧這樣,也沒法再抹藥:“后背上的都抹好了。剩下的,前面的——”
“前面的,我自己來。”
像隔著空氣能覺到他的溫,他的呼吸力度。四周的擺設,都是那面屏風,立在兩人旁,茶壺茶盞,香爐,甚至壁紙都有影子。影子連著影子,圍攏著他們,遮掩著這房里的一切。
“婚宴時——”
他呼出來的氣息,落到劉海上,是低了頭,在等說。
“你朋友要來嗎?”輕聲問。
似一聲笑,無聲的笑,也只有離得如此近的才能應。
“你嫂子……”他言而止,故意道,“不好說。”
他確信昭昭是真忘了昨夜。
沒人會傻到接連試探兩次,試探他有沒有朋友。
昭昭被那三個字砸得心神難定,那剛剛算什麼,片刻的難自已?
沈策背過,笑著將擱在原地,回去沙發上閑坐著,還在為自己斟茶。一抬頭,眼瞅繞過屏風,問了句:“真不聽完?”
這恐怕是頭次對他白臉,半步不留,轉臉就不見了人影。
Advertisement
沈策著那面屏風。
登流眉……
那小人影往他上坐懷里鉆,舉著卷書,哥,登流眉的香,焚一片則盈室,香霧三日不散,哥你日后做了大將軍,一箱箱堆滿我們屋子。的發在他耳下輕蹭著,是在撒,孩子樣的親昵。登流眉,登流眉,從日落前念到點燈后,他被這一聲聲催的心如火燒,別說登流眉,他連殘香都買不起。不日將走,誰來護……他甚至想,去茍且誰家的寵侍妾,亦或是柴桑名,用這過人姿容去換的日日好食,夜夜安眠。
世間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當然包括他自己。除了昭昭。
……
沈策仰靠在沙發里,看屏風最高的雕花紋路。從初次聽到昭昭,聽到夜盲,他就約知道有什麼要回來了。
時至今夜,他才真正看到。他曾有個親人,有個妹妹,昭昭。沈昭昭。
***
昭昭回到房間里,姐姐也剛回來。
往年兩姐妹每回見,都要徹夜聊到天明,這一夜也不例外,只是昭昭格外心神不寧。在姐姐訴說剛結束的一段小暗時,在窗臺上前,后,側。到深夜栽倒在床尾,疲憊闔眸。
雕花的屏風像立在房里,他也像在邊,握的手,也不是靜止不的。昨夜在添水的人打擾前,他也曾用指腹輕刮的手背,指背……
電話鈴音鬧醒的是。
姐姐剛在洗過臉,準備回自己房間,替接了電話。
聽筒塞給:“沈策找你。”
昭昭反應良久,突然起,話筒的線不夠長,被一拽,電話機直接撞到床頭,換來姐姐奇怪的一眼。著被驚醒的心悸,眼看門被撞上,先前是簡單怕姐姐在一旁聽到什麼,沒外人了,自然想到昨夜。
“人走了?”
不答。
“還在氣?”人像在旁說著話,“話不聽完,氣一夜值不值得?”
“哥你找我有事嗎?”昭昭板著聲音。
“找你說話。”
“大早上,有什麼好說的。”
“現在十點。”
“……”
“你不是想問嫂子的事嗎?”
“也沒想問,只是客氣客氣,”昭昭自認裝傻的功夫不算一流,也算上乘了,“我不經常在這里,你私生活怎麼樣,也不想知道。”
被捉著手算什麼,是自己先沒拒絕,跟著他去的。只當是經驗,了騙。昭昭在努力繭剝,客觀分析,努力快刀斬麻。
“真不想問?”他再問。
“問什麼?問你何時結婚嗎?”
他笑了。
……
像是算準會惱意上涌,要掛電話,他跟著說:“我道歉。今天陪你,當賠罪。”
昭昭想問他是要賠什麼罪,昨夜荒唐手之罪嗎。最后還是下念頭,他不認,那也不認:“不用。”
“昭昭,”沈策忽然認了真,“我一個人,一直是。”
猜你喜歡
-
完結1286 章

我成了反派的親閨女
反派陸君寒,陰險狡詐,壞事做盡,海城之中,無人不怕。可最後卻慘死在了男主的手中,成了海城圈子裡的大笑話!錦鯉族小公主為了改變這一悲慘結局,千方百計的投胎,成了陸君寒的親閨女陸梨。三歲半的小糰子握緊拳頭:爸爸的生命就由我來守護了!誰都不能欺負他!眾人臉都綠了,這到底是誰欺負誰?!後來——陸君寒:「來人!把他扒光扔到池子裡。」陸梨:「爸爸,我來吧!脫衣服這事我會的。」「……」陸君寒頓了頓:「算了,脫衣服礙眼,把他一隻手給我砍——」話未說完,陸梨先亮出了刀:「我來我來!爸爸,這個我也會的!」陸君寒:「……」事後,有記者問:「陸總,請問是什麼讓你洗心革麵,發誓做個好人呢?」陸君寒含笑不語。為了不帶壞小孩子,他不得不將所有的暴戾陰狠收起,豎立一個好榜樣,將小糰子掰回正道,還要時時刻刻防著其他人騙走她!……可誰知,小心翼翼,千防萬防養大的寶貝閨女,最後居然被一個小魔王叼了去!向來無法無天、陰險狠戾的小魔王一臉乖巧:「梨梨,他們都說你喜歡好人,你看我現在像嗎?」【團寵!巨甜!】
191.4萬字8 30842 -
完結1311 章

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被我撩醒了!
【先婚後愛+大型真香現場+追妻火葬場】 時淺被繼母設計,被迫嫁給了個植物人。植物人老公有三好:有錢,有顏,醒不了! 昏迷三年多的傅斯年醒來,發現自己多了一個妻子。小嬌妻膚白、貌美、大長腿。 傅斯年表示:不愛,不需要!隨後冰冷冷地甩出一份離婚協議。 …… 不久,小有名氣的時淺被拍到上了大佬傅斯年豪車的照片。 傅斯年公開澄清:我和時小姐認識。 網友:只是認識嗎?都車接車送了!坐等傅大佬在線打臉,九百萬粉絲看著呢! 再不久,紅出圈的時淺被拍到與傅斯年同時進入一家酒店,三天三夜才出來。 傅斯年再次澄清:我與時小姐不是你們想的那種關係,並未交往。 網友:傅大佬一定是追求失敗!這世上若有傅大佬都搞不定的女人,那一定是她們的女神時淺!三千萬粉絲,繼續吃瓜! 再再不久,坐擁兩億粉絲的時淺在最佳女主角頒獎典禮的現場,孕吐了! 傅斯年緩步上臺,摟著時淺的腰,「謝謝大家關心,傅太太懷上二胎了!」 兩億粉絲集體懵圈:時淺大美人竟然已經是二胎了?她們吃瓜的速度到底是哪一步沒跟上?
157.2萬字8 601282 -
完結737 章
霍太太她又奶又萌
溫知羽非但冇有掙開,反而摟緊了霍司硯。她生得好看,身材更是一流。霍紹霍不輕易衝動的人,也願意和她來段露水姻緣。
102.7萬字8 50012 -
完結2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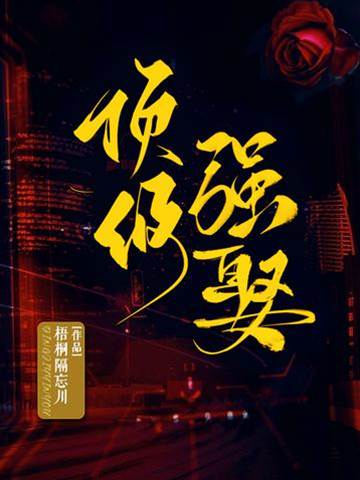
頂級強娶
【大女主?替嫁閃婚?先婚後愛?女主輕微野?前任火葬場直接送監獄?男女主有嘴?1v1雙潔?暖寵文】被未婚夫當街摔傷怎麼辦?池念:站起來,揍他!前未婚夫企圖下藥用強挽回感情怎麼辦?池念:報警,打官司,送他進去!前未婚夫的父親用換臉視頻威脅怎麼辦?池念:一起送進去!*堂姐逃婚,家裏將池念賠給堂姐的未婚夫。初見樓西晏,他坐在輪椅上,白襯衫上濺滿了五顏六色的顏料。他問她,“蕭家將你賠給我,如果結婚,婚後你會摁著我錘嗎?”一場閃婚,池念對樓西晏說,“我在外麵生活了十八年,豪門貴女應該有的禮儀和規矩不大懂,你看不慣可以提,我盡量裝出來。”後來,池念好奇問樓西晏,“你當初怎麼就答應蕭家,將我賠給你的?”他吻她額頭,“我看到你從地上爬起來,摁著前任哥就錘,我覺得你好帥,我的心也一下跳得好快。”*樓西晏是用了手段強行娶到池念的。婚後,他使勁對池念好。尊重她,心疼她,順從她,甚至坦白自己一見鍾情後為了娶到她而使的雷霆手段。池念問,“如果我現在要走,你會攔嗎?”“不會,我強娶,但不會豪奪。”再後來,池念才終於明白樓西晏的布局,他最頂級強娶手段,是用尊重和愛包圍了她……
51.8萬字8.25 37689 -
完結1054 章

嬌妻在上,大叔乖乖寵我
高冷男神周霆深年近三十不近女色,直到有一天,撿到了一個嬌滴滴的小美人,瞬間變身寵妻狂魔。霧霧,我們結婚好不好?不要不要,你……年紀……太大了。什麼,你再說一遍?年齡!我說年齡!什麼,嫌棄他大?直接撲倒教會她年紀大有年紀大的好處!【先婚後愛+高甜無虐+腹黑大叔X小白兔嬌妻】
178.5萬字8.33 241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