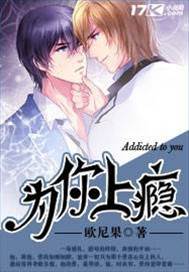《離開七團後全滅》第26節
的花叢裏。到我自己時就沒這麽走運了,再的土壤也會加重嗆傷的傷勢。我從窗戶中出來,重重墜落在地,雖然雙腳先著地緩衝了墜落的大部分衝力,但還是夠我的。我的耳邊隻能聽見一陣哄哄的嗡鳴。這不是周圍的聲音,而是來自於我的腦海。我到自己癱瘓了,到周都變得蒼白明,我的皮浮起一片發冷的東西。艾德跑過來,他對我說話,但我什麽都沒有聽到--隻有他的在。過了一會兒,他大概發現我聽不到他說話,於是讓我躺在枯萎的花叢中,一養料和不明的臊臭味彌漫在周圍,他將我藏好,轉匆匆離去。
25.生命河
這一次,我夢見我在母親的子宮裏。
我對這個地方很陌生,因為我對母親也很陌生。是一個虛幻的影子,有點神,還有點詭異,沒有臉部特征,發型容易混淆。唯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總是上穿著白襯,下`穿著紅。這一定是我潛意識中構造出來的母親,一個大眾形象,白意味著純潔,紅意味著生育。這個形象非常重要,當我不知道母親究竟是誰的時候,我賦予純潔無瑕的本質,如同天使一樣溫慈,而生育則是我和之間唯一的紐帶。生下了我,返回了天堂。實際上,我在家庭相冊裏見過母親。從一歲開始的照片,直到懷孕,不過我一直固執地認為那是羅德和瑪拿來欺騙我的冒牌貨,對於母親的樣子,我總是頑固而又吹求疵地有著自己的想法。
我夢見周圍一片漆黑,在這個狹小悶熱的地方不能彈,全都疼。一種奇怪的聲音在四周回,像心跳聲,又像水滴聲,甚至有點像什麽人在呼喚我的名字。我無法出聲,與世隔絕,四麵八方湧來的熱流散發著腥臭味,一種羊水的味道(我本不知道羊水是什麽味)。忽然,周圍的聲音又改變了,變磨聲,就像外祖父在花園裏翻土的聲音,鐵鍬叉近土裏。我突然開了竅,四周的溫度驟然降低,我發現自己躺在冰冷的墓中,耳邊傳來清晰的撒土聲。
Advertisement
我死了嗎?胡說八道,怎麽會有這種事?我想從這個惡夢中醒來。我睜開眼睛,可看到的卻是黑暗騎士。他騎在幽靈馬上,灰綠的眼睛看著夢中無能為力的我。
"你在想什麽?"他問我。
我說不出來,我已是個僵的死人了。我想對他說:我很後悔,對過去所做的一切悔恨加。他朝我出手來,黑的,閃爍著金屬澤的右手,一直向我的腮部。盡管這一下是有點聳人聽聞了,但他的手就在我耳邊,我覺得一陣清涼。
接著,我醒了。
在我醒來的一刻,我看到了"對手"。
他正彎著腰,手指輕輕按著我的太。
"他醒了。"這是珍妮在說話。
我一時不太明白究竟發生什麽事,枯萎花叢中出的一小塊天空是我最後看到的景象,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空白。等我的腦子稍微清楚一點才了解到目前的狀況--我大概得救了,至沒有落在"自己人"手裏。
我試著一,活肢、,但的覺還沒有恢複。這不免讓我有些恐慌,開口問:"我怎麽了?"
"你了傷。""對手"說,他平靜地陳述一個我早知道的事實,可我想問的並不是這個。
"為什麽我不了?"
"是因為麻藥的關係。"他說,"再過一會兒你就會覺得疼,不過看來你很想要疼痛,這樣就不必擔心自己癱瘓。"
我鬆了口氣。
"對手"正看著我,似乎在等待我的說明,越過他的肩膀,珍妮和羅恩也在看我:士神平靜,男士則保持一貫的冷漠。羅恩對我仍然耿耿於懷,要讓他忘記同伴的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艾德走過來,站在我麵前。他似乎有話要說,我們全都看著他。
Advertisement
"對不起。"他對我說,"我不該這麽做。"
"為什麽道歉。"
艾德看了看羅恩,羅恩平靜地說:"是我讓他這麽幹的,我一直在你們後。"
"哦。"我忽然靈一閃,明白他的意思。這麽說即使我什麽都不做,艾德也不會有事,羅恩隻是想看看我和嗆火之間會不會來真的。我問:"結果怎樣,我合格了嗎?"
即使此刻麵對我的問話,羅恩仍能保持坦然的沉默,他的雙眼、神、任何舉都無法反映心的想法。
我疲憊極了,像剛從狂風暴雨中歸來。
"好了。""對手"說,"出去吧。"
他把艾德推到羅恩跟前,我以為他也會跟著出去--這裏是什麽地方,像個閣樓。
"對手"最終留了下來,在趕走所有人後,從角落裏搬了一張椅子,坐在床前。
這是一張普通的彈簧床,結實、沉重,冒著一老舊的傻氣,不時發出咯吱聲。我盯著他看,他也毫不回避。我們第一次不在危機四伏的場所會麵,而且周圍沒有其他人。也許這會是一個說服他的好機會,他應該能冷靜地做出判斷。
但是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對手"已先開了口,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反應確實有些遲鈍。
"你打算什麽時候走?"他直截了當地問。
"我?"
"我在教堂後麵找到你的背包。"他說,"手電筒、淡藥、火柴、防水布、指南針......唯獨沒有吃的。"
"我找不到吃的。"
"我可以給你,足夠你到下一個落腳點。如果你要走的話,還能分給你一些巧克力。"
他的說話方式很奇特,不會讓人覺糟糕,也不像我那樣強而明確地說"希你們離開"。這使我到,他並不是要趕我走,離不離開完全取決於我自己的決定。
Advertisement
"我得想一想。"我說,"我還沒有想清楚。"
"當然。"他停頓了一會兒說,"如果你想繼續留在這裏,我也不會反對。也許你會對羅恩的態度到不高興,但是死去的盧克是他的兄弟,他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從親人去世的悲痛中走出來。人們常說:死者可以摧毀生者。"
"你也這樣想嗎?"
"是的,也許吧。"他說,"每個人都經曆過這種事。"
"比如凱瑟琳。"
他吃了一驚,非常意外。
"你從哪聽來的這個名字。"
"凱瑟琳?S?米勒夫人,我看到的墓碑。他是艾德的母親。"我說,"這也是你不想離開的原因?"
"不。"他又停頓了一下,看著我說,"紀念一個人最好的方法是將牢記在心,我們留在這裏則是有別的原因。"
"是嗎?"
-_-!思-_-!兔-_-!在-_-!線-_-!閱-_-!讀-_-!
"對手"說:"你會知道的。"
我原本以為他會點頭說是,再一口回絕我打聽這個的要求,可他看起來並不生氣,甚至給了我一個非常值得回味的答案--你會知道的,但還需時間。
"嗆傷恢複之前,你可以留在這裏,不管白天還是晚上,至會有一個人看顧。"
在我傾聽這些話時,我們之間堅不可摧的壁壘似乎有了小小的缺口。
這個小屋四周環境並不明亮,甚至可說昏暗,他在背的一麵說:"其實我應該道歉,然後謝你。"
我那時的覺簡直就是寵若驚,忍不住重複了一遍:"道歉?謝我?為什麽?"
"還記得羅恩說,他記住了盧克上的每一道傷口嗎?"
"記得。"然而我想起的是那個盧克的男人全鮮淋漓,倒掛在樹上的樣子,還有那雙灰白的眼睛反天空的微。這不免讓我有些心虛,希"對手"能跳過這些,直接進正題。"對手"說:"我也記得,但我不像羅恩隻記住了傷口的位置。我察看盧克的,那些刀傷已經足以讓他斃命,但他會死得很痛苦,時間會很長。想必製造這些傷口的人是希能讓他驗到最可怕的痛苦,並讓痛苦更持久一些。雖然最後致命的是對準心髒的擊,可在那種況下,本不需要浪費紫淡。"
Advertisement
他看著我說:"現在我想問,你有沒有把刀叉近盧克的,割斷他的嚨?你有沒有參與這場殺?"
這時,我忽然到有什麽東西從眼前飛過,不由自主地眨了一下眼睛。
"沒有。"我回答。
在這簡短的一刻,"對手"似乎鬆了口氣。他說:"抱歉,謝謝。"
"真的嗎?"我說,"你相信了?"
這麽輕而易舉,簡直不可思議。
"對手"站在門口說:"我相信了。你演得太像真的了。"
他出去之後,我開始反複琢磨這些麻煩而複雜的事為什麽都讓我遇上了,就好像踩到老鼠夾子摔倒後又砸碎了花瓶。我想我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噩運和死神總是形影不離。
至於"對手",我可以說,他原本並不願意,甚至沒有想過要接納一個陌生人,即使此刻他做了這樣的決定,我也認為是在冒險。羅恩一看見我就生氣,因為他沒辦法一一找到殺害盧克的兇手,至目前做不到,於是隻能把氣出在我上。這對一個團隊而言非常危險,即使我本還算不上隊員,隻是暫時被允許待在這裏,但矛盾仍然無不在。
我躺在床上又試著一,這次隻覺得起來覺十分奇怪,好像的一部分不是自己的。稍稍讓我安心的是,這個遲鈍麻木的軀是一個遠離痛苦的軀,我決定就這樣睡一會兒,避開疼痛襲來的時段。最近總是東躲稀zang,已經很久沒有接過床了。在這張簡易的彈簧床上,我很快睡著,並且沒有到噩夢侵擾。這是我流浪至今最舒適的一覺,不知睡了多久,最後被傷口傳的疼痛弄醒。我出了一冷汗,從腰部的位置開始,一種噴火似的劇痛沿著脊椎爬上來。我的也開始因為這種疼痛而僵。起先我還以為這是因為睡覺的姿勢不對造的,我應該側躺或者俯臥,不過後來發現要換一個姿勢本是不可能的事,這隻會讓我更多罪。
我堅持了一會兒,手朝旁邊去,希能有什麽東西讓我握在手裏,這樣好分散注意力,或是有個撒氣的地方。我的手在彈簧床靠牆的那邊了幾下,手指到一團茸茸的東西。我將它拉過來,是一隻絨小熊。可能由於長期把玩,玩熊上的絨已經有些落,一塊塊像長了疥瘡。這種老式玩偶也像過去的工匠們那樣古板嚴肅,瞪著兩個圓圓的眼睛,傻乎乎的樣子。小時候我有過一個類似的玩熊,但我總是把它扔到床的那一頭去,我非常討厭和它一起睡覺,那是小孩才幹的事。但是我忽然有些明白為什麽人們總喜歡在孩子床頭放一個玩娃娃,這樣能夠填補空缺,能讓孩子們孤獨時抱個滿懷,生氣時用力發泄。玩偶是的化。
房間裏有了一些微,我不知道
猜你喜歡
-
完結65 章

無法攻略的賀先生
*手動【生子/狗血/帶球跑/追妻火葬場】高亮* *霸道醋精狗比攻×軟糯哭包小美人受 *這年頭狗血文生存真的不易,作者就這點愛好了,別罵了,再罵孩子就傻了。 賀商越習慣了見到陶洛清。 那個說著要追自己,做事冒冒失失的漂亮小美人。 冬日寒意蕭冷,陶洛清的笑容卻宛如暖陽治愈。 再一次見到陶洛清的身影,賀商越心里微暖,偏偏嘴上還是那樣:“不是叫你別再來了嗎?” 他以為小美人會繼續對他笑。 然而這次陶洛清眉眼低落,沉默未語。 第二天開始,陶洛清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賀商越有意無意路過他的工作室好幾次,后來才知道,人都搬走了。 — 陶洛清追了賀商越幾個月,費盡心思卻毫無結果,最后決定放棄。 哪里想到兩個月后,難得出門取個快遞的他卻在自家樓下被賀商越堵住。 賀商越將他困在寬大結實的懷抱里,霸道強勢地問道:“為什麼不出現了?招惹了我就想跑?” 陶洛清眨著迷惑不解的雙眼:“不是你說的……” 話被賀商越打斷,他大氣不喘,不容置喙地說道:“我沒說,你也不準跑。”
25.8萬字8 4775 -
連載167 章

永夜之鋒
刺客大師穿到星際時代。其他選手負責打電競,他負責吊打其他選手。劍藏極晝下,他是光中蒞臨的君王; 鋒行永夜中,他是世間生死的無常。 “你們知道,星際聯賽的難度是這樣排列的: 天堂<簡單<普通<困難<噩夢<地獄<【泰倫•奧丁】” 注意事項: 1.主攻!反穿!蘇破天際,帥裂蒼穹 2.受君是個外星學霸,1v1、HE 3.主要打競技!不慢熱不種田,上來就是贏! 我不管,我就要時髦一把冷題材!60%打電競比賽,30%玩網游,10%現實!【大概吧 作品簡評:主角泰倫•奧丁是西幻世界一名刺客大師,與神明交易後穿越到了星際世界,機緣巧合之下直接出現在電子競技的賽場上。主角此後加入電競圈,一路披荊斬棘,成為炙手可熱的“戰神奧丁”,踏上了用顏值和實力征服全星際的道路。他在圖書館與維克多的巧遇,則開始了一段男神與迷弟的浪漫故事。
43.2萬字8 293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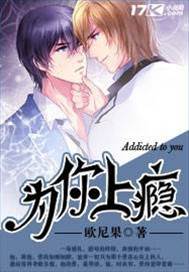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5973 -
連載67 章

鳳凰圖騰
誰家的嬌兒憨然入夢,春夜裡金酒銀樽葡萄紅?誰家的天下灰白憧憧,江山萬里、一騎蒼穹 睥睨家國千萬場,白衣銀鎧、劍影刀狂;秦淮水上浮胭脂,江南歌不盡,夢裡看春光。
23.1萬字8 919 -
連載113 章

蟲婚
此文"虐"! 狗血! 雷! 慎入…… 一隻雌蟲出嫁了。 它的雄蟲說,“我厭惡蟲族。” 結局HE,先婚後愛,坑品有保證~ 純血雌蟲隱忍受X人類芯子厭世攻
35.7萬字8 11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