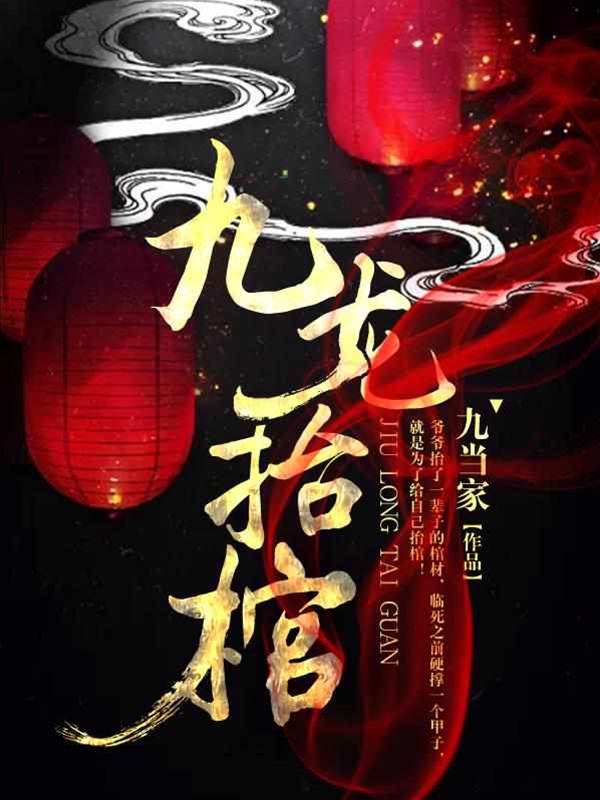《別相信任何人》Chapter 2克麗絲的秘密日誌:11月14日
11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問本他是否蓄過須。我仍然到困,不知道哪些是事實哪些不是。我醒得很早。不像前幾天,醒來時我不覺得自己還是個孩子。我覺自己是年人。的年子。腦子裏盤旋的問題不是我為什麽會跟一個男人同床?而是他是誰?還有我們做了什麽?在浴室裏我驚恐地看著鏡子裏的自己,但它周圍的圖片似乎印證了事實。我看見那個男人的名字——本——不知道什麽原因它似乎有點悉。我的年齡,我的婚姻——似乎是有人提醒了我這些事實的存在,而不是我第一次知道。它們被埋在某,但埋得不深。
本剛去上班,納什醫生就打來了電話。他提醒我日誌的事,然後——等納什醫生說完他會開車來接我做掃描之類的話後——我讀了日誌。裏麵有些事我也許能夠記起,還有幾大段我也許記得寫過,似乎帶著一些殘留的記憶熬過了一夜。
也許這就是為什麽我必須確保日誌的容是真實的。我打了個電話給本。
“本。”他剛剛接起電話說他不忙,我便說,“你蓄過胡子嗎?”
“這真是個奇怪的問題!”他說。我聽到勺子敲在杯子上叮當作響,想象著他正把糖舀到咖啡裏、麵前攤著報紙。我到有點尷尬,不知道該說多。
“我——”我開始說,“我有一段回憶。我想。”
一陣沉默。“回憶?”
“是的。”我說,“我想是的。”腦海裏閃現出那天在日誌裏記下的一幕——他的胡須、他赤的、起的下——還有昨天記起的。我們倆在床上接吻。圖像短暫地發著,又沉思緒深。突然間我到害怕:“我隻是似乎記得你有胡須的模樣。”
Advertisement
他笑了,我聽到他放下飲料。我覺得腳下原本堅實的地麵開始搖。也許我寫的一切是個謊言,畢竟我是個小說家,我想。或者說我曾經是。
突然我想到了我的整套邏輯是多麽無力。我以前是寫虛構故事的,因此我自稱是個小說家的說法可能不過是個虛構,那樣的話我沒有寫過小說。我的思路混起來。
可是那個說法覺很真實,我告訴自己。再說我會打字,至日誌上說我會打……
“你蓄過嗎?”我拚命想要抓住救命稻草,“這件事隻是……很重要……”
“讓我想想。”他說。我想象著他閉上眼睛,似乎一副聚會神的模樣咬著下。“我想我可能留過一次。”他說,“留了很短時間,是很多年前。我忘了……”沉默了一會兒,他接著說,“是的。沒錯,是的。我想我留過,一個星期左右。在很久以前。”
“謝謝你。”我說著鬆了一口氣。腳底的地麵覺牢固一些了。
“你沒事吧?”他問,我回答說我沒事。
中午時分納什醫生來接我。在這之前他讓我先吃點午飯,但我不。我猜我是有點兒張。“我們要去見我的一個同事。”他在車裏說,“帕克斯頓醫生。”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是功能像領域的專家,專治有你這種問題的病人。我們一直在一起工作。”
“好吧。”我說。現在我們坐在他的車裏,在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車流裏一不。“我昨天打電話給你了?”我問。他說我打過。
“你看過你的日誌了?“他問。
我承認我看過了:“大部分,我跳過了一些。它已經很長了。”
他似乎很興趣:“你跳過了哪些部分?”
我想了一會兒。“有幾個地方似乎有點悉。我覺得它們好像隻是提醒了我已經知道的事,已經記得的……”
Advertisement
“那太好了。”他說著向我坐的地方看了一眼,“非常好。”
我到一陣喜悅:“那我昨天打電話幹什麽?”
“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寫過小說。”他說。
“我有嗎?”我說,“寫過嗎?”
他轉看著我,臉上在微笑。“是的。”他說,“是的,你寫過。”
車流再次開始行進,我們啟了。我放下了心。我知道日誌裏說的是真的,便放鬆地投了旅途。
帕克斯頓醫生比我預想的要老一些。他穿著一件花呢夾克,沒有修剪的白發從耳朵和鼻子裏支出來,看上去好像已經過了該退休的年齡。
“歡迎您到文森特館影像中心。”納什醫生剛剛給我們做了介紹,他便說。他一直著我的眼睛,眨眨眼然後握了握我的手。“別擔心。”他加了一句,“沒有聽起來那麽大排場。這兒,進來,讓我帶你到看看。”
我們進了屋。“我們跟醫院和學校都有聯係,朝這邊走,”我們穿過大門時他說,“既是好事,也是麻煩。”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等他說個明白他卻沒有說話。我笑了。
“真的?”我說。他在試著幫助我,我想表現得禮貌一點兒。
“所有人都希我們幹所有的活。”他放聲笑了起來,“但沒人願意給我們付賬單。”
我們走進一間候診室,裏麵點綴著一些空椅子,幾本雜誌和本為我留在家裏的一樣——《廣播時代》,《鄉村生活》和《瑪麗·嘉爾》——還有用過的塑料杯,看上去這裏好像剛剛辦過一個派對,所有人都急匆匆地離開了。帕克斯頓醫生停在了另一道門口:“你想看看控製室嗎?”
“是的。”我說,“讓我看看吧。”
“功能磁共振像(mri)是一門相當新的技。”走進控製室後他說,“你聽說過mri嗎?磁共振像?”
Advertisement
我們站在一個小房間裏,室隻有一排電腦顯示發出幽幽的亮,有扇窗戶占了一麵牆,旁邊是另外一間房,房間的一個大圓筒狀機十分顯眼,從機裏出的一張床像一隻舌頭。我到害怕起來。我對這臺機一無所知。沒有記憶的我怎麽可能知道呢?
“沒有聽過。”我說。
他出了微笑:“我很抱歉。你當然不可能悉這些。mri是個相當規範的程序,有點兒像給照x線。我們用的是一些相同的技,不過實際上是在查看大腦如何工作,就功能來講。”
納什醫生這時說話了——他有一會兒沒有開口了——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小,幾乎有些膽怯。我不知道他是懾於帕克斯頓醫生的權威還是不顧一切地想要給他留個好印象。
“如果你有一個腦瘤,那我們需要掃描你的頭部找出腫瘤所在、找到它影響了大腦的哪個部分。這是在查看大腦的結構。功能mri可以讓我們看到你執行某些任務時使用的是大腦的哪個部分,我們想看看你的大腦如何理記憶。”
“哪些地方亮起來,”帕克斯頓說,“就是在向哪裏流。”
“這有幫助嗎?”我說。
“我們希這將幫助我們確定損害在哪裏。”納什醫生說,“看看出了什麽問題、是哪些地方沒有正常工作。”
“這會讓我恢複記憶?”
他頓了一下,然後說:“我們希如此。”
我下結婚戒指和耳環放在一個塑料托盤上。“你還需要把包放在這裏。”帕克斯頓醫生說,然後他問我是不是還在上打過別的。“你會吃驚的,親的。”當我搖搖頭時他說,“現在是一隻有點吵的老野,你會用到這些。”他遞給我一對黃耳塞。“準備好了嗎?”他說。
Advertisement
我有些猶豫。“我不知道。”我說。恐懼在上遊。房間似乎小了暗了,隔著玻璃看過去掃描儀本顯得森森的。我有種覺,我以前見過它,或者見過一架類似的機。“我不是很確定。”我說。
納什醫生走到了我的邊,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這是完全無痛的。”他說,“隻是有點吵。”
“安全嗎?”我說。
“非常安全。我會在這兒,就隔著一麵玻璃。我們可以全程看著你。”
我的神看上去一定還有點猶豫,因為這時帕克斯頓醫生說:“別擔心。我們會照顧好你,親的。不會出什麽事。”我看著他,他笑著說:“你隻要這麽想:你的記憶藏在了意識的某個地方,我們要用這臺機做的,就是找出它們在哪裏。”
這裏有點冷,盡管他們已經給我裹上了毯;這裏還很黑,隻有一盞紅燈在房間某閃爍,一麵鏡子從我頭頂幾英寸的架子上掛下來,擺的角度可以反屋裏某的電腦屏幕。除了耳塞我還戴著一副耳機,他們說會用它跟我說話,可是現在他們都一聲不吭。我隻聽見遙遠的嗡嗡聲、自己又又重的呼吸聲和單調的怦怦心跳聲。
我的右手抓著一個塑料球,裏麵充滿了氣。“如果你有什麽要告訴我們的,它。”帕克斯頓醫生說,“你說話我們聽不見。”我著它的橡膠表麵,等著。我想閉上眼睛,但他們告訴我要睜著看屏幕。泡沫楔子牢牢地固定住了我的頭;即使我想也不了。我上蓋著一條毯,像一件保護罩。
安靜了片刻,傳來了哢噠一聲。盡管戴著耳塞,聲音還是大得嚇了我一跳,接著又是一聲,第三聲。一個低沉的響聲,來自機部或者我的頭部。我不知道。一隻行遲緩的野正在醒來,停在發起進攻前的沉默中。我抓住橡膠球,下定決心不去它,接著一個聲音——像警報又像鑽床——一遍又一遍地響起,大得不可思議,每響一次我的整個就抖一次。我閉上了眼睛。
我的耳邊有人說話。“克麗。”聲音說,“你能睜開眼睛嗎?”不知道怎麽的,他們可以看到我。“別擔心,一切都很好。”
很好?我想。他們知道什麽做很好?他們知道我是什麽覺嗎?躺在這兒,在一個不記得的城市裏,邊都是從未見過的人。我想我在四飄浮,是完全無的浮萍,任憑風的擺布。
另外一個人的聲音,是納什醫生的聲音:“你能看看照片嗎?想想它們是什麽,說出來,不過隻對你自己說。不要大聲說出來是什麽。”
我睜開了眼睛。在我頭頂的小鏡子裏是一些圖畫,一張接著一張的黑底白圖案。一個男人、一張梯子、一把椅子、一把錘子。每出現一張我便說出名字,然後鏡子裏閃出謝謝你!現在放鬆!的字樣,我把這些話對自己重複一遍好讓自己忙起來,同時也有點好奇人在一架機的肚子裏要如何放鬆。
屏幕上出現了更多指令。回想一個過去發生的事件,它說,然後下麵出現了幾個詞:一個派對。
我閉上了眼睛。
我試著回想和本一起看煙花時我記起的派對。我想象自己在屋頂上挨著我的朋友,聽到腳下派對吵鬧的聲音,嚐出空氣裏焰火的味道。
圖像一幅又一幅地出現了,但它們似乎並不真實。我可以斷定我並非在回憶,而是在想象。
我試著看到基斯,記起他不理睬我,但什麽都想不起來。我又一次失去了這些記憶。它們被埋了起來,仿佛永遠不會麵,但至現在我知道它們存在,它們在那裏,鎖在某個地方。
我的思緒轉向兒時的派對。跟我的母親、姨媽和表妹西一起過的生日。玩繞口令。擊鼓傳花。“搶座位”遊戲。“唱跳停”遊戲。我的母親把糖果包小袋作為獎。夾罐頭和魚醬的三文治,去了麵包皮。鬆糕和果凍。
我想起一件袖子有褶邊的白,荷葉邊子,黑鞋。我的頭發還是金的,坐在一張放著蛋糕和蠟燭的桌子前麵。我深吸一口氣向前傾,吹蠟燭。空氣裏升起了煙霧。
這時另外一個派對的回憶湧了進來。我看到自己在家裏,著臥室的窗外。我著子,大約17歲。街上有些排長隊的的擱板桌,上麵放著一盤盤香腸卷和三明治,一壺壺鮮橙。到掛滿英國國旗,每一個窗口都飄揚著彩旗。藍、紅、白。
猜你喜歡
-
連載285 章

鬼滅之劍聖
黑暗中的鬼怪窺視人間—— 不為人知的角落裡,血腥和殘酷悄然生長。鬼吃人,人斬鬼,千年的傳說和恩怨在命運的血脈裡交織。 在這個黯淡渾濁的世界裡,是誰在舞動手中的刀,開闢著新時代的晨曦.......
51.4萬字8 2127 -
完結25 章
大唐狄公案·銅鐘案
半月街肖屠戶之女純玉被姦殺,純玉的情人被控待判;真智方丈住持的普慈寺中屢生姦淫;林梁兩家結下難解的世仇。為破林梁世仇一案,狄公與其親隨遭遇暗算,一同被扣在銅鐘之下……
5.4萬字8 505 -
完結1320 章

守尸人
太平間,是生與死的交界點,在生死界上,需要注意的忌諱有很多,我是個在醫院太平間旁邊長大的孩子,用不一樣的視角告訴你醫院的禁忌。禁忌1:看到有病人搶救時不要去湊熱鬧。禁忌2:發現有病人家屬把死人生前用品扔到垃圾桶的,不要直接把自己的垃圾扔到上面。禁忌3:夜里聽見貓叫不要出去看,不管你是病人還是家屬。"
222.6萬字8 747 -
連載13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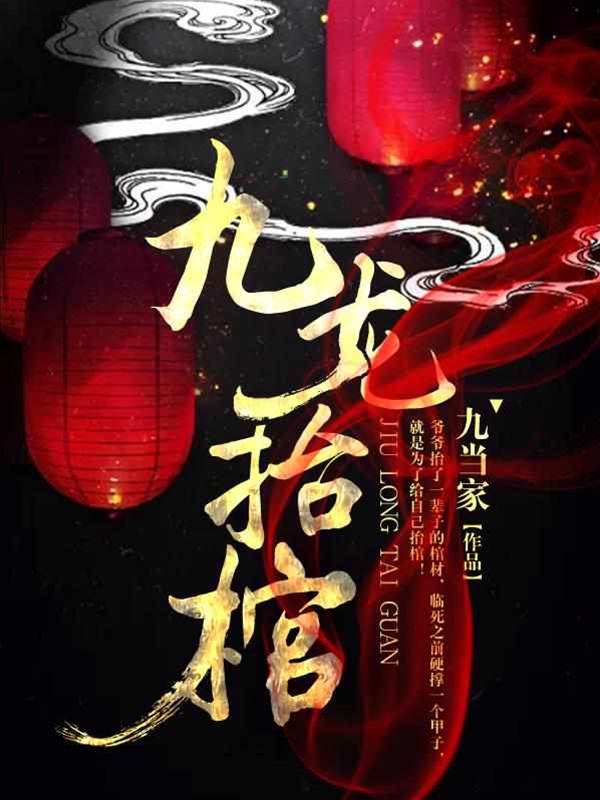
我是一名抬棺匠
爺爺出殯那晚,我抬著石碑在前引路,不敢回頭看,因為身后抬棺的是八只惡鬼……
262.2萬字8 138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