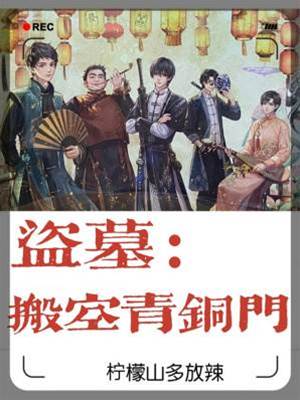《別相信任何人》Chapter 2 克麗絲的秘密日誌:11月21日
11月21日,星期三
整整一上午我都在讀這本日誌。盡管如此,我仍然沒有讀完。有幾頁我跳過了,而有的地方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想要相信它們。現在我在臥室裏,坐在凸肚窗臺上寫記錄。
我的上放著手機。為什麽撥打克萊爾的號碼覺如此艱難?神經衝,收。隻需要這些便足以撥通號碼,沒有什麽複雜的,沒有什麽艱難的。可是恰恰相反,相比之下,拿起一支筆寫下號碼覺要容易多了。
今天早上我走進廚房裏。我的生活建立在流沙上,我想。它從頭一天流到下一天。我認定的事並非真相,我所能確信的、關於我生活和我自己的點點滴滴,則屬於多年以前。我讀過的所有經曆像部小說。納什醫生,本,亞當,現在還有克萊爾。他們的確存在,不過卻像黑暗中的影。他們是陌生人,他們的生活軌道像十字一樣穿過我的生活,一會兒與之叉,一會兒分道揚鑣。難以捉、虛無縹緲,仿佛鬼魂。
而且不僅僅是他們。一切都是如此。所有的一切都源於虛構,是想象的結晶。我非常實實在在地找到些真實的東西,一些在我睡時不會消失的東西。我需要能夠係住自己的支柱。
我打開垃圾桶的蓋子。一暖氣從桶裏湧出來——是分解和腐爛產生的熱量——傳來陣陣味道。腐爛食的甜、惡心的氣味。我可以看見桶裏有張報紙上出一塊填過的字謎遊戲,一個孤零零的茶包打了報紙,把它染了褐。我屏住呼吸跪在地板上。
報紙裏裹著瓷碎片、麵包屑,白細塵,它的下麵有個提包,打了個結封了起來。我把它撈出來,心裏猜是髒紙巾,打算待會有必要的話再把它拆開。包下麵是削下來的土豆皮和一個幾乎空了的塑料瓶,正在往外番茄醬。我把它們都放到一旁。
Advertisement
蛋殼——四五個——還有一把像紙一樣薄的洋蔥皮、去了籽的紅椒渣、一個爛了一半的大蘑菇。
我心滿意足地把東西放回垃圾桶裏,合上蓋。是真的。昨天晚上我們吃的是煎蛋,打碎過一個碟子。我在冰箱裏麵看了看:一個塑料盤裏擺著兩塊豬排。走廊裏本的拖鞋放在樓梯的底部。一切都在,跟昨晚我在日誌裏記下的一毫不差。我沒有虛構,一切都是真的。
這意味著號碼的確是克萊爾的。納什醫生真的給我打過電話。本和我離過婚。
我想現在給納什醫生打電話。我要問他怎麽辦或者甚至想讓他給我代辦。可是這樣一個過客的角我還要在自己的生命裏扮演多久?能夠消極多久?我要掌握主。一個念頭從腦海裏閃過:我可能再也見不到納什醫生了——既然我已經告訴他我的覺、我對他的暗——但我不讓這個念頭生發芽。不管怎麽樣,我需要自己去跟克萊爾聊一聊。
可是要說什麽呢?我們似乎有那麽多要談的,可是又那麽。我們之間有這麽多的過去,可是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我想到了納什醫生告訴我本和我離婚的原因。跟克萊爾有關。
這完全說得通。多年以前,當我最需要他、但最不了解他的時候,我的丈夫跟我離了婚,現在我們又回到了一起,他告訴我,我最好的朋友在這一切發生前搬到了世界的另一端。
這就是我無法鼓起勇氣給打電話的原因嗎?因為我害怕還藏著更多我想也沒有想過的真相?這就是為什麽本似乎並不熱衷於讓我恢複更多記憶的原因?甚至這就是為什麽他一直暗示任何治療的企圖都是徒勞的,這樣我就永遠無法把一幕幕回憶聯係起來從而明白過來到底發生了什麽?
Advertisement
我無法想象他會這麽做。沒有人會。這件事很荒謬。我想到了納什醫生告訴我的、我在醫院的形。你聲稱醫生們謀對付你,他說。表現出妄想的癥狀。
我想知道現在自己是否再一次掉進了同樣的陷阱。
突然間一幕回憶淹沒了我,它幾乎是猛烈地向我湧來,從我空的過去卷起一個浪把我跌跌撞撞地送了回去,卻又飛快地消失了。克萊爾和我,在另一個派對上。“上帝啊。”在說,“真煩人!你知道我覺得什麽出錯了嗎?每個人都他媽的就知道上床。不過是配,知道吧?不管我們怎麽回避,把它說得天花墜打扮別的東西。不過如此。”
有沒有可能我深陷地獄的時候,克萊爾和本在對方上尋求了安?
我低下頭,手機靜靜地躺在我的上。我不知道本每天早上離開後實際上去了哪裏,也不知道在回家的路上他可能會在哪裏停留。哪裏都有可能。我也沒有機會由一次懷疑推斷出另一個懷疑的理由,把一個個事實連接起來。即使有一天我把克萊爾和本捉在床,第二天我也會忘記我見到的東西。我是完的欺騙對象。說不定他們還在往;說不定我已經發現了他們,又忘記了。
我這麽想著,然而不知為什麽我又不這麽想。我相信本,可是我又不信。同時擁有兩種相反的觀點、在兩者之間搖不定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他為什麽要說謊?他隻是覺得自己是對的。我不斷告訴自己。他在保護你,不讓你知道那些你不需要知道的事。
理所當然,我撥了那個號碼。我沒有辦法不那麽做。電話鈴聲響了一會兒,接著傳來哢噠一聲,有人在說話。“嗨。”那個聲音說,“請留言。”
Advertisement
我立刻認出了這個聲音。是克萊爾,毫無疑問。
我給留了一個言。請給我打電話,我說。我是克麗。
我下了樓。我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
*****
我等著。等了一個小時,又變了兩個小時。這個過程裏我記了日誌,沒有打電話來,我做了一個三明治在客廳裏吃了。當我正在廚房裏忙活的時候——著工作臺,把碎屑掃到自己的手掌裏準備倒進水池——門鈴響了,聲音嚇了我一跳。我放下海綿,用烤箱手柄上掛著的抹布幹手,開門去看是誰。
過磨砂玻璃我約見了一個男人的廓,穿的不是製服,相反他上穿的看上去像是西服,係著一條領帶。本?我想,接著才意識到他還在上班。我打開了門。
是納什醫生。我知道這點有一部分原因是不可能是其他人,但另一部分原因是——盡管今天早上讀日誌的時候我無法想象他的模樣、盡管在知道我的丈夫是誰後本對我來說仍然有些陌生——我認出了他。他的頭發有些短,向兩邊分開,係得鬆鬆的領帶不是太整潔,外套下是一件很不搭配的套衫。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臉上驚訝的表。“克麗?”他說。
“是的。”我說,“是的。”我隻把門開了一條。
“是我。埃德。埃德·納什。我是納什醫生。”
“我知道。”我說,“我……”
“你讀過你的日誌了嗎?”
“是的,不過……”
“你沒事吧?”
“是的。”我說,“我沒事。”
他低了聲音:“本在家嗎?”
“不。不。他不在。隻是,嗯,我沒有想到你會來。我們約好了要見麵嗎?”
他猶豫了一下,隻有不到一秒鍾,但已足以打我們的談話節奏。我們沒有約,我知道,或者至我沒有記下來。
Advertisement
“是的。”他說,“你沒有記下來嗎?”
我沒有記,但我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站在房子的門檻上看著對方——我仍然不認為這棟房子是我的家。“我能進來嗎?”他問道。
剛開始我沒有回答,我不確定是不是想請他進門。不知道為什麽這似乎有點不對,像一種背叛。
但是背叛什麽?本的信任?我不再知道他的信任對我有多大的意義,在他撒謊以後。整個上午我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讀這些謊言。
“好的。”我說著打開了門。他進屋時點了點頭,左右看了看。我接過他的外套掛在架上,旁邊掛的一件雨我猜一定是我自己的。“進來。”我指著客廳說,他進了客廳。
我給我們兩人衝了喝的,端給他一杯,拿著自己的坐到他的對麵。他沒有說話,我慢慢地啜了一口等著,他也喝了一口。他把杯子放在我們之間的茶幾上。
“你不記得讓我過來了嗎?”他說。
“不。”我說,“什麽時候?”
這時他說了那句話,讓我上冒起一涼意:“今天早上,我打電話告訴你上哪裏找你的日誌的時候。”
我一點兒也記不得今天早上他打過電話,現在也仍然想不起來,盡管他已經了。
我想起了我寫過的其他東西。一盤我記不起曾經點過的瓜果。一塊我沒有點過的曲奇。
“我不記得了。”我說。一陣恐懼從腳底爬上來。
他的臉上閃過一個擔心的表:“你今天睡過覺嗎?比打瞌睡程度要深的覺?”
“不。”我說,“沒有,完全沒有。我隻是一點兒也不記得了。什麽時候?是什麽時候?”
“克麗,”他說,“冷靜。也許本沒有什麽大不了的。”
“可是如果——我不——”
“克麗,拜托,這並不意味著什麽。你隻是忘記了,僅此而已。所有人有時候都會忘記東西的。”
“可是忘了整段話?那可隻是幾個小時前發生的事!”
“是的。”他說。他說話的口氣和,努力想要讓我平靜下來,卻沒有挪。“不過最近你經曆了很多。你的記憶一直不穩定,忘掉一件事並不意味著你在惡化、你不會再好轉了。好嗎?”我點點頭,不顧一切地想要相信他。“你讓我到這兒來是因為你想跟克萊爾談談,可是你不確定你可以做到。你還想讓我代表你跟本談談。”
“我有嗎?”
“是的,你說你覺得你自己做不到。”
我看著他,想著我記下的所有東西。我意識到我不相信他。我一定是自己找到日誌的,我並沒有讓他今天過來,我不想讓他跟本談。我已經決定現在什麽都不對本說,那為什麽還要讓他來?而且我已經打過電話給克萊爾、留過言了,為什麽還要告訴他我需要他來幫我跟克萊爾談?
他在說謊。我不知道他來這兒還可能有什麽別的原因、有什麽他覺得不能告訴我的。
我沒有記憶,但我並不蠢。“你來這兒到底是為什麽?”我說。他在椅子上挪了挪。也許他隻是想進來看看我住的地方,或者再來看我一次,在我跟本談之前。“你是不是怕我告訴本我們的事以後本會不讓我見你?”
又一個想法冒了出來。也許他本沒有在寫研究報告,也許他花那麽多的時間跟我在一起有其他的原因。我把它趕出了我的腦子。
“不。”他說,“完全不是這個原因,我來是因為你讓我來的。另外,你已經決定不告訴本你在跟我見麵,等到你跟克萊爾談過再說。還記得嗎?”
我搖了搖頭。我不記得,我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麽。
“克萊爾在跟我的丈夫上床。”我說。
他看上去很震驚。“克麗,”他說,“我——”
“他像對待一個傻子一樣對待我。”我說,“在所有事上都撒謊,任何一件事。嗯,我不傻。”
“我覺得這事不太可能。”他說,“為什麽你會那麽想?”
“他們勾搭上已經很多年了。”我說,“這說明了一切:為什麽他告訴我搬走了;為什麽盡管是所謂的我最好的朋友,我卻沒有見過。”
“克麗,”他說,“你在胡思想。”他走過來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本你,我知道。在我試圖說服他讓我跟你見麵的時候,我跟他通過話。他對你十分忠誠,毫無保留。他告訴我他已經失去過你一次,不想再次失去你。他說每當人們試圖治療你的時候他都看著你苦,再也不願意看見你痛苦了。他你,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在試著保護你,不讓你知道真相,我想。”
猜你喜歡
-
完結1354 章

尋屍人
二十年前,父親離奇死亡,人頭被切下擺在了家門口,嚇瘋了母親。二十三年後,我追查起了父親的死,追查的過程中,一場場始料未及的詭異事件接踵而至,千屍秘葬,陰女孕魂,雙屍纏棺……我是一名尋屍人,給你講述我走過的路,見識過的形形色色的古怪之事。
248.9萬字8 5443 -
完結619 章

陰宿
從前有座陰宿山,山中有個尕老漢,尕老漢手里拿著捻好的線,線是噬魂攝魄的線。走上這條路后,校園內的紅衣學姐,別墅中的第三具尸體,畫卷中的平行世界……一個普通人看不見的詭異旅館……一個隔世陰謀,歲月之書,萬妖古窟。和魔教少主的戀情。與千年妖后的隔世孽緣……
111.8萬字8 4555 -
連載1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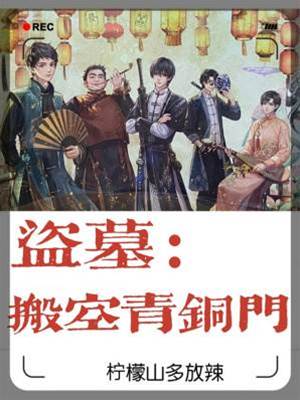
盜墓:搬空青銅門
群尸龍宮,王母鬼宴,尸國之城,青銅門內等你(一起搬空)。千棺枯冢,萬里孤墳,三尺龍淵,墓氣化龍!擁有先秦時期觀星之術和薅羊毛系統的周凡和小哥天真胖子,繼續開啟給三叔的填坑之旅。中元節吳山居整條街被堆滿了送給吳邪的“禮物”,無數個辦喪事的白紙祭奠燈籠和一幅畫。畫上是被七彩流星雨籠罩著的古街花燈游人如織,“古老的街上能遇到古老的靈魂”。眾人在深入張家古樓底下的隕玉山脈深處時,恰逢百年前被除名的象限儀座隕玉流星雨爆發連降三個月,引得青銅門突開,陰兵隊伍中竟然混入了…小花和黑瞎子,帶著二月紅早年收到的...
38.8萬字8 364 -
完結430 章
活人殯葬
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向來最為神秘、讓人聞風喪膽的職業之一。 我就是一名這方面的從業者,這些年來我壓抑著心裡恐怖的秘密輾轉難眠,現在給你娓娓道來我的親身經歷,我真實經歷的殯儀館工作內幕和一些內部禁忌,你或許想不到,在你所看到的殯儀館裡工作的,並不全是活人。
102.4萬字8 11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