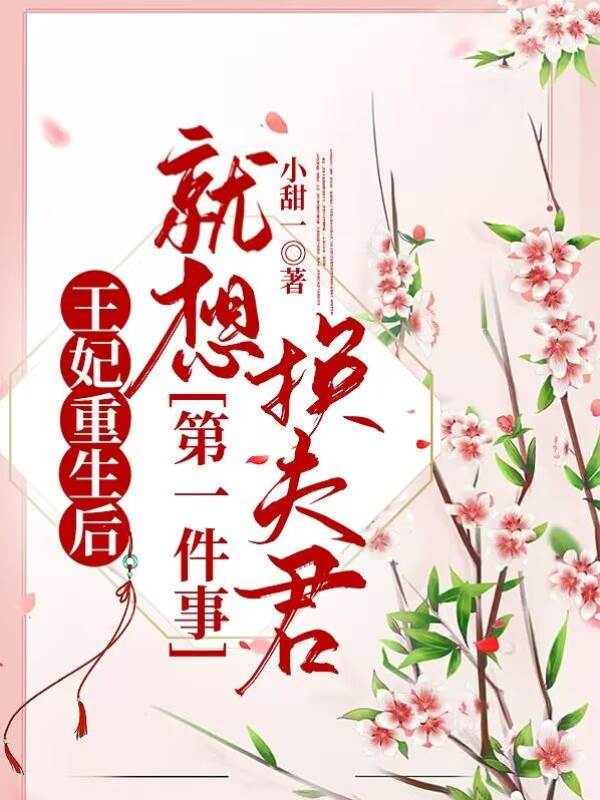《冷王盜妃:側妃不承歡》 第二十五章 這是面具?
瑟瑟從鼻孔里冷哼道:“風暖,你還以為在你的溫鄉麼?”
風暖瞪大了眼睛,才知眼前這個滿臉吻痕的人竟是瑟瑟。見他提及溫鄉,忽想起之前一切,雙頰不微紅。
“你為何要這麼做?為何要真的輕薄江小姐,為何要到青樓買醉?”瑟瑟繃著臉,低幽的聲音里寒意彌漫。
“公子,暖對不起你!”風暖抿,卻是再不出聲。
“為何不說話!”瑟瑟冷聲再問。
“公子,暖此刻心里很,日后必會向你說明一切!”
“你恢復記憶了?”瑟瑟淡淡問道。風暖今日行為,太過怪異,所以猜,他是恢復了記憶。
“是!”風暖輕聲道。
瑟瑟見他平日原本幽深犀利的黑眸此時一片黯淡,知他昔日的記憶必定很不愉快。莫非他和夜無煙有深仇大恨,所以當時才會那樣對待作為夜無煙側妃的?若果真如此,真是僥幸。方才在胭脂樓,風暖一直醉醺醺地垂著頭,沒被夜無煙看到真容。不然,今日他們肯定逃不出來。
Advertisement
馬車不一會兒便出了京城,到了郊外。
前方是一片黑的林,瑟瑟車夫停車,四人下了車,給了車夫一把碎銀,將車夫遣了回去。
瑟瑟回首著隨其后的金總管道:“這是解藥,金總管接好。”
素手從袖中掏出一個錦囊,向著金總管的方向投去。
金總管唯恐囊中再有暗,沒敢手接,刀鞘一,將錦囊挑住,跌落在寬袍之上。他小心翼翼地打開錦囊,卻只見里面只有一張紙,用畫眉的黛青寫著四個字:銀針無毒。
金總管微微一愣,待他抬頭,前方四道人影早已沒在林之中。
林完全被黑暗籠罩,月掙扎著從枝葉的隙間揮灑而下。四人在林中緩步走著,側耳傾聽著外面的靜。很奇怪,金總管似乎并未帶人追來,瑟瑟這才松了一口氣,和風暖一道,將北斗和南星送到了安全之地。
Advertisement
一番折騰下來,天已到了亥正時分,眼前一片月華朦朧。
瑟瑟不覺向眼前那道瘦高影,酒意一醒,此時的風暖,已恢復了一貫的冷然和淡定。真難以想象,那個在香渺山上挾持的那個人和眼前之人竟是同一人。
風暖似乎應到了瑟瑟的注視,回首了一眼,忽從袖中拿出一塊帕子,遞到了瑟瑟面前。
瑟瑟有些愕然,良久才反應過來,自己臉上還遍布著痕,頓時失笑,不曉得風暖是如何看的,不會真將當了好之徒吧。
抬頭著他,月過疏枝碧葉打下重重影,一時看不清他的表。手接過他遞來的帕子,凈了面上的胭脂痕,出一張清水芙蓉般的容。
將污了的帕子扔還給風暖,調笑道:“抱歉,弄臟了。”
風暖不以為然地收起來,卻忽然從的襟里又掏出一件事再次遞了過來。
Advertisement
淡淡月下,瑟瑟看出那是像布一樣薄薄的東西,接到手中,才看清是一副面。
“這是面?暖,你怎麼知道我想要一個面呢?”瑟瑟驚異地問道,欣喜地著手中的面。
猜你喜歡
-
完結831 章

穿書後我成了首輔的心尖寵
宋綿綿穿進書裡,成了未來首輔的炮灰前妻。 和離? 不可能,這輩子都不可能……除非她有車有房有存款。 家裡一窮二白? 挽起袖子使勁乾。 種種田,開開荒,做做生意,攢點錢。 宋綿綿終於賺夠錢想要逃時,某人強勢將她拽進懷裡,“夫人,彆想逃。”
139.6萬字8.33 67906 -
完結581 章

絕色啞妃:王爺,彆來無恙
臨終前還被男友騙光了所有的財產,她含恨而終。再次睜開眼,她竟然穿越到了古代一個啞巴的身上。小啞巴芳齡十八,正是青春好年華,不想有個自稱是她夫君的趙王爺一口一個“賤人”的處處為難。她堂堂21世紀的新新女性怎麼可能被你這封建迷信給打到?虞清絕:趙王爺,你我都是賤人,難道不能一起和平共處嗎?看她一步步破封建思想,平步青雲,殺渣男,捶渣女,絕不手軟!【如果你這輩子,你都不能開口說話,本王便說儘天下情話與你聽。】
115萬字5 46938 -
完結32 章

授他以柄
城欲破,國將亡,皇后裴輕給那人寫了封求救信。整整七日都毫無回音。然絕境之時,他來了。一張絕世俊顏上盡是不屑和輕蔑。蕭淵刀尖滴著血,走到她丈夫面前懶懶地喊了聲皇兄,仗著勤王護駕的功勞,自是要討些恩賞——“那些個金銀財帛我多得是,皇兄可別賞這些。”“不如就把你的皇后送給我玩玩?”
4.2萬字8 10447 -
完結730 章

假千金替嫁糙漢后被寵翻了
【經商種田+天災逃荒+甜寵雙潔】樊梨梨本是天才醫生,名家之后,左手手術刀,右手烹飪勺,堪稱醫廚雙絕。一朝穿越回古代,竟成為惡貫滿盈的假千金,還嫁了個人人恥笑的糙瘸子?村人嘲諷,親戚蔑視,豺狼虎豹來者不善。樊梨梨軟萌小臉板起,握緊了鋒利手術刀。本是天之驕子,身懷絕世醫術,豈容他人放肆!收玉佩,進空間,養極品藥材,種大片農田,蔬菜水果牲畜不斷,逃荒路上舉家歡。一手銀針玩的人眼花繚亂,醫仙谷傳人跪求要做她弟子。失傳百年的食譜她能默寫一百份,開酒樓,做甜品,賺的盆滿缽滿。又帶著自家護妻糙漢在荒地混的風生...
118.5萬字8 255782 -
完結1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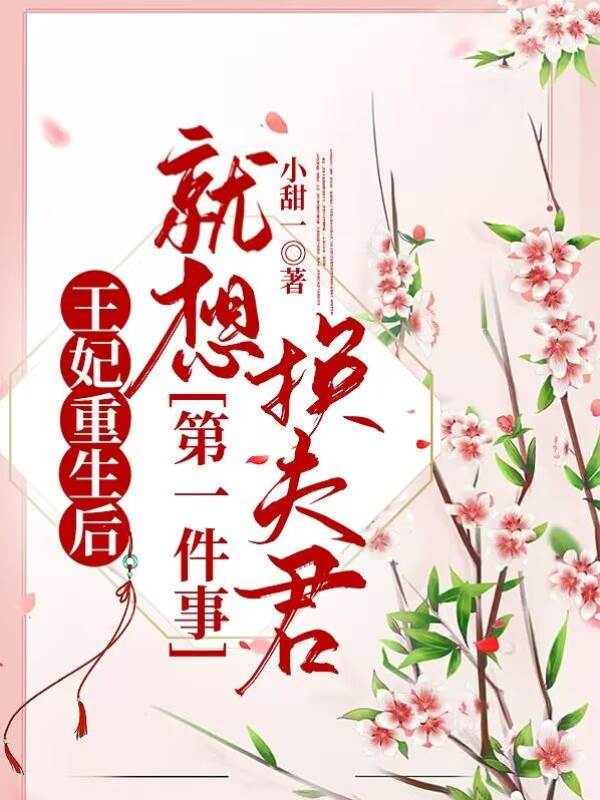
王妃重生後,第一件事就想換夫君
上輩子盛年死於肺癆的昭王妃蘇妧重生了。回想自己前一世,溫婉賢惠,端方持家,一心想把那個冰塊一樣的夫君的心捂熱,結果可想而知;非但沒把冰塊捂化了,反而累的自己年紀輕輕一身毛病,最後還英年早逝;重生一世,蘇妧仔細謹慎的考慮了很久,覺得前世的自己有點矯情,明明有錢有權有娃,還要什麼男人?她剛動了那麼一丟丟想換人的心思,沒成想前世的那個冤家居然也重生了!PS:①日常種田文,②寫男女主,也有男女主的兄弟姐妹③微宅鬥,不虐,就是讓兩個前世沒長嘴的家夥這輩子好好談戀愛好好在一起!(雷者慎入)④雙方都沒有原則性問題!
34.3萬字8 208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