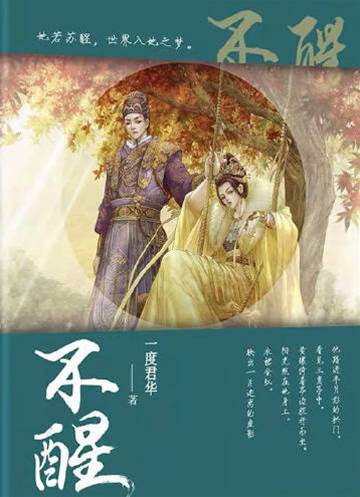《如她一般善良的替身不多了》[如她一般善良的替身不多了] - 第2節
偶有人掀開轎窗朝了一眼,口中嘀咕著什麽,落下轎窗離去。
“蘇棠?”一輛馬車突然在邊停了下來,嗓音清雅且遲疑。
蘇棠腳步一頓,遲鈍了會兒方才轉頭。
一人穿著靛藍團領衫,頭戴烏紗帽出現在狹窄的轎窗,眉目溫厚清斂,比起前幾年單薄的清秀,多了幾分深邃的雅致。
戶部侍郎,陸子洵。
此刻,他正著。
蘇棠怔了怔,沒想到,還能再見到他,下瞬已跪在了雪地上:“民叩見陸大人。”
陸子洵眉頭皺,昔日也曾一襲胡服、縱馬行欒京的子,而今竟這般順從的跪在他跟前:“你終還是怪我。”他低歎。
蘇棠依舊看著地麵:“大人說笑了,民不敢。”
有何資格怪他呢?
父親一介商賈,僥幸爬上首富之位,卻在新帝初登帝位時,勾結三皇子,予其數十萬擔糧草,意圖助其謀反。
彼時還是戶部郎中的陸子洵陸郎中,一年暗中調查,一紙狀書上奏新帝,奉旨抄了蘇家,百萬家財盡歸國庫。
一心為民、剛正不阿的陸大人,抄了意謀逆的大商賈,名遠揚。
若隻是如此,蘇棠是不敢怨、不敢恨的,父親疼寵,可作的確是滔天的惡、犯的是斬九族的罪。
能活著,已屬僥幸。
可陸子洵萬不該……為得父親信任,應下與的婚約。
陸子洵盯良久,著上的,突然想到了什麽:“這三年,在靖王府的子,是你?”
朝堂權勢變更,他自是知曉,而今見上不似有傷,卻滿滿手的跡,也能猜出幾分。
隻是對於鬱殊後院的子,向來傳的五花八門,他從未想過……竟是?
“大人,時辰到了。”馬夫小聲提醒著。
Advertisement
陸子洵看了眼前路,目在跪在地上的人影上定了一會兒:“下朝後我會去靖王府,你在那等我。”
話落,已匆匆離去。
蘇棠站起,如未聽到般,徑自回了王府。
王府的人已死走逃亡的差不多了,滿院的狼藉被藏汙納垢的積雪覆蓋,幹淨且安靜。
兩個守衛站在門口,盤問了好一番才放進去。
蘇棠一邊走進屋子,一邊將上的裳褪去。
太諷刺了,這裳。
不喜歡勞什子的月白,喜歡濃烈的紅,喜歡暗沉的黑。可這三年,隻穿過月白的裳,隻為去討一人的目。
既被當卑賤的影子,便任由那人被丟去葬崗,被野狗啃其皮骨,被禿鷹啖其,不得完軀,不得超生。
錦雲為收拾的包袱仍在床邊。
蘇棠解開包袱,出一件暗灰的裳,隨著裳一同落的,還有一張枯黃的紙,輕飄飄的落在地麵上。
蘇棠手一頓。
那紙上,端端正正書著三字:賣契。
賤籍三年,終於已是自由之。
第2章
靖王府門前的積雪,被踩踏的有些汙濁。
玄馬車停了下來,陸子洵過轎窗朝外看了一眼,溫斂的眉心輕蹙,一前袍方才下去。
“陸大人,”早有守衛上前候著,“抄點的家當已收錄在冊,晚些時辰便能送到您府上。”
“嗯。”陸子洵低應一聲,仍朝裏走著,未曾理會積雪覆蓋下的狼藉,徑自走進後院。
守衛雖不解,卻仍跟在其後。
後院不小,長廊涼亭布置的極為雅致,各院落自有春秋,卻都顯得蕭瑟。唯有一月門下,有不雜的腳印。
陸子洵靜默片刻走了進去,房屋不大,裏麵的香爐地龍早已熄滅,一片冰涼,窗子大開,除卻那些上好的家,再無旁。
Advertisement
他的目卻定在地上那襲沾的月白廣袖長上,那是蘇棠今晨穿的。
京城傳了好久,攝政王鬱殊竟從教坊司買了個子回去,三年獨寵於後院,不令其見客。
果真是。
當年,他曾回蘇府瞧過,可那裏早已被封。
蘇長山三尺白綾自盡於房梁之上,其無妻無子,唯有一,極盡寵溺,恨不得將天上星月都捧到跟前。
隻是蘇長山商賈份,登不得大雅之堂,他也看中了他一門心思場,便求娶了蘇棠。
蘇府倒後,婚約不攻自破,而蘇棠也不知所蹤了。
陸子洵蹲下`子,將那裳拿在手裏,果真沒將他今晨的話聽進去,沒在此等著。
也許聽進去了,卻不願等吧。
想到那個跪在自己跟前的子,恍惚之中,他仿佛又瞧見數年前,那子著一襲紅戎服,縱馬行於市集,而後一勒韁繩,馬匹堪堪停在他跟前。
下頜微揚,手中馬鞭指著他道:“便是你去找爹爹求娶我?生得倒是不錯。”
彼時,仍帶著千金大小姐的驕縱,青高束在後微微擺,嗓音如鈴,眉目飛揚。
“大人,”耳畔,守衛聲音傳來,“那子今晨回來不久便朝城門而去,大抵是離開了。”
陸子洵回神,歎息一聲將裳放下,站起來:“可記得那子樣貌?”
“自是記得。”
“往後若再見,便知會我一聲。”
話落,他已轉朝外走去,背影頎長筆直,清雅如竹。
雖無,但到底……這孽緣因他而起。
……
隆冬的風,總是恨不得刮到人骨子裏。
蘇棠了外裳,站在一片野林邊上,腳下積雪與枯枝極為鬆,遠的白刺的人眼睛痛。
爹是個人,卻也曾告誡“拿人手短吃人”,不願欠鬱殊。
Advertisement
哪怕一無所有,甚至曾淪落風塵下賤至此,可當初在教坊司對他的那一眼萬年,卻是幹淨的。
並非任何人的影子。
王府後院三年的養活、賣契之恩,還他一個麵。
深吸一口氣,蘇棠最終走進野林。
越往裏走,令人作嘔的味道便越發濃鬱,當瞧見一個個的雪包時,知道,到了。
葬崗極大,骨悚然。
幸運的首被掩埋在地下,而今被積雪覆蓋,能得安眠,卻也有埋的極淺的,風吹雨打之下,出半截白骨。
而被直接扔在此的,幾乎不見完好的骨。
如今天寒,仍有不乞人凍死路邊,被扔在此。
風裏夾雜著腥腐的味道,頭頂仍能聽見幾聲,哪怕如今是白日,仍著冷暗沉。
蘇棠心中止不住的栗,從不知,人的肢竟能被蜷、扭曲這番模樣。
邁過一首,朝那堆暴在外的新走去,強忍著肺腑的翻湧,在堆中尋找著。
可即便走到盡頭,都未能找到想找的人。
蘇棠蹙眉,極度的張惹得鼻尖、後背出了一層冷汗,驚懼倒是了些。
隨手拭了下,便繼續尋找。
“啪”的一聲細微聲響,蘇棠子僵直,幸而隻是踩斷了一枯枝,鬆了口氣。
可下瞬,腳踝卻爬上了一陣冰涼。
蘇棠滯在原,一再不敢不。哪怕穿著冬,仍能察覺到腳踝上的寒。
如一隻手,在攥著那裏。
良久蘇棠方才垂首,一個十歲左右的年“首”伏在地上,上過於寬大的裳盡是跡,他的手正攥著的腳踝,手臂上數道痕,有幾已深可見骨。
蘇棠聲音微:“還活著嗎?”
“……”年仍趴在那兒。
Advertisement
良久蘇棠艱難蹲下,拿過枯枝想要將腳踝上的手撥開。
可撥開的瞬間,那手突然轉而抓住了的手腕,如厲鬼討命一般,驚的手一哆嗦,黏膩的染紅了蒼白的。
徹骨的冰涼。
蘇棠怔愣,著那隻手,明明和的一般大小,可骨節分明,手指修長,像極了過去三年,懶懶躺在膝上,著眉眼的那隻。
將他的子翻轉過來。
年臉上的跡早已幹涸,眉目雖稚,卻如尚未綻放的罌粟,隻等一夕盛開,便是萬千風華。
那般悉。
蘇棠忍不住手,輕輕著那麵頰,就像是一場幻覺,卻又無比的真實。
年睫細微的抖了一下,嚨了,隻剩氣聲低低道了句什麽。
蘇棠湊近些許。
“……依依。”聲音極輕。
蘇棠隻覺如五雷轟頂,本著年的臉頰停了,相的眉眼、相的手,還有這句“依依”。
“你是誰?”低喃。
鬱殊覺得自己如在地獄,滿的,揮之不去的寒,凍的他每一寸骨頭都在唞著,卻無法彈,隻能等待著死亡的到來。
恍惚中,一隻手帶著溫熱與淡雅的馨香,輕輕著他的臉頰,他想蹭蹭的手心,如數日終得一口甘霖的修行者,的溫度,可他不了。
是依依嗎?不,不是。
央他舍權棄位,甚至不惜下跪相求;布下伏兵,卻要那伏兵箭弩對準了自己。
不會對他這般溫。
隻有時,那個一遍遍自己的溫暖的手:“娘親……”
蘇棠手指凍得通紅,僵在年的臉頰上,他將當做娘親了?還是……秦若依是他的娘親?
鬱殊今年二十有六,曾聽他喚秦若依“阿姐”,想必秦若依比他要大。
那這年……
“你姓鬱?”蘇棠低低問道。
抓著手腕的手沒有半點靜。
蘇棠沉默半晌:“依依?”
那隻手了。
蘇棠盯著他好一會兒,終聽見心底一聲自嘲的笑——不過是眉目像極了鬱殊罷了,怎會是他?
方才定是癡傻了,好好的大人,如何變十歲的年?
但這年,定是和秦若依、鬱殊有關。
蘇棠吃力地將年背起,腥味頃刻將裹住,臨走前,轉頭看了一眼冷的葬崗。
二人終是無緣,連他的首都未能找到。
第3章
一日後,城郊。
仄的院落盡是枯草、積雪,破舊的房屋一片昏暗,唯有一個鏽跡斑斑的火爐燃著幾塊碎柴,散著點點熱氣,卻到底驅不散隆冬的寒。
年躺在簡陋的病榻上,寬大袍服下的手臂,蒼白瘦弱的。
醫館的老大夫正坐在床邊仔細探著脈象。
良久,老大夫捋了捋白須,輕歎一口氣搖搖頭,小心將那細若新竹的小臂蓋好,靜悄悄轉過來。
“大夫,如何了?”蘇棠上前低聲問。
老大夫看著眼前的姑娘,一深灰麻裳,卻也蓋不住那雙膩白皙的手,眉眼又著幾分執拗,初見隻覺清麗,觀久了竟覺如驚鴻之姿。
“不知那小公子是姑娘何人?”老大
猜你喜歡
-
完結309 章
金牌王妃
陰差陽錯,他錯娶了她,新婚之夜,他說,這輩子他可以給她無盡的寵,卻給不了她愛情.她風輕雲淡回,她可以給他妻子所能給的一切,也給不了他愛情.他分明是一隻狡詐的狐貍,卻裝成純潔的白兔,看她周旋王府內外.雲不悔:此情應是長相久,君若無心我便休.程慕白:萬里河山再美,不及你的笑靨,這浩浩江山留給他人負責,我的餘生,只想對你負責.程佑天:上輩子,我一定欠了你,今生來還債.樓嫣然:我永遠也搶不走不屬於我的東西,生生世世皆如此.
55萬字7.67 58807 -
連載1610 章

十裡紅妝:明妧傳
章節老是會出現空白章節問題,請大家在站內搜索《十裡紅妝:明妧傳》觀看新上的小說~ ———————————————————————————————————————————————————————————————————————————————————————————————— 穿越是門技術活,宅鬥憑的是演技。她攜絕世醫術而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奈何左有狠毒叔母,右有偽善姐妹。算計她,搶了她的未婚夫,還反過來汙衊她裝傻逃婚?刁難,毒殺,陷害接踵而至!避之不及,那就乾脆鬥個天翻地覆!隻是不小心救了一個甩都甩不掉的大麻煩。妖孽、狡詐、腹黑、狠辣、睚眥必報,慣會扮豬吃老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290.2萬字8 26211 -
完結1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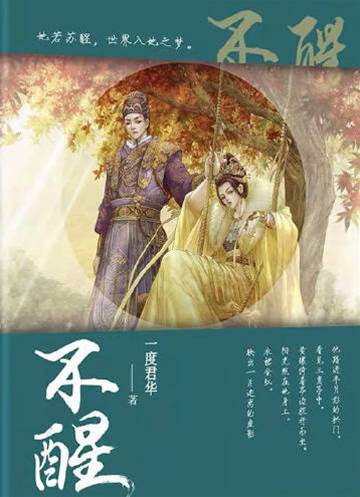
不醒
心機女主x狗東西男主。 黃壤成了一個活死人,被囚禁在密室之中。 司天監監正第一秋把她救了出來。 ——然後搓澡搓黑了五盆水。 二 司天監監正新做了一個“手辦”,異常精緻美貌。眾人越看越像一個女人。 ——那個拒絕自家監正,嫁給了第一仙宗宗主為妻的黃壤! 難道是咱們監正實在過不去這道坎,思念成狂。所以仿著謝夫人……做了個假的?! 眾:震驚! 三 長街之上,監正大人忽然停下腳步。 眾人立刻拔刀戒備,卻見他突然進了一家胭脂鋪。 胭、脂、鋪?! 半個時辰後,眾人為監正大人提著星子黛、額黃茜粉、桃花口脂、牡丹花凍等等瓶瓶罐罐走出胭脂鋪,心中充滿了“我是誰,我在哪兒”的荒誕感。 四 黃壤一路進到監正大人的房間,坐到他的榻上。 監正大人很自覺地蹲下,為她脫去繡鞋。正解著羅襪的系帶,黃壤突然反應過來,兜胸一記窩心腳。 監正提著黃壤的襪子,看看黃壤的臉,又看看她的腳。 如此微賤之事,自己竟幹得這般自然流暢,好像曾經為她做過許多次一樣。 難道自己在她面前,竟有不自知的奴性? 震驚!! 五 小殿下滿月酒,朝廷所有官員全數到場。 黃壤也不管那麼多,撿了好吃的,就準備吃個飽。 她喝了口茶準備順一順嘴裡的糕點。 突然身邊有人說:“八十六殿下真是一臉福相,看著就令人喜愛得緊啊。” “噗——”黃壤一口茶全噴在了地上。 ……萬萬沒想到,我也是喝過自己夫君滿月酒的人了。
46.7萬字8 2164 -
完結136 章

逆天五寶:主母她是個受寵體質
一朝穿越,她直接就當起了便宜媽,寵愛一個遊刃有余,一下子五個寶寶真的吃不消。 她刷著小算盤打算全都退還給孩他爹,卻突然間發現,這一個個的小東西全都是虐渣高手。 她只需勾勾手指,那些曾經欺負她害過她的就全都被她五個寶寶外加娃他爹給碾成了渣渣! 爽點還不止一個,明明一家七口五個都比她小,結果卻是她這個當娘親的成了全家人的心尖寵。
12.5萬字8 37815 -
完結109 章

撩錯夫君后
忠義侯府的三姑娘蘇眉撞壞了腦子,錯把衛國公府庶出的林三爺當成了夫君,放著已經定親的衛國公世子不嫁,非要跟雙腿殘廢的病秧子在一起。林三爺垂死病中驚坐起,忽然多了個媳婦,對方睜著一雙濕漉漉的大眼睛,柔柔地喚他:“夫君……”林三爺:“……三姑娘認錯人了。”從那天起,林以安身后就多了個小尾巴。下人怠慢,小尾巴擼起袖子就沖上前維護,把國公府攪個天翻地覆,替他委屈得吧嗒吧嗒掉眼淚,說她的夫君誰也不能欺負。出身低微的林三爺,心里從此多了一道暖光。后來,蘇眉腦子終于恢復正常,想起自己從前種種行徑,尷尬不已,卷起...
37萬字8 4850 -
完結46 章

早安,老公對我乖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魅力,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故事,這是這個城市的其中一個故事——關于愛情的故事。
15.5萬字8 1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