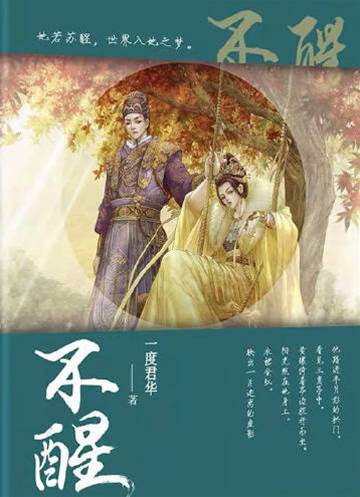《如她一般善良的替身不多了》[如她一般善良的替身不多了] - 第5節
出了以往的誼,哪怕……他會因此殞命。
他爬上高,念了那麽久的人,一心想讓他死,何其諷刺?
若知道他還活著,會如何?歡喜?失落?
會憾吧。
“剛巧你醒了過來,也省的喂藥麻煩了。”蘇棠的聲音傳來,走到床邊火爐旁,上方的藥正泛著熱氣。
將藥端下來盛在碗裏,順手在火爐煮上一盆雪水。
蘇棠端著藥碗到床邊,舀了一勺便要湊近到年邊。
鬱殊目漆黑一片,無半波,他隻是打量著眼前的藥良久:“我上已無任何價值,你也無須裝模作樣。”稚的嗓音仍嘶啞的厲害。
世人皆有所圖,也不會例外。
他不相信這世上有人這般傻,寧願拖著一個累贅,還是一個極有可能為招來殺之禍的累贅。
蘇棠不解了他一眼,二人四目相對,拿著瓷勺的手微抖。
這個年的眼神,太像鬱殊了,正如當初他半靠在膝蓋上,這樣隨意著的形一模一樣——漆黑的深不見底的眼神。
不同的是,那時他滿目的深邃讓人難以捉,唯恐被吸其中,而今卻是……鋪天蓋地的空。
蘇棠輕抿朱,穩了穩心神方道:“我不過喂你吃藥罷了。”
鬱殊收回落在上的目,閉雙眸再不看:“你若也想報複我,趁此刻殺了我更好。”
他說得很平靜,神間無半點生機。
雖然他不記得,除卻將買回府後,自己與之間還有何恩怨,但所有人都盼著他死,確是肯定的。
蘇棠看著他的眉目,沉穩的不似一個年,沉思片刻,最終將藥碗“啪”的一聲放在床邊的桌上,人也坐在火爐旁,安靜烤著冰涼的手。
聽著側的靜,鬱殊心底終忍不住冷笑。
Advertisement
果真這般,不過是個沒什麽耐心的蠢人罷了,如此快的便暴了目的。
什麽喂藥,也不過隻是索他命的借口。
此一生,他的這雙手沾滿鮮,是以一直為人所棄,他竟覺本該如此。
他汙濁如厲鬼,便不該妄想凡人垂憐。
側,有細微的布麻挲的聲音傳來。
蘇棠站起,以手背了藥碗,已沒有了方才的滾燙,將瓷勺放在一旁,起悄然走到床邊,俯視著床上的年。
鬱殊依舊閉著眸,他不記得誰人說過,他像一匹深夜的野,總能察覺到周圍丁點兒風吹草,並防備著一切。
那個人要手了吧。
“得罪了。”人的聲音仍帶著幾分歉意。
鬱殊一未。
下刻,他卻突然覺下頜微,一隻被烤得幹燥而溫暖的手,鉗製了他的下,掰開了他的,隨後,滿口的苦以及溫熱的藥灌了進來,直衝他的嚨,迫使他咽下幾大口。
“你,咳……”鬱殊猛地咳嗽一聲,牽扯到上的傷口,臉煞白。
蘇棠卻已極快將藥灌完,藥碗放在一旁,拿過絹帕便要拭他的角。
“滾。”年的聲音沙啞厲,目終於不負方才的空,恨恨盯著。
從未有人這樣待他,也無人敢這般!
蘇棠拿著絹帕的手一頓,被年這樣眼神盯著,如一頭瞄準了獵的野一般,好一會兒才意識到他雙臂也傷嚴重,不能對如何,索繼續將他角殘留的藥漬去。
“你的子若不喝藥,隻怕連這個臘月都熬不下去。”慢條斯理道,拿過桌上的紙包,拿出一個青瓷瓶,裏麵裝著淡青藥膏。
這也是那老大夫開的,止愈傷的,一小瓶便七錢銀子,金貴的。
Advertisement
蘇棠將瓷瓶塞打開,扭頭看了眼年,遲疑了下:“事急從權,你如今傷重,我為你上藥亦是不得已而為之。”到底男授不親。
年未曾理會,隻以那漆黑如深淵般的眸子死死著。
蘇棠睫輕了下,上前便要掀開他上的被褥。
卻在掀開的瞬間,隻覺眼前一暗,一隻痕遍布的手驀地抬起,掐著的脖頸。
隻是因為傷之故,那隻掐著的手並無力氣。
蘇棠一頓。
頸上那隻手在細微的唞著,年也因著用力,臉青白,額頭陣陣冷汗,手臂上深骨的傷口再次溢出來,一點點順著蒼白的小臂到手肘,滴落在被子上。
“休要……再我……”鬱殊的嗓音逐漸綿。
蘇棠垂眸,看了眼他滴的小臂:“我方才說錯了,你不止熬不過臘月,若這樣下去,隻怕今夜便會盡而亡。”
“……”鬱殊沒有再回應,隻是著自己的手。
強大的意誌力如被衝塌,那手太過瘦小,瘦小到……不像他的手。
蘇棠向這年。
因著疼痛,他的眼神有些渙散,氣息紊而虛弱。隻有那隻手,仍固執而防備的放在的頸部。
他真的……像極了鬱殊,此刻明明痛的要命、卻依舊不做聲的偏執模樣,太像了。
鬱殊也曾過傷。
他那樣的“佞權臣”,總不了刺殺的人。
偶有一日,他肩頭中了一劍,未曾知會任何人,隻一頭鑽進了的房中。
那一劍極深,還抹了毒,險些殃及到他的心口。
了驚嚇,便要去找大夫。鬱殊卻喚住了,如此刻一般,掐著的頸啞聲道:“不許告訴任何人。”
蒼白著臉點頭。
鬱殊本掐著的作逐漸無力,他輕了下的麵頰,低聲道了句:“真乖,去將酒與蠟燭拿來。”
Advertisement
那次,鬱殊喝了半壇酒。
那次,第一次剜去一個人的肩頭。燒紅的匕首鑽進他的肩頭,在裏橫行,黏膩的聲音如催命符,一點點剜去了泛著黑的。
而鬱殊,隻是蒼白著臉躺在那兒,臉上青白,大汗淋漓。
剜完了,上了藥,他還對著朦朧笑了笑,語氣溫:“這是你我二人的,旁人若知道了,可就活不了。”
點頭,活不的不會是他,隻能是。
他滿意了,又如平常一般躺在的膝蓋上,了的眉眼:“真好看。”道完便徹底昏睡過去。
之後,他在的後院,待了整整十五日,不曾出門,不曾見客,隻是陪著。
京城關於專寵於後院的傳聞,也是那時傳出去的。
直到宮裏來了懿旨,點名要見鬱殊,他方才離開。
之後,兩個月未曾出現在後院,隻聽說他又開始忙碌起來。
蘇棠猛地回神。
眼前年已有些堅持不住了。
無奈輕歎一聲,蘇棠抓著年手腕上僅有的一塊沒傷的,將他的手拿了下來。
年幾乎立刻回神,睜開了眼,滿眼防備盯著。
“你如今沒有任何力氣,又能奈我何。”蘇棠拿過絹帕,輕輕了他手臂上的跡,而後將其放被褥下,又著他慢慢躺下。
年的眼神又有些渙散。
蘇棠輕歎,他的防備心也這般重,不還好,若了,他便會立即清醒。仿佛支配他子的,不是力氣,而是……他過於強大的意誌。
藥膏,今日隻怕是上不了,免得最後他因著過激,全傷病再加重。
蘇棠拿過藥碗便朝外麵走去,卻在走到外屋時,鬼使神差的以食指蹭了點殘餘的藥,放口中。
隻一點便苦的令人作嘔。
Advertisement
蘇棠皺眉心,輕輕搖頭,最怕苦了,時但凡偶風寒,爹便會將抱在上,一手端著藥碗,一手拿著餞,喝一口,喂一下。
真不知那年方才喝藥時,如何做到全無表的。
將藥碗刷好,火爐上的熱水已經煮沸,正咕嚕冒著熱氣。
蘇棠照那阿婆所說,小心端著熱水,一點點灌水井口中,陣陣熱氣蒸騰,在睫上氤氳出幾滴極小的水珠,晶瑩剔。
眨了眨眸,水珠順著臉龐低落,如一滴淚,頃刻在雪上。
蘇棠試了試水井的柄,果真鬆了些許,又等了片刻,已經能夠。
起初上來了幾塊碎冰,“噗通”砸在地上,而後方才是泛著霧氣的水,清冽澄澈。
蘇棠抿笑了笑,心底生出幾分安心,左右是不死了。
許是天嚴寒,水井的水竟讓人覺得並不太冷,接了盆水,漱口潔麵,又拆開幾日未曾打理過的青,一點點著清水,整理著。
待到梳洗過後,方才走進屋,火爐仍燒的旺盛,年依舊躺在床榻上,閉雙眸。
如今水倒是有了,飯食卻還是須得準備的。
輕歎一聲,蘇棠在包袱中出些許銀兩,走出門去。
悄悄鎖院門之際,一旁一陣穩健的腳步聲傳來,驚了蘇棠一跳,轉過方才看見,一個高大的男子正從不遠的隔壁大門走出。
那男子生著高大魁梧的形,古銅的皮,一雙劍眉星目,魯莽中又添了似俊朗,穿著一黑,神冷的凍人。
想到二人如今已是鄰居,此人今晨還曾掃過自家門前雪,蘇棠頷首笑了笑:“李公子。”
李阿生目從的手上一掃而過,未曾言語,隻點點頭算作回應,徑自離去。
蘇棠也不在意,看了眼已院門,朝市集走去。
……
聽著院中落鎖的靜,鬱殊幾乎立時睜開雙眸,如寶石般的眸斂。
他吃力抬起手,手臂上的傷口在麻被褥攃的生疼,他隻咬牙忍著。
他的手瘦弱而稚,嗓音也如同年。
這一切都太過詭異。
鬱殊蹙眉心,終以手撐著子,一點一點的坐起。
細微的作,幾乎要了他半條命,全的傷口牽扯著,好些已裂開,染在服,一片黏膩。
他大口呼吸著,眼前一陣陣黑,幾暈厥。
當赤腳終於踩在地上,右骨更是一陣陣鑽心的痛。
那個剛學會“爭食”的年帝王,親自命人持棒打在了他這條上,他記得清清楚楚。
可是,他的形矮了,那雙赤足,也小了,本合的袍服,此刻都空的墜在下。
鬱殊深吸一口氣,一瘸一拐朝外屋走去,全陣陣溼潤,隻不知是疼出的汗,亦或是傷口裂開的。
他終站定在水井旁,那裏擱置著一盆水。
鬱殊踩在雪上,徹骨的寒都已察覺不到,子痛的不控的微。
他低頭,看著水盆中的倒影。
一個年,眉目很是悉。
他手,那年也手。
像極了……當初被那個傾城子拋棄在街頭的“野狗”;也像極了被那穿著月白紗的孩放棄的“乞丐”。
心中一,鬱殊猛地轉,隻作太急,人倏地倒在地上,上、手上的染紅了地上
猜你喜歡
-
完結309 章
金牌王妃
陰差陽錯,他錯娶了她,新婚之夜,他說,這輩子他可以給她無盡的寵,卻給不了她愛情.她風輕雲淡回,她可以給他妻子所能給的一切,也給不了他愛情.他分明是一隻狡詐的狐貍,卻裝成純潔的白兔,看她周旋王府內外.雲不悔:此情應是長相久,君若無心我便休.程慕白:萬里河山再美,不及你的笑靨,這浩浩江山留給他人負責,我的餘生,只想對你負責.程佑天:上輩子,我一定欠了你,今生來還債.樓嫣然:我永遠也搶不走不屬於我的東西,生生世世皆如此.
55萬字7.67 58807 -
連載1610 章

十裡紅妝:明妧傳
章節老是會出現空白章節問題,請大家在站內搜索《十裡紅妝:明妧傳》觀看新上的小說~ ———————————————————————————————————————————————————————————————————————————————————————————————— 穿越是門技術活,宅鬥憑的是演技。她攜絕世醫術而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奈何左有狠毒叔母,右有偽善姐妹。算計她,搶了她的未婚夫,還反過來汙衊她裝傻逃婚?刁難,毒殺,陷害接踵而至!避之不及,那就乾脆鬥個天翻地覆!隻是不小心救了一個甩都甩不掉的大麻煩。妖孽、狡詐、腹黑、狠辣、睚眥必報,慣會扮豬吃老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290.2萬字8 26211 -
完結1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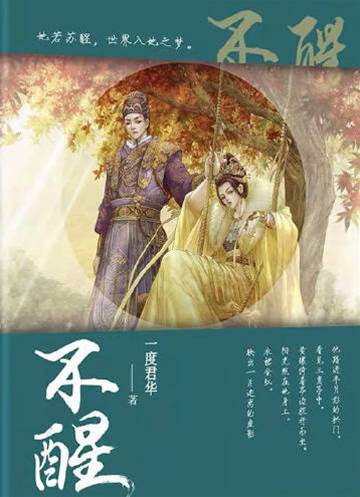
不醒
心機女主x狗東西男主。 黃壤成了一個活死人,被囚禁在密室之中。 司天監監正第一秋把她救了出來。 ——然後搓澡搓黑了五盆水。 二 司天監監正新做了一個“手辦”,異常精緻美貌。眾人越看越像一個女人。 ——那個拒絕自家監正,嫁給了第一仙宗宗主為妻的黃壤! 難道是咱們監正實在過不去這道坎,思念成狂。所以仿著謝夫人……做了個假的?! 眾:震驚! 三 長街之上,監正大人忽然停下腳步。 眾人立刻拔刀戒備,卻見他突然進了一家胭脂鋪。 胭、脂、鋪?! 半個時辰後,眾人為監正大人提著星子黛、額黃茜粉、桃花口脂、牡丹花凍等等瓶瓶罐罐走出胭脂鋪,心中充滿了“我是誰,我在哪兒”的荒誕感。 四 黃壤一路進到監正大人的房間,坐到他的榻上。 監正大人很自覺地蹲下,為她脫去繡鞋。正解著羅襪的系帶,黃壤突然反應過來,兜胸一記窩心腳。 監正提著黃壤的襪子,看看黃壤的臉,又看看她的腳。 如此微賤之事,自己竟幹得這般自然流暢,好像曾經為她做過許多次一樣。 難道自己在她面前,竟有不自知的奴性? 震驚!! 五 小殿下滿月酒,朝廷所有官員全數到場。 黃壤也不管那麼多,撿了好吃的,就準備吃個飽。 她喝了口茶準備順一順嘴裡的糕點。 突然身邊有人說:“八十六殿下真是一臉福相,看著就令人喜愛得緊啊。” “噗——”黃壤一口茶全噴在了地上。 ……萬萬沒想到,我也是喝過自己夫君滿月酒的人了。
46.7萬字8 2164 -
完結136 章

逆天五寶:主母她是個受寵體質
一朝穿越,她直接就當起了便宜媽,寵愛一個遊刃有余,一下子五個寶寶真的吃不消。 她刷著小算盤打算全都退還給孩他爹,卻突然間發現,這一個個的小東西全都是虐渣高手。 她只需勾勾手指,那些曾經欺負她害過她的就全都被她五個寶寶外加娃他爹給碾成了渣渣! 爽點還不止一個,明明一家七口五個都比她小,結果卻是她這個當娘親的成了全家人的心尖寵。
12.5萬字8 37815 -
完結109 章

撩錯夫君后
忠義侯府的三姑娘蘇眉撞壞了腦子,錯把衛國公府庶出的林三爺當成了夫君,放著已經定親的衛國公世子不嫁,非要跟雙腿殘廢的病秧子在一起。林三爺垂死病中驚坐起,忽然多了個媳婦,對方睜著一雙濕漉漉的大眼睛,柔柔地喚他:“夫君……”林三爺:“……三姑娘認錯人了。”從那天起,林以安身后就多了個小尾巴。下人怠慢,小尾巴擼起袖子就沖上前維護,把國公府攪個天翻地覆,替他委屈得吧嗒吧嗒掉眼淚,說她的夫君誰也不能欺負。出身低微的林三爺,心里從此多了一道暖光。后來,蘇眉腦子終于恢復正常,想起自己從前種種行徑,尷尬不已,卷起...
37萬字8 4850 -
完結46 章

早安,老公對我乖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魅力,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故事,這是這個城市的其中一個故事——關于愛情的故事。
15.5萬字8 1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