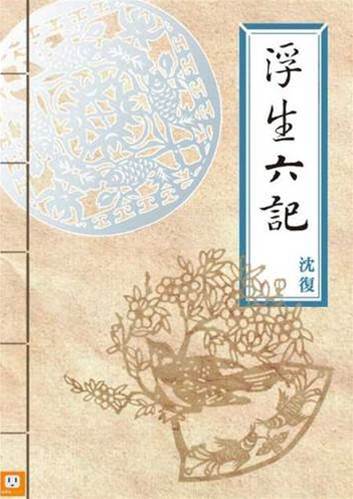《獨立電影人》第27節
,不過幾本膠片都已經被寄掉了,給海關的說明也上了,他完了一件大事,還是開心。
從東四十條所出來後,謝蘭生連走路都變得一顛兒一顛兒的。
他走了兩步,越來越雀躍,越走越快,一分鍾後終於是在北京街頭跑了起來,穿過街道,穿過人群,風起了他的額發,他像一隻乘著風的鳥。
…………
不過,他的興隻持續了大約十五分鍾。
一回到家,謝蘭生就冷靜下來,開始變得患得患失坐立不安。
與郵寄後的興不同,謝蘭生一瞬間覺得自己心裏空落落的,連父母的嘮嘮叨叨都不願意再理會了。
他的工作已經完,現在能做的隻有等了。
如同一個母親等待在外打拚的孩子的隻言片語,謝蘭生也惴惴不安,日夜難眠輾轉反側。
他就像有強迫癥一般,一閑下來便不斷回想拍攝時的每個細節,一會兒覺得這裏不好,一會兒覺得那裏不好,又想改這裏又想改那裏,然而因為知道一切都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便徒勞地唉聲歎氣。
他用最大度數的放大鏡和最苛刻的眼看待《生》這部作品,雖然明知它的眾可能本不會在意,卻還是難。
比較奇怪的事是他從來不懷疑祁勇。他沒想過焦點會不會錯了,畫麵會不會虛了,在他眼裏,莘野、囡囡、祁勇、岑晨肯來幫忙就已經是最大的福,他不應該指責什麽,他唯一能指責的對象就隻有他自己。
有時,因為不想過於糾結,謝蘭生會讓自己轉移注意力,想想莘野。
在莘野去上海那天,謝蘭生曾問過莘野以後究竟想幹什麽。
當時莘野說:“暫時是想當演員了。”
而謝蘭生則是奇道:“為什麽是‘暫時想當’?”
Advertisement
莘野笑笑:“因為另外一件想做的事現在還做不。”
“是什麽?”謝蘭生隻覺得疑——莘野還有做不的?年輕、英俊、明世故,繼父還是城的oldmoney。
莘野笑笑,沒有回答。
看出莘野不打算講,謝蘭生又向他確認:“所以,你一共有兩件想做的事,當演員是其中一件想做的事,此外還有另外一件想做的事,對嗎?”十分奇怪,謝蘭生堅持認為他自己的天賦有限,一生隻能做一件事,而莘野卻一定是能同時完幾項事業的。
莘野頷首,承認了:“對。其實剛從Harvard畢業時……覺得演戲無聊的,不過這幾個月相下來我的看法已經變了。做電影……很有意思。我的水準還遠不夠。如果想講故事,想幫你演繹故事,我還需要再去觀察形形的各類人,理解各自不同的立場,再用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進行誇張、放大,這很有趣。我希有一天自己可以真正到滿意,然後……”
後麵的話莘野沒說。直到很多年以後,謝蘭生才知道莘野當時省略的話是“幫你實現你的夢想,幫你完你的藝。”
那時莘野眼神很沉,謝蘭生隻到疑,卻完全看不明白。
但他其實預到了與自己會有些幹係。他是一個纖細的人,時常會有非常敏銳的察力和“未卜先知”的能力。他22歲,沉湎自,對於渾渾噩噩混沌無知,但卻憑著一本能約窺見了未來的一角。
…………
謝蘭生就這樣在反省和焦慮當中度過了最難捱的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說長很長,說短其實也很短。他常常在胡思想中便突然察覺自己已經發了好幾個小時的呆。一上午,一下午,一晚上,就這麽地,在空白中飛逝而去。每晚睡下,再睜開眼,就又是新的一天了。
Advertisement
這天早上北京有霧,清晨茫茫地一片白,謝蘭生在焦急當中終於接到了後期公司剪輯師Nathan的電話,是來自澳大利亞的國際長途。謝蘭生的爸爸在單位裏是總工程師,家裏有臺固定電話,這在1991年非常罕見。也多虧了這臺電話,謝蘭生能接到長途。
“Hello,”Nathan那悉的嗓音通過話筒傳了出來:“謝導在嗎?”
謝蘭生答:“Thisishe。”也不知道是為什麽,謝蘭生在Nathan的語氣中察覺到了一無奈。
他希是自己多想了。
下一刻,Nathan說:“謝導,《生》膠片我們公司剛剛已經全收到了。”
“嗯,”謝蘭生鬆了一口氣,“太好了。”
看來果然是他多想了。
一切進展都很順利。郵電局並沒丟東西。他的膠片寄過去了,分鏡腳本也寄過去了,不應該再出現任何意料之外的問題了。他檢查過他的膠片,應該沒有明顯劃痕,而他其實可以忍比較細微的損壞。祁勇也並不可能出現大的拍攝事故,要知道,祁勇可是在好萊塢也能拿出手的攝影師。
謝蘭生想自己有時大概真的過分敏[gǎn]了,也不知道是好是壞。
“可是……”那邊Nathan言又止,似乎覺得難以啟齒。不過,半晌後,他終於是又開了口,“謝導,是有這麽一件事……膠片在過澳洲海關時,負責檢驗包裹的海關員對這一塊比較了解,他見報關單上寫的是‘膠片’,寄送地址也是一家電影後期理工廠,然而發件那欄卻是一個個人地址而不是公司地址,便知道這是不正常的,因為過去寄往澳洲電影後期理公司的包裹都來自幾個固定地址,比如,北京都是北影來的。於是,他認定了這個包裹裏的品是違,是有問題的,毫不猶豫地進行了海關檢查。”
Advertisement
“!!!”謝蘭生的呼吸一窒,道,“我在箱子側麵特意了說明!裏麵是膠片!不能見!!!”應該不會出問題的!
“我知道,我看見了。”Nathan又繼續道,“檢查員也看見了。他決定了海關檢查,對於‘膠片’這個說明有點注意,但也沒太注意。他並沒有直接開箱,而是拿去照了x……想先大致看看裏麵品類型,再做定奪。哎,澳洲海關這回可能也是過於自信了。”
聽到這話,謝蘭生呆了。
一般人隻知道膠片不能暴在亮中,卻並不會知道,x,對於膠片來說同樣是致命的。高輻的x掃描會讓圖像立刻出現過度曝和顆粒,深或者黑圖像則會被顯示為綠,其他地方也會霧化,而且無法後期修補。甚至可以說,x比還要致命,因為它是穿的,可以毀滅所有膠片,而不隻是外麵幾層。
謝蘭生的嗓子發,他的右手攥住自己握著話筒的手指頭,仿佛正在什麽不祥之,這不詳讓他渾戰栗發抖。
剛剛接到電話時那讓他|麻的興凝結了冰冷的失落,並且一路到腳尖,令他四肢輕輕唞。
“謝導,”對麵,Nathan語氣沉痛地說,“膠片輻,廢了。”
作者有話要說: 蘭生:我太難了。
第21章《生》(十九)
掛斷電話,謝蘭生去洗了洗手。他打開了水龍頭,不斷地洗,好像希提話筒的那個♪離他而去,可激烈的流水聲卻掩不住他耳中的流澎湃。
膠片廢了。
膠片廢了!膠片廢了膠片廢了!!!
他大腦發麻,太也突突地跳。
那現在呢,他究竟要怎麽辦?膠片以及拍攝資金一個月前就用了,團隊散了,祁勇已經回國了,囡囡、莘野也不在了,整整半年都白幹了。
Advertisement
他不該去澳大利亞做這電影的後期的,他也不該為省經費把膠片放一起寄的,他起碼該以防萬一把膠片全分開裝的……然而一切沒有“如果”,最壞的事已經發生了。⑩思⑩兔⑩在⑩線⑩閱⑩讀⑩
他沒寄過國際包裹,也不知道還有“清關”。他隻覺得,反正不能查看樣片,拍好拍壞都隻能認,先後寄、一起寄,全都是一樣的。
謝蘭生對自己的指責甚至已演變錐心的痛悔。他的口好像是有一團火球,即將裂。
他想到了跟親戚們“求資助”的那些畫麵,想到了和王老師借攝影機的那些畫麵,想到了火車去買膠片的那些畫麵,想到了邀莘野飾演“王福生”的那些畫麵,想到了與村長喝到胃出的那些日子,也想到了請岑晨、祁勇加的那些日子……一幕一幕那樣真實,然而全部是無用功,此刻想來真是諷刺。不僅他自己做無用功,囡囡、莘野、岑晨、祁勇等十幾人也全都在做無用功。
他又想到Nathan說的話,“負責檢驗包裹的海關員對文化產業比較了解……於是,他認定了這個包裹裏的品是違,是有問題的,毫不猶豫地進行了海關檢查。”
謝蘭生用手捂住臉。
他隻是想當當導演,隻是想拍拍電影,這怎麽就這麽難呢?
他甚至都忍不住想,如果他像千千萬萬的螺釘一樣工作,沒有理想,沒有野心,是不是會容易一點?他和別人一樣,老老實實在瀟湘廠當副導演甚至場記,是不是會比較開心?或者,像他父母說的那樣,當年本不考北電,而是考科大,是不是會生活順遂?
有幾個人在工作上要經曆這樣多的波折呢?這樣多的未知、這樣多的不明、這樣多的自責、這樣多的懊悔?
說白了,大家都是一樣活的,就隻有他如此矯。
他知道,惶恐不安,一驚一乍,不是生活本來麵目。
謝蘭生在桌前坐著,渾無力,大腦發麻。
他心頭有千鈞重。它就躲在一片濃稠的黑暗中孜孜窺視,既不出來,也不離開,就隻是在盯著他看。那重的下麵好像還拴著些什麽,如果真提起來,他就不得不麵對比之前的重大得多的東西,那是挫折背後所象征的失敗——他畢業後的前兩年一部片子都沒拍上,而折騰了又一年後他依舊是碌碌無為。
謝蘭生覺得,如果某個家人朋友此刻見到他的表,一定無法認得出來這是一貫樂觀的他,估計覺得這是一個拙劣畫家在以他為模特兒,盡揮灑本人的悲哀。
一直到了晚上十點,謝蘭生還渾渾噩噩。
窗外路口有人燒紙。火焰本來躥得極旺,慢慢慢慢暗了下去,最後變一堆灰屑,風一過,呼啦啦地舞起來,再紛紛揚揚地落下去。謝蘭生覺得,特別像他的這一路,一開始熱高漲,最後了無痕跡。
…………
謝蘭生這整整一天連飯都沒心吃了。
他就躺在自己床上,枕著小枕頭,抱著小被子,對天花板胡發呆,真恨不得長睡不醒。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了次日的一大早。九點左右時,謝蘭生接到了遠在上影廠的莘野電話,問他膠片怎麽樣了,澳洲那邊收到沒有。
“莘野……”
“嗯?怎麽了?”
突然聽到莘野聲音,謝蘭生的
猜你喜歡
-
連載120 章

穿成校草前男友[穿書]
穿成了校園文中瘋狂迷戀校霸男主的癡漢前男友,景辭表示,是數學題不好做,還是考試不好玩,為什麼要談戀愛? 沒興趣,不可能,費時間。 校霸贏驕語錄—— “煩,滾邊去,談個幾把戀愛,沒興趣。” “開玩笑,景辭就是個變態玩意兒,爸爸會多看他一眼?” 后來—— “看到那個考第一的了嗎,那是我男朋友。” “說吧,景辭,數學和我你選哪個。” 再后來—— 校霸同學把景辭按在墻上,狠狠親吻:“乖,說句好聽的就放了你。” 一個真香以及追妻火葬場的故事。 騷里騷氣流氓校霸攻x外冷內軟強迫癥學霸受。
35萬字8.17 24023 -
完結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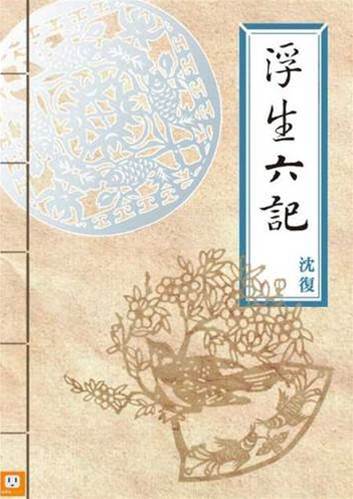
浮生六記
進藤忽然想起,以前戀人學習漢語時,自己湊過去搗亂,無意中瞥見的一句: 每到紅時便成灰。 戀人曾細細地同他講解,但是那時,他不懂得。 現在,對照著眼前的景物,進藤覺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麼。 再往高處,連黑褐色的葉子也落盡了,只剩下枯瘦的荒枝,而日光山頂,已經開始下雪了。 那不是普通的雪,細小的幾乎無法辨認,那麼一丁點兒輕飄的白,好似風飄過的身姿,飄過了便算,不落絲毫痕跡。 進藤攤開手掌,雪并不著身,雖然明明是落在了掌心,也只有那一瞬兒的涼,便似空氣一般化去了。 在鬼怒川的溫泉旅館里,進藤聽旅館的女將說起,這樣的雪,叫做風花。 只在風中開放,在風里凋謝。 在第一場雪還沒有來臨之前,會下一兩次風花,接下來就是細雪了。 是的。 紅葉凋零了,還可以期待風花。 風花過后,仍可以期待細雪。 細雪過后呢? 搜索關鍵字:主角:進藤光,塔矢亮,緒方 ┃ 配角:棋魂眾人 ┃ 其它:棋魂,緒光,浮生六記
3.7萬字8 505 -
完結44 章

婚后熱戀
紅豆牛奶冰擴寫/夫夫婚后戀愛 全文填充,時間線有變,大段倒敘,部分插敘 希望大家不要先入為主,(沒看過原文的就不要補了,看過原文的建議先失憶哈哈哈哈) 人設上面不能保證萬無一失 擴寫有風險,跳坑需謹慎 口嫌體正傲嬌攻 x 豁達通透聰明受
8.3萬字8 3787 -
連載36 章
單行線
: 單行線,是否注定不會有交集? 單向的愛,是否注定不會有結果? 驕傲而自我的單戀,不能停止、無法回頭, 然而前進,是不是一定會有想要的幸福? 都市情緣 情有獨鍾 悵然若失
10萬字8 518 -
完結32 章

蕭秦
虐渣文,不會愛人別扭攻X理智人妻受 現代/短篇/小狗血/HE
4.5萬字8 37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