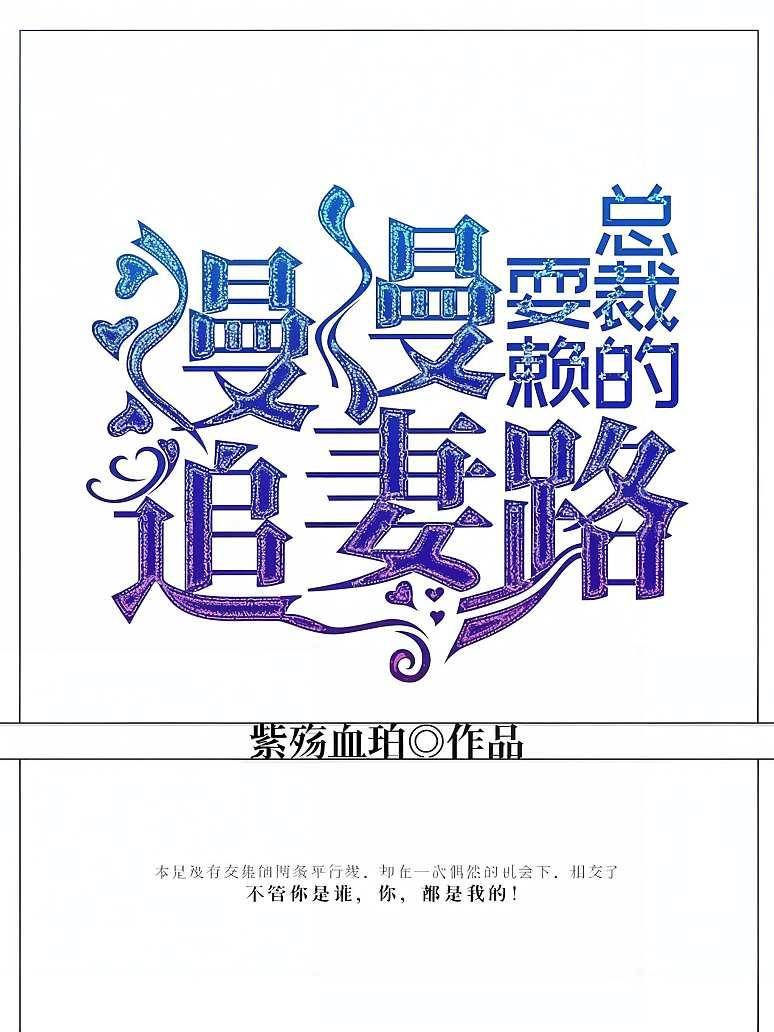《十二年,故人戲》 26.第二十五章 奈何燕歸來(1)
;
兩人在床上鬧騰這麼久,話囫圇著,聽不分明,響卻是真的。
別的院子裡都是通房丫鬟在爺們跟前伺候,行房事時也不躲避,主子們興起讓丫鬟一同上床**、同赴巫山是常有的事。三爺這裡,早先也被長輩安排了丫鬟通房,都被他打發掉,一直是小廝換著睡在房裡伺候。
院子裡,從未有人來過。更何況是同床共枕。
眼下這位沈小姐,是頭一位。
小廝又怎會不懂?
他人一退出去,這話就待下去了。
此時,在西面的,尋不到銅鏡,對著玻璃窗,以指作梳,勉勉強強地理了頭髮。
傅侗文住的是上房的東暗間,西面也有一間,沈奚在那裡換了裳。
回到東面去,兩個丫鬟在伺候傅侗文盥漱。見沈奚來了,傅侗文挽起袖子,親自把另一個銅盆里的白巾撈出來,稍微絞了:「來。」;
沈奚一步一挪,到他面前。
他低頭的神,像要親。
當臉被覆上熱巾,才曉得,他是要給自己臉。
四年。
遠渡重洋地離開,萬水千山地歸來。
在傅家的日子,就從這裡、這個冬天重新開始了。
傅侗文的院子不小。
垂花門進去是穿堂,後頭是間廳,再往後才是上房大院。
上房被隔了一明兩暗的三間房,正中明間是堂屋,兩側暗間,用隔扇隔開。東面那間是傅侗文的臥房,冬天怕寒氣侵,丫鬟們給他掛上了厚重的棉布簾子。
上房東面的耳房是書房。順著西面,打了一面牆的書架,滿是書。
院子裡有四個丫鬟,六個小廝,還有譚慶項和那個年。年名喚萬安。這名,是為住傅侗文上的病魔起的。;
Advertisement
「你先前什麼?」沈奚有一日問他。
年如臨大敵,仿佛說出來,會害傅侗文大病難愈,慎而又慎地答:「我就只萬安。」
說這話時,他在給書房換紅梅。
紅梅是老爺讓人送來的。
沈奚貿然闖傅家,打破一潭死水、一場僵局,老爺對這院子不聞不問的態勢得以緩解。先前垂花門外二十四個守門人,帶著槍,都是老爺的親信,除了運送食材和補品、藥品,完全將這個曾在京城裡風無限的三爺冷落在宅院一角,不聞不問。
而真正打破冰封的,是1915年的12月8日,星期三。
乙卯年,冬月初二。大雪。
這天,丫鬟們燒了滾燙的水,一盆盆去潑院子裡結得冰。小廝們用笤帚將融化的冰碴和水都掃了去,又用棉布吸地面上的水。
沈奚在書房裡,蜷在太師椅上,膝上蓋了狐裘,在等傅侗文。;
看窗外丫鬟小廝忙活著,餘里的男人,背對著。襯衫袖子用細細的黑袖箍勒住,將袖口提高了幾寸。這樣子的穿法,手腕子都在了袖外,方便他翻書和寫字。
「要走了吧?回房去收拾收拾?」下搭在膝蓋上,小聲問。
今日大雪,也是傅老爺壽辰。傅老爺著人傳話來,讓他去聽戲。
這是一道赦令。
可傅侗文並不覺得,只憑沈奚和那謊話就能這樣的太平。
垂花門外,什麼在等著他?是何時局?要如何去應對,在屏退老父親信僕從後,傅侗文早在心裡做了種種猜想。
眼見著,要到去聽戲的時辰了,他還沒拿定主意:是否要帶沈奚去?
「走,一道去。」他合了書。
「我去?」沈奚忙搖頭,「這不妥……」
Advertisement
他微笑著,把書塞回到書架第三層,去把上的狐裘掀了,將沈奚從太師椅里拽起來:「你去,還能打個掩護。」;
「掩護?」沈奚不懂。
他笑,把西裝外套搭在肩上。
「你要我做什麼,先要說好。我並不了解你家裡的人,四年前見過誰都不記得了,你到底有幾個兄弟姐妹?你父親有幾個姨太太?你要我打掩護,是如何打?」
傅侗文把臉上的黑框眼鏡摘下來,鏡折回,在考慮怎麼去解釋。這樣的份,在沈家很敏:「你去,是為了讓我不想說話時,能有個閃避的法子。」
這樣說,倒心裡有譜了。
回房裡,照例是抱了裳去西面暗間裡換。
人走過他旁,傅侗文扣了的手腕子,笑著低語:「今日過節,在這裡換好了。」
大雪也算是過節?「要遲了。」倉促地說。
傅侗文也是在玩笑,沒多堅持,就放逃走了。
他將拇指和食指的指腹輕著,像在回味手腕皮的膩。;
他正在落魄時,掌不住自個的生死,絕不能再拖下水,也不想在當下和有夫妻之實。
沈小姐這三個字,是在給留退路,不子,也是讓能保全自己。那日晨起,他確實在床帳里把看了個乾淨,可也僅是看了。
不過傅侗文畢竟是從風月場過來的男人,這「看」也和旁人的不同。他最喜好在午後小憩、清晨睡醒時把邊睡得迷糊的沈奚抱到懷裡,把睡都剝去,再將的子仔仔細細地瞧一會。從上到下,該看的一樣不落。
「三哥有分寸,」他每回都這樣說,還會笑著逗,「只這樣弄,不妨事的。」
Advertisement
看得堂而皇之,有時之所至也要上好一會,可又說得好似自己是個正人君子。
……
四親八眷聚來府上,比往年都要多。
一來是為傅老爺七十大壽,都說是古來稀的年紀,又是整數頭,自然都要湊個熱鬧;二來是傅家是大總統跟前紅人,如今新皇要登基,沒份捧朝堂上的場子,捧一捧傅家的場子也是好的。;
人一多,府里的車都不夠用,是長輩和眷就分批接了十幾趟。
傅老爺準傅侗文出了院子,卻沒讓他和長輩們一同用午膳,有意削他的臉面。等下午兩點上,傅侗文帶沈奚進了後花園,戲臺子對面是兩層樓,觀戲用的。
樓下早坐滿了人。
圍坐在臺下的男人們多是穿著夾層棉的長衫和馬褂,戴一頂瓜皮的帽子,緞面的。人也是舊式著,旁大多有孩子立著、坐著,人聲嘈雜,沸沸揚揚,好不熱鬧。
都是傅家的遠近親眷。
傅侗文帶沈奚從一樓經過,由著小廝引路上樓,後頭幾個年長的男人見他,忙著起寒暄,都在他「三叔」。等他們走上樓梯了,沈奚才悄聲問:「那幾個,看上去比你年紀大吧?」
傅侗文微笑著,在腦後,笑一笑:「沒錯。」
「我稍後上去就不說話了,你要有用得找我的地方,給我打個眼。」;
「放輕鬆,」他反倒是輕鬆,兩手握了自己上呢子西裝的領口,擺正了,「今日你跟著三哥來,就是看戲的。」
傅侗文角帶了笑,悠哉哉地上了樓,他腳下的皮鞋在樓梯板上一步步的響聲,落在耳中,格外清晰。沈奚瞧見他的右手抄在了長口袋裡,一隻手將襯衫領口扭了一下,輕蔑不屑的神,從他眉梢漾開來。
Advertisement
這細微的作,像給他上了戲妝。
院裡院外的他,判若兩人。
胡琴恰在此刻拉起來,開場了。
沈奚略定了定,跟他上樓。
和那日在書房不同,這回樓上的人都全了。
傅老爺和夫人居中而坐,幾房姨太太帶著各自年紀小的兒子、兒依次坐在夫人下手。另一邊是年長的兒,大爺、二爺和小五爺、六小姐都在,還有三個見了年紀的兒帶著婿。傅侗文帶著一面,二樓雀無聞。;
大家不清老爺的脾氣,都沒招呼。
穿著軍裝的小五爺倒和大家不同,熱絡起,笑著對後伺候的小廝招手:「給我搬個椅子來,」又說,「三哥,坐我這裡。」
「你坐,同三哥客氣什麼。」
傅侗文的右手從長口袋裡收回來,頗恭敬地對上座的人服了:「爹,不孝子給您賀壽了。祝您長春不老,壽同彭祖,」言罷又說,「願咱家孫子輩我這樣的人,也能讓爹您省省心。」前一句還像模像樣,後一句卻是在逗趣了。
那幾個姨娘先笑了,有意給傅侗文打圓場。
傅老爺深嘆著氣:「你啊。」
跟著又是一嘆。
從被押送回府,父子倆從未見過。說不想是假的。
「坐吧,你爹氣你,也不會氣上一輩子。」傅老夫人也開了口。
笑地喚人來,給傅侗文搬了兩把椅子。傅侗文昔日在家裡對下人最好,那幾個伺候的丫鬟和小廝見老爺不計較了,不用吩咐,就給他們上了茶點。;
戲**,樓上的孩子們都跑到了圍欄桿上,笑著,學樓下的男人們好。這樣的日子,就連茶杯里泡漲開的一蓬碧綠茶葉都像有著喜氣。無人不在笑。
沈奚坐在傅侗文側,不言不語地看戲。
沒多會,小五爺傅侗臨就挪坐過來,親厚地和傅侗文低聲聊起來。小五爺的親生母親是朝鮮族的人,生得溫婉,導致兒子也是男生相,眉眼。可偏偏傅家這一輩裡頭,僅有他穿著軍裝。沈奚從他們隻言片語中聽出,小五爺是在保定軍校念書的,即將畢業時因為和同學鬥毆,取消了進北洋軍隊的資格。
保定軍校最後將他發配去了南方的雜牌部隊。傅老爺不肯,還在為他斡旋。
「去南方才好,我會想辦法攪黃父親的安排的,」小五爺低聲笑,「三哥這回恢復了自由,我就有人說話了。今夜去你那裡?」
傅侗文微笑著,翹了二郎,皮鞋在隨著戲腔打節拍:「你老實些,南方的雜牌部隊軍餉都常有發不出的,留在北洋軍最好。」;
小五爺笑:「三哥迂腐了。」
「三哥這剛能走,父親還沒完全消氣,」傅侗文又說,「我那裡,你能去就去。免得牽累你被責罵。」
小五爺軍靴分立,端著架子說:「這怕什麼,都是自家人。」
這邊,小五爺才剛宣誓一般地說完,偎在圍欄桿旁的六小姐傅忽然笑了,對傅侗文說:「三哥,你快看,你看那裡就曉得為什麼父親讓你今日出來了。」
哪裡?沈奚順著六小姐的指向,看過去。
樓梯那裡,有位穿著黑呢子大,脖子上圍著白狐尾的人,兩手斜在大口袋裡,慢慢走了上來。有著極為明的五,留到耳下的短髮梳理的十分整齊,人是在笑著的,可鎖在傅侗文上的目卻在微微抖著。
傅侗文和對視了一眼後,眼風過去,到了戲臺上。
猜你喜歡
-
完結937 章
私家甜寵:雙面總裁太寵妻
雙雙被算計,一昔歡好。他說:“結婚吧!不過我是私生子!”她說:“正好,我是私生女!”彆人隻知道他是傅家不受待見能力低下的私生子,不知道他是國際財團QG的創始人,坐擁萬億身家。彆人隻知道她是黎家名不見經傳的私生女,不知道她是驚才絕絕的金融操盤手,坐擁客戶萬家。當身份被揭曉,狂蜂浪蝶蜂擁而至。他說:“日落西山你不陪,東山再起你是誰?”她說:“窮時執手夕陽,富時方可相擁黎明!”
168.6萬字8.33 85163 -
完結206 章

私藏一個盛夏
「盛夏焰火,落日晚風,都不及你望進我眼里」 阮糖初遇程霄的那天,大雨傾盆 路上行人匆匆,眉眼凌厲的少年靠在小巷的檐下看雨,指尖燃著一截猩紅 聽見巷子口的腳步聲,他抬眼,目光里還橫著一抹打完架后未散的狠戾 阮糖望進那雙眼里,倏地握緊傘柄,惶惶垂下眼 她貼著墻根快步走,心里默念著阿彌陀佛…… 快走快走,這人好兇的樣子 小巷狹窄,她被沒帶傘急急跑過的路人撞了一下,踉蹌著差點摔倒 卻不敢停留,跌跌撞撞撐著傘跑了 離開時似乎還聽見后頭極輕的一聲笑 程霄看著已經躥出巷子的嬌小背影和那兩條被晃起來的長辮子,覺得這姑娘好像只受了驚的小羊 嗯,小綿羊,還綁辮子的那種 2 阮糖沒想到還會見到那個在雨巷里兇神惡煞的少年 這次他是她的后桌…… 從此,她小心翼翼,連椅子都不敢往他桌前哪怕輕輕一靠 程霄看著姑娘恨不得離他八百米的模樣,指尖轉著筆,莫名勾了勾唇 直到有天,他看見姑娘去向數學滿分的學委請教題目 她認真又軟和,看著人的神情很專注 程霄垂眼,抿直唇角,捏彎了手里的可樂罐 深冬傍晚,積雪皚皚的臺階上,男生將女生困在懷里,替她擋掉凜冽的風 呼吸間,她身上軟甜的香清晰可聞 程霄聲音低啞,指尖輕觸她的臉: “以后數學不問別人,來問我,好不好?” 女生眨了眨眼,細聲細氣:“可是,你的數學都沒及格……” 3 后來的某日,3班的班主任拿著一張措不及防出現的滿分試卷老淚縱橫 “程霄同學,是什麼讓你轉了性?” 程霄:“沒什麼,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給同學輔導功課。” 班主任:? 程霄斂眸,目光落在手腕的那根紅繩上—— 滿分而已,他也能考 「只要你喜歡,我也可以」
29.6萬字8 13519 -
完結174 章

重生後孕吐:殘疾大佬心疼哄到哭
【病嬌殘疾大佬vs撩哄嬌軟甜妻 打臉虐渣 高甜孕寵 HE 雙潔 救贖】上一世,秋苒在被軟禁時生下了一對龍鳳胎,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就被閨蜜用一把火活活燒死。死後成為魂魄,她看見那個曾經厭惡至極的男人,在幫她手刃仇人後,於她墳前自戕。重來一世,秋苒誓要手撕渣男賤女,保護好自己的一對兒女,將那個偏執狠戾的男人寵上天。結果某位大佬不認賬了。秋苒挺著孕肚,抹著不存在的眼淚,“老公,你怎麼能把人家肚子搞大後就不負責了?”男人的手撫摸著她的小腹,眼中閃著危險的光:“苒苒,我已經給過你離開我的機會了。”龍鳳胎兩歲時,秋苒看著兩條杠的驗孕棒一頭黑線……世人都說,顧家家主心狠手辣,睚眥必報,對家人精於算計,注定要孤獨終老一輩子。秋苒冷笑,那她偏要給他生好多孩子,再同他白頭偕老,狠狠打那些人的臉。更有人說秋苒是廢柴一個,和那個顧鬱殘廢剛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可最後她卻成了世界級珠寶設計師,每個富婆排隊走後門也要訂她的高奢珠寶。不到一年,顧家不僅多了對呱呱墜地的龍鳳胎,連那個隻能坐輪椅出門的男人都能把老婆扛在肩上。眾人皆歎:原來秋苒是個小福星!
35.5萬字8 52510 -
連載994 章

人潮洶涌
周稚京終于如愿以償找到了最合適的金龜,成功擠進了海荊市的上流圈。然,訂婚第二天,她做了個噩夢。夢里陳宗辭坐在黑色皮質沙發上,低眸無聲睥睨著她。驟然驚醒的那一瞬,噩夢成真。陳宗辭出現在她廉價的出租房內,俯視著她,“想嫁?來求我。”……他許她利用,算計,借由他拿到好處;許她在他面前作怪,賣弄,無法無天。唯獨不許她,對除他以外的人,動任何心思。……讓神明作惡只需要兩步掏出真心,狠狠丟棄。
175.2萬字8.18 3299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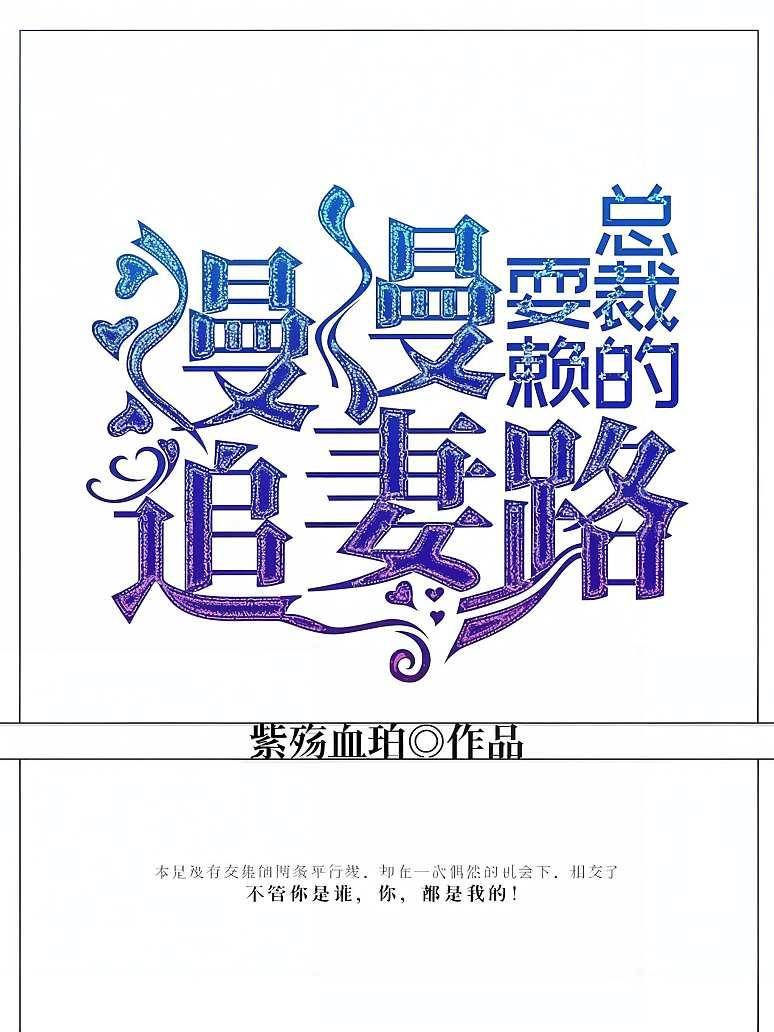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