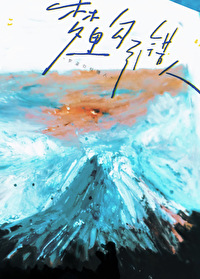《離婚冷靜期?鹿小姐上訴凈身出戶》 第1卷 第3章 我們離婚吧
直到躺進溫暖的被窩里,聽著窗外淅瀝瀝的雨聲,鹿晚星依然心緒很。
一個小時前,溫硯禮將送回了家,下車前他將他的名片給了。
他笑著說:“鹿小姐,如果想通了,隨時可以給我打電話,詳談我們之間的易。”
鹿晚星打開床頭臺燈,拾起床頭柜上的那張名片,目定格在‘溫硯禮’三個字上,臉凝重,糾結。
耳邊不停回響著溫硯禮在公站牌下跟說的話。
——有沒有一種可能,我圖你。
——鹿小姐,我,圖你。
確定跟溫硯禮真的不,也不會自到覺得溫硯禮對一見鐘。
溫硯禮這樣優秀的男人,邊是不缺人的,可他卻說圖這個有夫之婦,這太奇怪了。
鹿家在京都上流圈子里只能算個小豪門,跟溫家這種頂級財閥權貴之家比起來,本不流,溫硯禮不能在鹿家撈到任何好。
他為什麼要幫鹿家,為什麼要跟做這個虧本易?
難道,他的目標是……季家?
鹿晚星心如麻,氣悶地將臉蒙進被子里,雙踢了被子好幾下。
有沒有什麼高科技,能讓直接鉆進溫硯禮的腦子里,看看他到底要圖什麼啊。
想著想著,不知不覺睡著了。
翌日清晨,鬧鐘準八點響起。
鹿晚星迷迷糊糊醒來,掌心下意識落在旁邊的枕頭上。
枕頭冰冷無溫,季司予整夜都沒回來。
呼吸短促地疼了一下,收斂負面緒,翻下床,進了浴室洗漱。
鹿家一堆棘手的麻煩事等著去理,現在沒工夫去想季司予的事。
幸好昨晚回來之后,洗了個熱水澡又提前吃了冒藥,沒有因為淋雨到不適。
等換上出門裝下樓,保姆張媽正端著剛做好的早飯從廚房里出來。
Advertisement
“,早上好啊。”
“張媽早上好。”
走到飯廳的玻璃缸前,拿出魚食,撒了點在水面上。
魚缸里只養了一條魚,是一條很漂亮的五花琉金,但因為魚缸太大,五花琉金顯得孤零零的。
看到五花琉金乖乖游到水面上吃投喂的魚食,心里一陣五味雜陳。
都說魚只有七秒鐘的記憶,所以季司予對的,也這麼短暫嗎?
張媽端上最后一道早餐。
鹿晚星走過去,拉開餐椅,坐下就開始吃。
張媽驚呆了,“你?!你不等等爺的?”
鹿晚星眼都沒抬,“難道他不回來,我就要著肚子等他一上午?”
“可是……”張媽很不理解,“你以前不都要等爺一起吃嗎,如果爺不回來,就會讓我把早飯打包好,你帶到財團去給爺吃。”
鹿晚星拿著粥勺的手一頓。
因為醫生囑咐過,季司予手后的日常營養一定要跟上,所以總是擔心他忙于公務而忽略吃飯。
可是上次,季司予當著的面,將飯盒扔進了垃圾桶。
還當著下屬的面,訓了一頓,說應該把心思都放在事業上,整這些花里胡哨,為此跟他大吵一架。
思緒回籠,鹿晚星自嘲一笑,“以前犯蠢,以后不會了,他吃不吃。”
這幾年,把季司予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他勝過自己。
以后,要學著多自己一點。
張媽還在說:“爺一整晚都沒回來,估計還在財團通宵加班呢,他那麼辛苦,就應該多心疼他的。”
“張媽這麼會心疼他,不如這個讓你來當?”
張媽噎了一下,臉上臊得慌,“我說這些還不是為了你和爺好,何苦對我怪氣。”
鹿晚星懶得再理,專心吃飯。
Advertisement
沒兩分鐘,大門的電子鎖傳來聲響,是季司予回來了。
“爺回來得剛剛好,早餐都還熱著呢。”張媽殷勤地跑進廚房,給季司予盛好粥,臉上堆滿笑。
季司予“嗯”了聲,拉開鹿晚星對面的餐椅坐下,將滿桌早餐掃視一眼后,拾起筷子開始吃飯。
他似乎很疲憊,一言不發的吃飯,不曾看桌對面的鹿晚星一眼。
鹿晚星卻忍不住抬頭去瞧他,瞧見了他眼下的一圈黑青和眼底的紅,雖然并未影響那張臉的值。
他僅僅是坐在那兒,慢條斯理的吃著飯,舉手投足間都是極致的貴氣。
但此刻的鹿晚星無暇欣賞他的,幽幽道:“最近財團是有什麼我不知道的新項目嗎,居然能讓你忙得通宵不回家。”
季司予好似沒聽出話里的怪氣,又“嗯”了一聲,淡定喝粥。
險些氣笑了。
這是他第一次對撒謊。
“看不出來,季總這麼厲害。”
勾冷諷,“跟初人在酒吧通宵喝酒,也能算是財團項目,不知道慕小姐一晚上賞你幾個億啊?”
季司予眸微掀,目不經意跟匯一秒,很快便淡漠地瞥向別。
“可剛回國,池良那幾個二貨吵著要老朋友之間聚聚,男男十幾個,不是跟單獨喝酒,沒告訴你是不想讓你誤會。”
明明被當面拆穿了謊言和敷衍,他卻毫不心虛,解釋得云淡風輕。
鹿晚星放下粥勺,連帶著食都減退了幾分。
“如果你們之間清清白白,坦坦,就不怕被人誤會,越是怕誤會,越說明你心里有鬼。”
嘭地一聲,筷子被季司予重重擱在桌上。
飯廳里的氣氛陡然變得嚴峻,站在一旁的張媽察覺到季司予生氣了,趕忙說:“,爺才剛回來,你就說兩句吧。”
Advertisement
鹿晚星冷笑:“我說錯什麼了嗎,難道不是他自己心虛嗎。”
“這……”
張媽將兩人分別看了一眼,別人夫妻吵架,也幫不上什麼忙,只能說:“昨夜下了一整晚的雨,外頭小花園全是落葉,我去掃掃。”
等張媽一走,飯廳反而變得安靜了。
季司予沒有反駁剛才的話,臉微沉。
一時間餐桌上只有碗筷的聲響。
眼見鹿晚星那碗粥快見了底,季司予終于開口了:“你昨晚說有急事找我,什麼事?”
鹿晚星一愣,還是決定再為鹿家爭取一下。
如果季司予肯幫,就不用冒著未知的風險去跟外人易。
說話的態度溫和不,“我爸被抓了,說他涉嫌稅稅等多項違法行為,如果不能替他翻案,他很有可能要去坐牢,這事你知道嗎?”
季司予淡定如斯,“好幾天前的事,我自然是知道的。”
“你知道?”鹿晚星呼吸一,眼圈霎時紅了,“所以,你從一開始就打算要袖手旁觀,是嗎?”
季司予取來紙巾,矜然。
談論正事的時候,他沒有了昨晚吊兒郎當的懶散態度,條理清晰道:“你爸他為人事不夠圓,墨守規,獨斷獨裁,本就不適合混跡商界,這些年他明里暗里得罪了不人,這次的事,算他活該。”
鹿晚星驚住,“你說什麼!”
他狹長的眸微垂,沒有去看鹿晚星的表,也沒有過多解釋,“以后你娘家的事,你摻和。”
鹿晚星呼吸一滯,不可置信的看著他,“你這是要我放棄鹿家?”
他不說話。
在鹿晚星看來,他這是默認的意思。
當初季司予出事,季氏財團也一度被推向風口浪尖,市暴跌,從沒考慮過退。
被季爺爺帶進財團職后,憑自己的實力在季氏混到如今的副總裁位置,替當時癡傻的季司予穩住了財團執行權。
一直以來都跟季司予、季氏財團共進退。
而在季司予眼里,鹿家似乎可有可無。
他本沒把鹿家當回事,也沒把當回事,所以父親的遭遇并不值得他為此付出太多心力。
“你太讓我失了。”
昨晚的事讓那樣難過,此刻季司予的態度,更讓覺得絕和扎心。
“季司予,我們離婚吧。”
猜你喜歡
-
完結2431 章
強勢寵愛:大叔染指小甜心
訂婚宴上,未婚夫偷吃被抓,她卻轉身被他扣入懷中世人眼中的秦三爺,冷酷,狠絕,不近女色傳聞他身有隱疾,也有人說他曾經被情所傷她卻知道,這個道貌岸然的男人哪是什麼不近女色,而是實打實的衣冠禽獸。
429.9萬字8 103363 -
完結593 章

美人有毒:顧先生別亂來
黎安安死了,被渣男的“初戀”,自己的親表姐逼死在了手術臺上,一尸兩命。 天可憐見,讓她重活一世。 這一世,她會惜命,會乖乖的待在愛護她的親人身邊,護他們周全。 上輩子,那些害了她的人,她要一筆一筆的跟他們清算!
112.7萬字8 95275 -
完結586 章

八零暖婚成為前夫的心尖寵
【雙潔 雙重生 先婚後愛 甜寵為主 撩夫 發家致富 基建】 夏傾沅上輩子直到死的時候,才知道沈奕舟那麼愛她。 重生歸來,她告訴自己,一定要好好補償沈奕舟。 可是,這輩子,他卻撩不動了。 於是,夏傾沅每天要做的事情又多了一樣:把沈奕舟拐上床。 她使勁十八般武藝,狗男人連眼皮都不曾抬一下。 她把心一橫,穿上自製的熱辣睡衣,嬌聲問他:“奕舟,你看我這衣服好看嗎? “ 沈奕舟的喉嚨上下滑動,眼睫輕抬,目光如勾:”來,床上說。 ”
103.7萬字8 44400 -
完結45 章

煙雨故人來
由生菜原創小說《最愛的還是你》講述:秦薇遇到了五年不見的前男友周夜白,還成了她的上司。不久後她不斷的會收到騷擾信息,而自己的男友居然出軌了閨蜜,在她生活一團糟的時候,還跟一個帶著麵具的陌生男子上了床,後來秦薇才知道這個人就是周夜白。 …
4.5萬字8 16763 -
完結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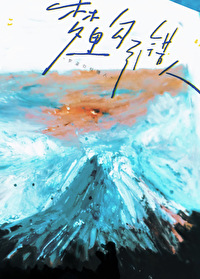
夢裏撩錯了前任的眼盲弟弟[救贖]
你是我假意裏的唯一真心。”雙向救贖!!!1鄭相宜擁有“控夢”的能力,得知前網戀對象家世顯赫後,她決定在夢中接近他。出乎意料的是,前任的夢裏是一片虛無。鄭相宜在夢裏引誘“前任”,少年在她指尖挑動下呼吸也變得急促。她喊前任的名字,沒有看到少年悄悄攥緊的拳頭。後來,鄭相宜得知自己一直以來進入的都是盲眼少年陶時安的夢。她入錯夢了。盲眼少年是前任的弟弟,家世優越,長相俊美,溫柔體貼,已經喜歡上了她。鄭相宜沒覺得愧疚,反倒很開心——“這下更好騙了。”陶時安是個瞎子,看不到她臉上的胎記,也看不到她藏在微笑背後的心。2鄭相宜一直在騙陶時安的愛和錢。陶時安溫柔又克制,得知真相後心甘情願為愛折腰。他真的是個很善良的好人,仍捧著真心告訴她:我都知道,我不怪你。等你媽媽同意我們就結婚。鄭相宜拒絕了,并提出了分手。在大雪紛飛的冬季,陶時安固執地拉住她不肯放手,紅著眼反複問著為什麽。“你是個……內容標簽:豪門世家 天之驕子 都市異聞 治愈 美強慘 救贖其它:眼盲
11.5萬字8 1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