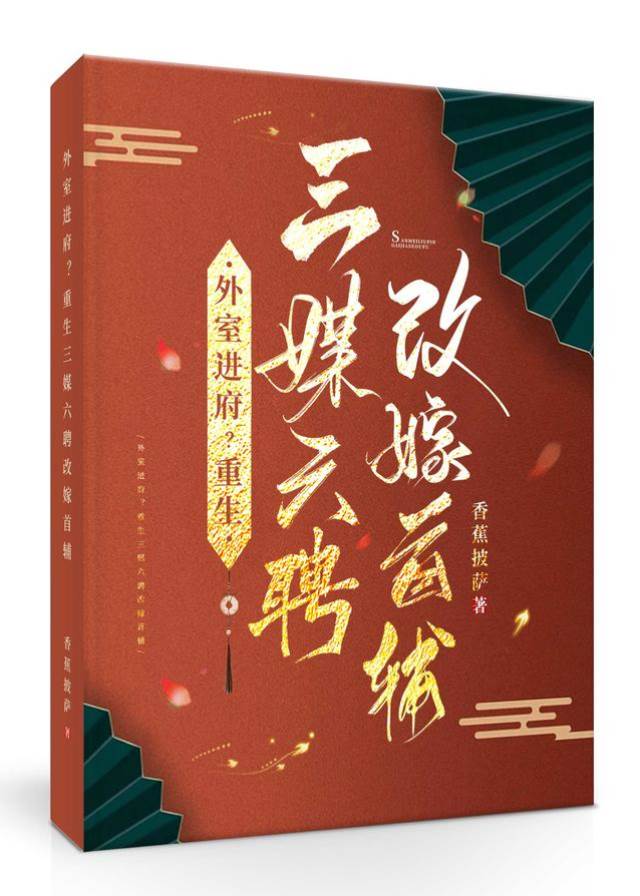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質子三年萬人嫌,歸來三月奪皇權》 第1卷 第8章 再無親人
昭武帝軀高大,容貌端正英武,眉眼間是多年帝王生涯積攢的威,令人而生畏。
他看著坐在一旁椅子上的郁棠,這個前往東瀾三年,而今剛回來就鬧出如此大靜的兒,眼底的震怒幾乎掩飾不住。
“郁棠,你太放肆了。”他語調沉沉,“不管你跟裴修竹之間發生了什麼,如今你已嫁作裴家婦,夫妻之間的事就該待在家里自己解決,非要鬧得這麼興師眾?你把皇族面置于何地?”
郁棠瞇眼看著昭武帝,似是覺得不可思議:“裴修竹新婚夜陷害公主,帶人捉,才是真正將皇族面踐踏在腳下,父皇不置他,反而責怪我將事鬧大?”
昭武帝噎了噎:“事尚未查清,若他是人蠱——”
“自古以來維護婿勝過兒的皇帝可真不多見。”郁棠輕輕笑了一聲,笑意莫名讓人覺得諷刺,“看來裴修竹確實是父皇最寵的臣子,這份寵已經超越了父子之。”
郁棠挑眉看著他:“只是不知有沒有超越夫妻之?”
Advertisement
“你放肆!”昭武帝三步并作兩步走上前,抬手就往臉上扇去,“簡直大逆不道,無法無天!”
“父皇。”郁棠面無表地看著他,“我懷了東瀾攝政王的孩子。”
昭武帝的手僵在半空:“你說什麼?”
“兒臣懷了東瀾攝政王的孩子。”郁棠平靜地重復一遍,隨即輕笑,“并且兒臣回來之前,他給我安排了一百暗衛,個個都是訓練有素以一敵百的頂尖高手。父皇但凡敢我一下,即刻就有人把消息傳到東瀾去,隨之而來的或許就是重兵境,兒臣為質三年爭取來的和平將瞬間毀于一旦。”
昭武帝的臉剎那間鐵青:“你懷了仇敵的孩子?”
“父皇應該想到這個結果的。”郁棠淡淡一笑,笑意著無盡的嘲諷,“您送兒去做質子的時候就該想到,子是會有孕的。”
“你——”
“兒一個弱子,去到千里之外的東瀾,沒有足夠自保的能力,誰想辱都能辱一頓。”郁棠聲音冷冷,“兒臣只是在被多人辱和一人辱之中,選擇了被一人辱而已,這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嗎?”
Advertisement
昭武帝氣得渾發抖。
他生氣的原因不是郁棠懷孕,也不是郁棠在東瀾遭遇過什麼,而是此時跟他說話的態度。
他是一國之君,從沒有人可以如此跟他說話。
他很生氣。
他想命滾出去,回裴家閉門思過,以后只能做一個賢妻良母,別再興風作浪。
一個做了質子又失去清白的子,還指男人對死心塌地嗎?
何況還懷了死敵的孩子……
東瀾攝政王的孩子?
昭武帝表冷得可怕,看著郁棠的眼神不像是看自己的兒,更像是看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
“三年前我以為自己去東瀾為質,是為殷朝爭取和平,是犧牲自己換來百姓免戰之苦,是在立一個跟將軍打勝仗不相上下的功勞。”郁棠角微揚,自嘲地笑了笑,“回來之后我才發現自己錯了,大錯特錯!將軍打勝仗是功勛,我去為質是恥辱,活該被人看不起。沒有人記得是我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他們只記得我是個殘花敗柳,是個東瀾人辱過的公主。”
Advertisement
“他們用那種陌生而鄙夷的眼神看著我。”
“父皇,就連你和太后,看兒臣的眼神都跟三年前不一樣了。”
郁棠緩緩站起,聲音冷得沒有毫波:“兒臣算是看清了所謂親人的臉,所謂夫君的品……從今以后,兒臣眼中再無親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44 章
海棠閒妻
穿越了,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翻雲覆雨的本事,只想平平靜靜過她的懶日子,當個名符其實的閒妻.然而命運卻不給她這樣的機會,爲了兒子,爲了老公,閒妻也可以變成賢妻!家長裡短,親友是非,統統放馬過來,待我接招搞定,一切盡在掌握.
33.5萬字8 24418 -
完結528 章

快穿之太子再虐你一遍
天界的太子殿下生性風流,沾花惹草,天帝一怒之下,將他貶下凡塵,輪回九世,受斷情絕愛之苦。左司命表示:皇太子的命簿…難寫!可憐那小司靈被當作擋箭牌推了出去,夏顏歎息:“虐太子我不敢……”她隻能對自己下狠手,擋箭,跳崖,挖心,換眼……夏顏的原則就是虐他一千,自毀八百!回到天宮之後……夏顏可憐巴巴的說:“太子殿下看我這麽慘的份上,您饒了我吧!”太子:“嗬嗬,你拋棄了孤幾次?”眾人:太子不渣,他愛一個人能愛到骨子裏。
92.1萬字8 11419 -
完結227 章

戀愛腦暴君的白月光
“你爲什麼不對我笑了?” 想捧起她的嬌靨,細吻千萬遍。 天子忌憚謝家兵權,以郡主婚事遮掩栽贓謝家忤逆謀反,誅殺謝家滿門。 謝觀從屍身血海里爬出來,又揮兵而上,踏平皇宮飲恨。 從此再無鮮衣怒馬謝七郎,只有暴厲恣睢的新帝。 如今前朝郡主坐在輪椅上,被獻給新帝解恨。 謝觀睥着沈聆妤的腿,冷笑:“報應。” 人人都以爲她落在新帝手中必是被虐殺的下場,屬下諂媚提議:“剝了人皮給陛下做墊腳毯如何?” 謝觀掀了掀眼皮瞥過來,懶散帶笑:“你要剝皇后的人皮?” 沈聆妤對謝觀而言,是曾經的白月光,也是如今泣血的硃砂痣。 無人知曉,他曾站在陰影裏,瘋癡地愛着她。
35.1萬字8 491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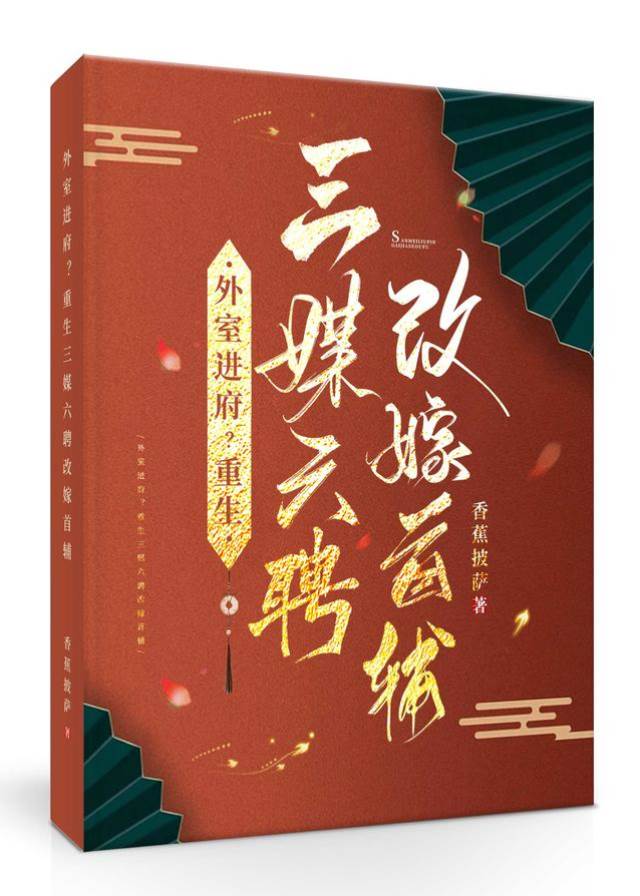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