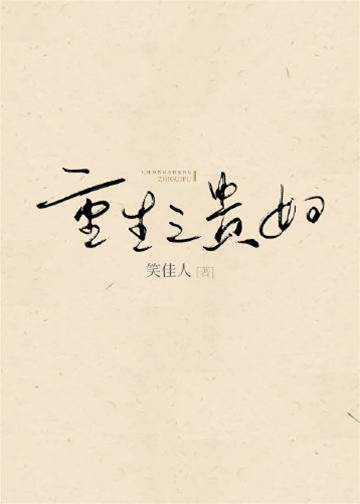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醉京棠》 第1卷 第1章 針鋒相對
建寧十年,秋初。
陛下大病初愈,立儲君,朝中群派林立,波譎云詭。
————
浮云卷靄,明月流。
滄靈山外,寒肅殺,劍影如風,銀刃尾梢滴落刺目鮮,濃郁的腥味充斥鼻息。
朦朧輕煙浮于匝竹林,地上橫七豎八的尸全然一劍斃命。
“難為你們從蘭月國追殺我至此。”說出此話的子嫣嫣含笑,凝著最后一個亡命之徒,細看那致眼眸,卻浸滿森寒。
“妖,你殺害我蘭月太師,罪不容誅。”為首的黑男人雙劍握,正準備殊死一搏。
云婧棠眉梢輕挑,劍鋒側過,不給人半反應時間,一刀抹頸。
鮮紅從劍往下垂落,正值秋初,落葉橫飛,沾染上濺起的,逐漸干涸……
弦月高掛蒼穹,滄靈山山腰,雅致的小院落中,隔間水霧繚繞。
“蘭月那批殺手還真是難纏,我們都回到東靈了竟還在追殺。”
一青侍站自浴桶邊,用潤的帕輕輕拭掉云婧棠下頜水漬。
“我在鬧市公然刺殺了他們的太師,對這些死士而言是莫大的恥辱,追殺我是應該的。”
“不過是一群廢,不足為懼。”
人腔調端的是漫不經心,淺淺抬起手臂,幾瓣紅艷的玫瑰依附其上,紅與白,極致惹眼。
花月貌,玉骨冰,實在無可挑剔,疏影燭火在睫羽落下一層影,誰能料想,看著如此溫的子,竟殺人不眨眼。
“明日回京,不得將我前往蘭月國的消息出去。”
“是。”
翌日,天朗氣清。
低調奢華的馬車沿著京畿道緩慢前行,四角飛檐懸掛的風鈴吊穗飄搖輕,風聲簫簫,倒是掩蓋住詭異靜。
Advertisement
路過昨日清晨殺人的地界,吆喝馬兒的車夫長吁一聲,迫使馬車停頓。
“小姐,出了些意外況。”
云婧棠緩慢掀開車窗云簾,瞧地上橫七豎八的尸已然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攔路的一眾黑侍衛。
誰的作這般快?
裝得一副無辜模樣,蛾眉淡淡蹙起,伴隨侍掀開馬車門簾,又端正坐在主位上,直視前方。
敏銳目不經察覺地掠過為首黑侍衛佩劍上的黑吊穗,聲音溫和問道。
“這是怎麼了?”
秦昳注意到馬車左檐伴著吊穗搖晃的玉牌上鐫刻著赫然醒目的“云”字,目醞著疑,這就是那位久居京郊修養子的云小姐,殿下的未婚妻?
“云小姐近日還是待在京城比較安全,京郊多險。”秦昳并未太多況,只持劍彎腰行了將禮,揮手命擋路的侍衛全部散開。
“多謝提醒。”云婧棠手里攥著巾,掩輕咳兩聲,琳瑯趕將門簾放下。
馬車車緩緩軋過地上半干涸的暗紅,視線收回的那一瞬間,眼底的溫婉消失殆盡。
“寧王回京了?”
“昨兒剛回,聽說在剿滅山匪的時候了傷,陛下派太醫院的季太醫留在寧王府照看。”琳瑯守在側位,一一答復。
云婧棠手肘撐在小桌,閉目養神:“他作倒是快,剛回京便馬不停蹄開始查潛東靈的蘭月死士。”
“傷了?要是能昏迷個一年半載最好。”
現在最焦惱的便是陛下賜的那一紙婚約。
琳瑯默默嘀咕,補充一句:“小姐,聽說寧王殿下只是了點兒皮外傷,季太醫要是跑得慢,估計傷口都快愈合了。”
寧王君硯璟,威名在外,臭名也昭著。
他戰功赫赫,兩年前率領黑鷹軍連奪蘭月三座城池,救東靈于水火中,因此,陛下在他未及冠之時便破例封他為寧王,賜虎符,掌東靈二十萬大軍。
Advertisement
不過君硯璟格晴不定,殺人于市井已是常有的事,如今二十有一,陛下也曾賜他妾,卻全部患了怪病,藥石無醫,不出三日就暴斃而亡。
陛下賜封號為“寧”也是警示他安分守己,擁護君王,莫生出篡權奪位的不敬心思。
君硯璟城府極深,陛下早已對他生出防備之心,此番賜婚,看似是平衡各皇子之間的勢力,實際不過是讓做監視拉攏寧王,杜絕他擁兵造反的心思。
這就意味著,必須牢牢抓住寧王的心,讓他徹底忠誠于陛下,又或是監視他的一舉一,若有異常,必要時……
這跟細作有什麼區別?
陛下冷眼旁觀眾皇子之間的斗爭,偶爾暗中推波助瀾,又給自己留足后路,這盤棋,真是妙哉。
不過,即使陛下對國公府極為信賴,也不愿被當作棋子任人控制,分明自己才最重要。
云婧棠思緒之時未注意時辰,再睜眼,馬車已至城關。
“督尉大人,您看這輛馬車轂有。”
“來人,給我攔下!”守城門的陳督尉揮手之間,數十位士兵將馬車團團圍住。
寧王有令嚴查京之人,他若是抓住疑犯,定能去邀功。
“小姐,是寧王殿下的人。”馬車外穿著便的侍衛站在窗口低語,此刻,已經有士兵上前收走他的佩劍。
云婧棠玉手拂過紗簾,稍側眸,眉目間蘊著幾分憂愁,像是真的不舒服:“陳都尉,本小姐不適,只想快些回國公府休息,你當真要攔著?”
這時,陳督尉才注意到馬車前檐掛著的玉牌,著急彎腰行禮以示歉意。
“這就放行,還請云小姐見諒。”
縱然有再多的疑也無濟于事,馬車里那位份擺在那里,豈是他一個督尉敢阻攔的?
Advertisement
攔路的士兵剛離開,一匹披著軍甲的黑駿馬朝城門奔馳,馬蹄疾步之聲促萬分,看清騎馬之人的面貌,眾士兵齊聲朝向城門側恭敬行禮。
“寧王殿下。”
“給本王徹查這輛馬車。”君硯璟居高臨下地看著馬車車窗,聲音冷厲似寒刃在脊,他當然注意到了云國公府的玉牌,不過那又如何?
云婧棠在滄靈山兩月,蘭月國的細作又全部無緣無故喪命于滄靈山,是否是巧合,有待查驗。
在此之前,任何嫌疑人都不得放過。
猜你喜歡
-
完結730 章

太子殿下你被逮捕了
世人皆讚,寧安侯府的四小姐溫婉寧人,聰慧雅正,知書達理,堪稱京城第一貴女,唯有太子殿下知曉她的真麵目,隻想說,那丫頭愛吃醋,愛吃醋,愛吃醋,然後,寵溺他。
134.7萬字8 8508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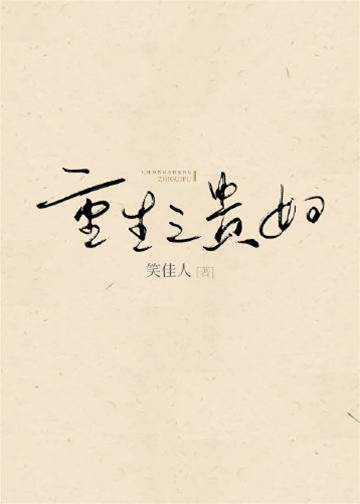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387 章

掌上齊眉
謝雲宴手段雷霆,無情無義,滿朝之人皆是驚懼。他眼裡沒有天子,沒有權貴,而這世上唯有一人能讓他低頭的,就只有蘇家沅娘。 “我家阿沅才色無雙。” “我家阿沅蕙質蘭心。” “我家阿沅是府中珍寶,無人能欺。” …… 蘇錦沅重生時蕭家滿門落罪,未婚夫戰死沙場,將軍府只剩養子謝雲宴。她踩著荊棘護著蕭家,原是想等蕭家重上凌霄那日就安靜離開,卻不想被紅了眼的男人抵在牆頭。 “阿沅,愛給你,命給你,天下都給你,我只要你。”
84.8萬字8 45840 -
完結322 章

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
蘇沉央一遭穿越成了別人的新娘,不知道對方長啥樣就算了,據說那死鬼將軍還是個克妻的!這種時候不跑還留著干嘛?被克死嗎?“啟稟將軍,夫人跑了!”“抓回來。”過了數月。“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抓回來。算了,還是我去吧!”…
86.3萬字8 86025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54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