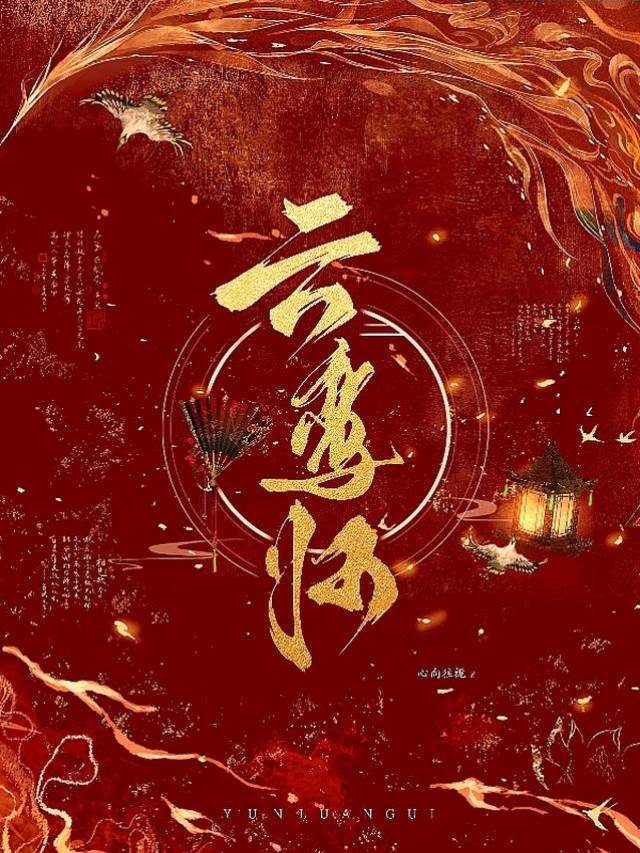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美人多嬌》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浦真買完饅頭,瞧馬車那邊的靜不大對,連忙跑回去,制止住劍拔弩張的兩個人。
“哎呦,明姑娘,陳先生一場誤會,都沒有上錯車!”
來人姓陳單名一個愖,字靜照,年二十三,應天江浦人,是魏欽的好友,魏欽今日便是特地來接他的。
明黛和陳愖兩雙眼睛瞪瞪,誰都沒有開口說話。
浦真把油紙包著的饅頭遞給裏面的明黛:“姐兒趁熱吃。”
明黛接過來,聽到他問陳愖:“大爺見過了約定的時辰您還沒有到,找您去了。您方才去哪兒了?”
陳愖肯定不是剛下船,他們在渡口等著這會兒,只有一只自瓜洲而來的客船停經渡口。
陳愖說:“今日河上風大,客船行得快,我下船看時辰早,就到逛了逛。”
他玩大,浦真都猜到他定是逛著逛著就忘記時辰了,估著魏欽過會兒回來肯定沒有個好臉待他。
陳愖此刻顯然對明黛更加好奇,他的面相閃過興味,長眸微瞇,打量著這個出現魏欽馬車上的姑娘。
明黛正翹著手指撕油紙。
陳愖手執折扇在掌心敲了兩下,“啪”的一聲開扇,扇面描著幾朵雍容豔的牡丹圖,清了清嗓子:“姑娘是……”
他剛一開口,魏欽就回來了,又瞬間噤了聲。
這回是三雙眼睛互相看著。
明黛放下遞到邊的饅頭,指指陳愖,對魏欽說:“你等的人已經來了。”
說著往裏面坐了坐給他騰出位置。
魏欽上車,不不慢地在旁坐下,拿起他用過的茶盅,抿了一口涼茶才看向陳愖:“只這一回。”
陳愖無奈地聳聳肩,看來日後這個免費的腳力是蹭不到了。
他笑著說:“好了,是我誤了時辰,我請你還有這位明姑娘吃酒賠禮。”
Advertisement
“今兒恐怕不行,方才聽人說今日全城都要實行宵,并有衛兵巡城。”跟著魏欽去找人的令威小聲提醒。
既有衛兵巡城,那便不再像以往那般寬松或是本無人管,而是要真格兒的了,過戌初時仍在街上行走一旦被發現,立即抓獲施以笞刑。
從三茅淹渡口趕回木樨街最也要耗費半個時辰,天漸晚,他們恐怕哪裏都去不了了。
陳愖十分失。
“那回去喝姜娘燉的魚湯吧。”明黛說。
魏欽嗯了一聲。
只有陳愖疑姜娘是誰,有些郁悶的是似乎也沒有人願意告訴他,怎麽魏欽回揚州一趟,邊多了許多他沒聽過的人名。
他折扇搖得呼呼作響。
魏欽眼睛也沒朝他那兒擡。
車廂裏只有明黛說話:“幫我倒杯茶。”
這自然是對魏欽說的。
明黛油紙撕得太大,饅頭裏的餡料足,油又多,沒有注意雙手都沾了油,正蹙著細眉,著繡帕手。
魏欽聞言,微微傾,提起茶柄幫添滿茶水,順道把茶盅往手邊輕輕推了推。
陳愖默不作聲地打量著他們,跟著說:“也幫我倒杯茶。”
魏欽奇怪地看他,淡淡地撇了一下他的手。
自己沒有手?
陳愖眼睛睜大了一些,眼神往明黛那邊示意。
魏欽懶得理他。
明黛沒注意他們的眉眼司,端著茶,連著喝了幾口剛添的溫茶才下饅頭的膩味,裏只剩清淡的茶香。
舒服的輕輕的“噯”了一聲,擱在茶盅,滿足地靠在墊上,這才發現陳愖在盯著。
明黛紅紅的瓣抿起來,不高興地瞪了他一眼。
陳愖微微一愣。
*
馬車到達的木樨街的時候,天已深,明黛最後跳下馬車,留在家裏看門的阿福溜到邊:“姐兒你家門口一直有人在敲門,他等了大概有一個半時辰了。”
Advertisement
“一個半時辰?”明黛腳步都沒有站穩,聞言驚訝地問,“現在還沒有走嗎?”
“沒有,半刻鐘前還在呢!”阿福搖搖頭。
“我溜過去從門裏看了一眼,是個和姑娘差不多大的郎君。”
說到這兒,阿福有些不好意思了,臉都紅了,小聲解釋:“這是我第一次在姐兒離家時翻牆過去。”
明黛不在意地擺擺手,提著擺往大門走:“我去瞧瞧。”
“往哪兒走呢?”
一旁的陳愖見裏回家的路竟然是穿過魏欽的家,眼底閃過驚訝。
“回家。”魏欽幽幽地道。
明黛圖方便,就算自己出門路過木樨街時,也常常從他家抄近道,穿過園子直接爬牆回家。
陳愖眉頭深鎖,到疑。……
“姐兒不從外面繞回去嗎?”阿福屁顛屁顛地跟在邊。
明黛才不願意繞那麽一大圈回去,先去看看究竟是誰來找,大不了就說不好意思,睡覺睡昏頭了,沒聽到敲門聲,實在抱歉。
阿福嘰嘰喳喳的說個不停:“哪有人這會兒睡覺的。”
只有他剛出生的小弟弟才會從中午一直睡到晚上。
明黛一臉這還不簡單的模樣,捂著心口蹙眉佯咳了兩聲,眸狡黠:“生病總行了吧!”
阿福被逗笑。
明黛眉眼彎彎,不過很快就笑不出來了。
過門看到裴二郎神焦急地站在門外。
明黛猶豫了片刻,推推阿福:“你先進去躲躲。”
等阿福藏起來了,閉了閉眼睛,深吸一口氣,拉開大門。
裴子京的手臂懸在空中,甚至都沒有反應過來,差點兒就沒有來得及收手砸到明黛臉上,他放下手臂,疲憊的臉上浮現驚喜:“嘉因,你在家啊!”
嘉因是明黛十五歲及笄時甄家的一位老姑為取的字。
Advertisement
“你方才沒聽……”裴子京頓了頓,改口溫地笑著說,“你剛剛肯定在家睡覺吧?”
明黛沒有回答,將他擋在門檻之外,反問道:“你來找我做什麽?”
“我前些日子隨父親去了趟濟南,昨日回揚州,今早才聽說你的事。”裴子京似乎生怕明黛誤會,認真地解釋道。
“我知道後立刻就來找你了,還有……我可以進去說嗎?”
他邊一個小廝都沒有,估著是跑出來的,明黛沒有耐心,忍不住“嘖”了一聲。
裴子京只好待在門口,猶豫著還是說出口:“嘉因你放心,我只會與你定親。”
明黛看了一眼他的後,他在家門口待了一個時辰肯定早就引起別人的注意了,愈發煩悶,側:“你進來吧。”
裴子京暗松一口氣,跟著走進屋。
但很快一盆冷水將他的熱澆滅。
明黛黑白分明的眼眸直視著他:“裴二郎君,可是我不想與你定親。”
“這怎麽會?你一定還在生我氣對不對?我母親說的那些話都不是當真的,不是誠心說你,說你……,”裴子想要為他母親解釋,可那些難以啓齒的話他說不出口,他忍不住流出挫敗的神。
院子裏一片寂然,明黛冷眼看著他。
裴子京緩了一口氣,認真地說,“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地勸,讓來找你道歉。”
明黛飛快地打斷他的話:“夠了。”
“裴子京你別天真了,你母親不會喜歡我,我也不喜歡,所以我們永遠都不會在一起,聽懂了嗎?”
裴子京不吭聲。
明黛不吃這一套,忍著不快,立刻下了逐客令:“你要是沒有別的什麽事,快回去吧,要宵了。”
擡手指著大門,讓他走,可著裴子京腦海中卻浮現他母親的聲貌,搖搖頭,還是在意,在意的要命。
Advertisement
明黛終究憋住火氣,嘲諷道:“要是被你母親知道,我挨罵的可不僅僅是殘廢兩個字,可能還會有更難聽到話,我聽不得那些,我怕忍不住會打人!”
“所以你最好不要再提了,也最好不要再來找我。”
裴子京回過神來,愣愣地看著,穿著最喜歡的綠,也還是他悉的那張麗飽滿得像花一樣的面龐。打小兒就漂亮,是他見過最漂亮的姑娘,也是他見過脾氣最差的姑娘。
裴子京時就認識明黛,很清楚從來不是個順的姑娘,就像此刻神倔強,眼眸憤怒尖銳,說起話來也毫不客氣。
脾氣上來了,什麽事都做的出來,裴子京不敢再惹生氣。
連忙擺手:“好,好,好,我這就走。”
不過現在天已晚,他趕不回邵伯鎮,他謹慎地說:“嘉因,我就住在前街的會同客棧。”
明黛站在原地沒有說話,直到阿福溜出來:“姑娘。”
明黛偏過頭去:“你回去吧,我不,不吃晚膳了。”
說完便回了屋,猛地拍上了屋門。
阿福幫把大門關好,栓好門閂,又拿椅子堵住才從梯凳翻回去。
“我只聽說什麽定親,什麽道歉之類的……”阿福撓撓頭,他躲在廚房裏聽得不算清楚,只能告訴他們一些自己聽到的話。
“總之,和那位郎君說完話姐兒就有些不開心了。”
“定親?”陳愖俊俏的臉龐閃過驚愕,不知道想到什麽,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話了,這會兒控制不住,難以置信地看著魏欽,“魏欽你不會看上一個有未婚夫的姑娘吧?”
魏欽啓,冷冷地吐出一個字。
“滾!”
猜你喜歡
-
完結480 章

穿書之沒人能比我更懂囂張
––伏?熬夜追劇看小說猝死了,她還記得她臨死前正在看一本小說〖廢材之逆天女戰神〗。––然后她就成了小說里和男女主作對的女反派百里伏?。––這女反派不一樣,她不嫉妒女主也不喜歡男主。她單純的就是看不慣男女主比她囂張,在她面前出風頭。––這個身世背景強大的女反派就這麼和男女主杠上了,劇情發展到中期被看不慣她的女主追隨者害死,在宗門試煉里被推進獸潮死在魔獸口中。––典型的出場華麗結局草率。––然而她穿成了百里伏?,大結局都沒有活到的百里伏?,所以葬身魔獸口腹的是她?噠咩!––系統告訴她,完成任務可以許諾...
86.1萬字8 11706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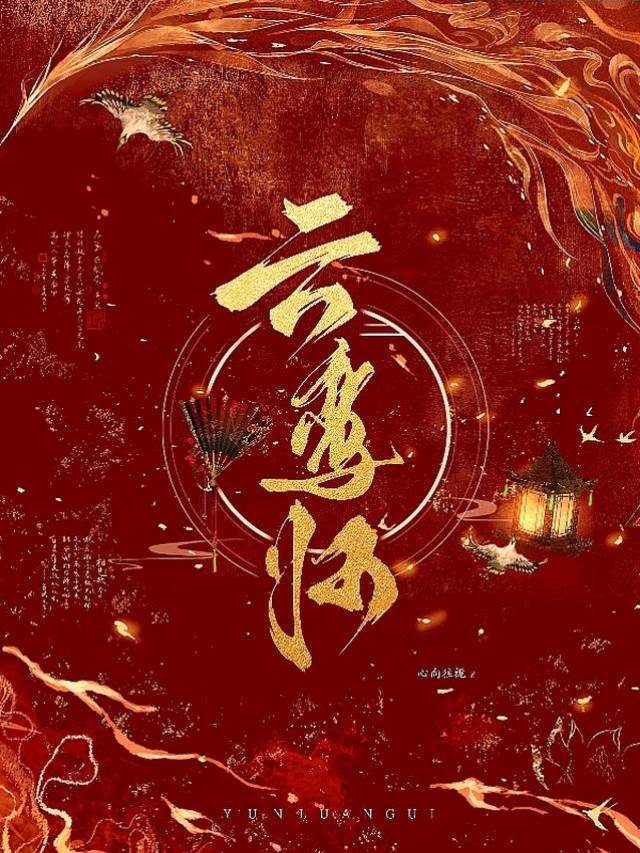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