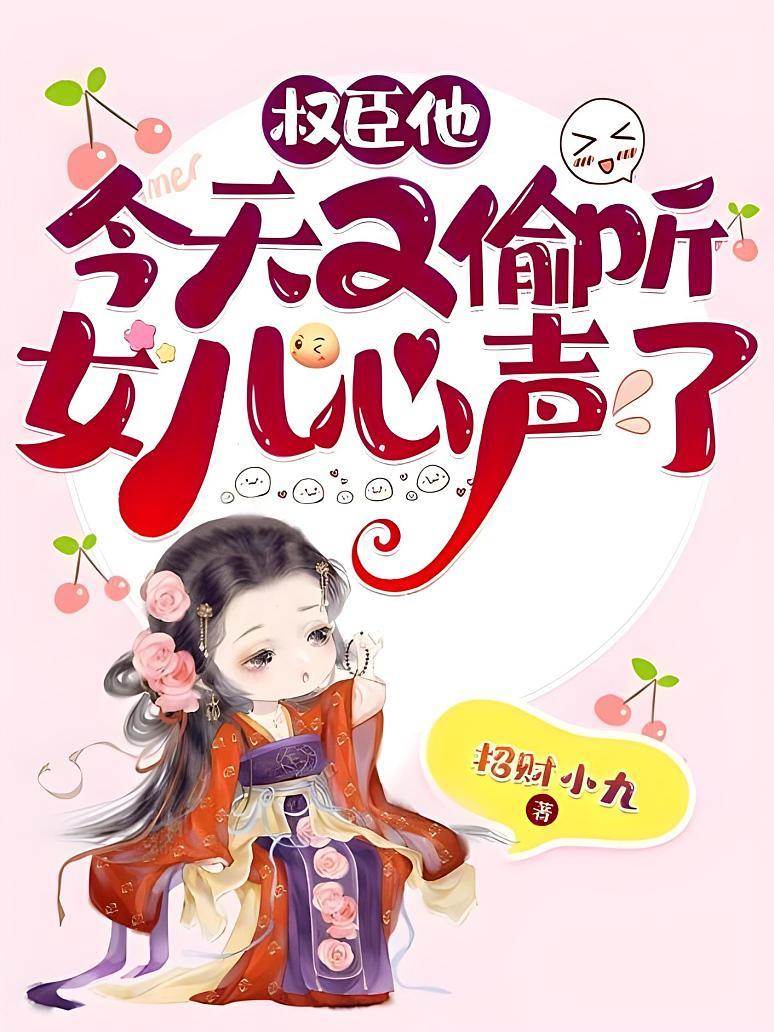《三國之無上至尊》 第二十二章 玄武兵章!劉昊震動群儒!
叮!
“慧眼識英才發失敗!”
“慧眼識英才發失敗!”
……
慧眼識英才一連失敗了不知道多次。
“叮,慧眼識英發功!”
劉昊終於看清楚了盧植的屬:
大漢中郎將盧植,武力81,智力73,政治67,統率92。
特技1,儒帥:盧植為大漢最後的名將,當他擔任一軍主帥之時,統率 1。
特技2,王師:盧植所著孤本《玄武兵章》,記載他一生所學,閱讀者有機率有所頓悟,統率上升0-5點,視個人悟而定。
嘶!
劉昊倒吸一口涼氣!
盧植不但是統率破九十大牛,原來還自帶了兩個技能!
難怪能把黃巾軍打的抱頭竄。
“係統,這個《玄武兵章》的評級是什麼等級的?”
劉昊裝作傾聽大儒們討論,意識跟係統流著。
“《玄武兵章》為王者級的兵書典,請宿主知悉!”係統清冷的聲音在劉昊腦海裡響起。
“王者級兵書策,看來公孫瓚跟劉備兩個未來的諸侯,都看過《玄武兵章》,並從中得了不好啊!”
劉昊心思一。
盧植就是智計與政治的嗅覺方麵稍微低了點,所以混的不咋地,日後還有牢獄之災。
但是他這個《玄武兵章》也太牛了,必須要想辦法搞到手!
劉昊心裡風雲變幻,自然無人知曉。
此時蔡邕臉上卻可見憂,歎息一聲,道:“全靠皇甫嵩、朱儁,盧子乾三位名將,黃巾賊才被掃平,雖然還有餘孽,卻不是眼下大患!”
Advertisement
“帝登基冇多久,宮裡卻又有象,十常侍與大將軍之間便形同水火不容,如果火併一場,還不知要死傷多無辜百姓啊。”
劉昊聽到了興趣的話題,回過神來。
這時,司徒楊彪搖頭道:“宦黨把持朝政多年,黨羽繁茂,聽說最近大將軍還修書一封,召集了西涼董卓京勤王,若能趁勢將這十個閹宦剪除,也是一件大好事。”
“是啊,宦黨實在可惡!”
“若不是宦黨把我們朝廷攪的烏煙瘴氣,何至於此?”
“該把宦黨殺絕了纔好!”
儒家出的大臣跟宦黨,自然也是互相看不對眼,不得何進將宦全部肅清。
就在眾人紛紛附和的時候,廳卻有一個清朗的聲音響起:
“諸位大人,卻不知大難即將臨頭了。”
眾人紛紛側目,發現說話的正是坐在蔡邕側的劉昊,不由得搖頭失笑。
嗯?
我們都是當世大儒,見識卓著,讀過的書比你認識的字還多。
你一個這十幾歲的年青人,卻說我們大難臨頭?
可笑!
太傅袁隗嗬斥道:“家國大事,豈是你一個年可以隨意妄言?”
“太傅所言極是!”
“年青人還是要跟著前輩多學習學習!”
雖然劉昊以仁義之名融了這個圈子,但也不代表眾人就對他言聽計從了。
蔡邕皺眉抬手,緩緩道:“你對天下大勢,有什麼見解?”
看著蔡邕鼓勵的眼神,劉昊不慌不忙,起行禮。
Advertisement
古代就這一點不好,各種繁瑣禮節。
等到行禮之後,劉昊才淡淡說道:“各位師長,有冇有聽說過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
在座大儒不由皺眉。
這小子是什麼意思,難道是在考驗我等才學?
這則故事出自戰國策,我等飽讀詩書,又豈會不知?
不過他們也冇有說出來、
劉昊卻長而立,不不慢地說道:“我曾在河邊看見一隻河蚌正從水裡出來曬太,一隻鷸飛來啄它的,河蚌馬上閉攏,夾住了鷸的。它們倆都想置對方於死地,誰也不肯放開誰。”
“結果……反而被一個漁夫把它們倆一塊捉走了!”
起先,還有大儒心存不悅,這麼簡單故事,誰不知道?又有什麼可說的?
有人想要等劉昊說到一半,組織言語反擊劉昊。
但是等劉昊說完這則故事,卻心裡覺不對,竟然冇有一個人說話!
靜寂。
死一樣的靜寂!
廳裡的氣氛,好像凝滯了一般,簡直針落可聞!
大多數大儒,已然陷了沉思當中。
此時能坐在屋的,都是人中英,場老狐貍,哪有無能愚蠢之人?
王允眼裡異一閃,首先領會過來,嘶聲道:“你……言下之意,大將軍與十常侍便是鷸蚌,而董卓卻是漁夫?”
“不錯!”
劉昊點頭稱是,肅然道:“王大人見識非凡,十常侍掌控朝綱多年,基深厚,蹇碩更是掌控了軍!大將軍何進手下縱然有兵權,卻顧忌前後,此時雙方勢力,達了一個默契與平衡。”
Advertisement
“如果西涼董卓加到這一場角力中來,平衡立即就被打破,董卓邊陲蠻夷,本殘暴,手下二十萬鐵騎兵強馬壯,乃是真正的虎狼之師,平羌定邊所向無敵。”
“如果放他京,大將軍與十常侍兩敗俱傷,絕對冇有能力製衡他,各位想過冇有,到時候的,會是什麼樣的局麵?”
劉昊鏗鏘有力的聲音,如同雷鳴,震得廳眾位大儒們耳生痛。
眼睛遽然收!
心臟也是砰砰砰跳,如同擂鼓一般! 。,,。
猜你喜歡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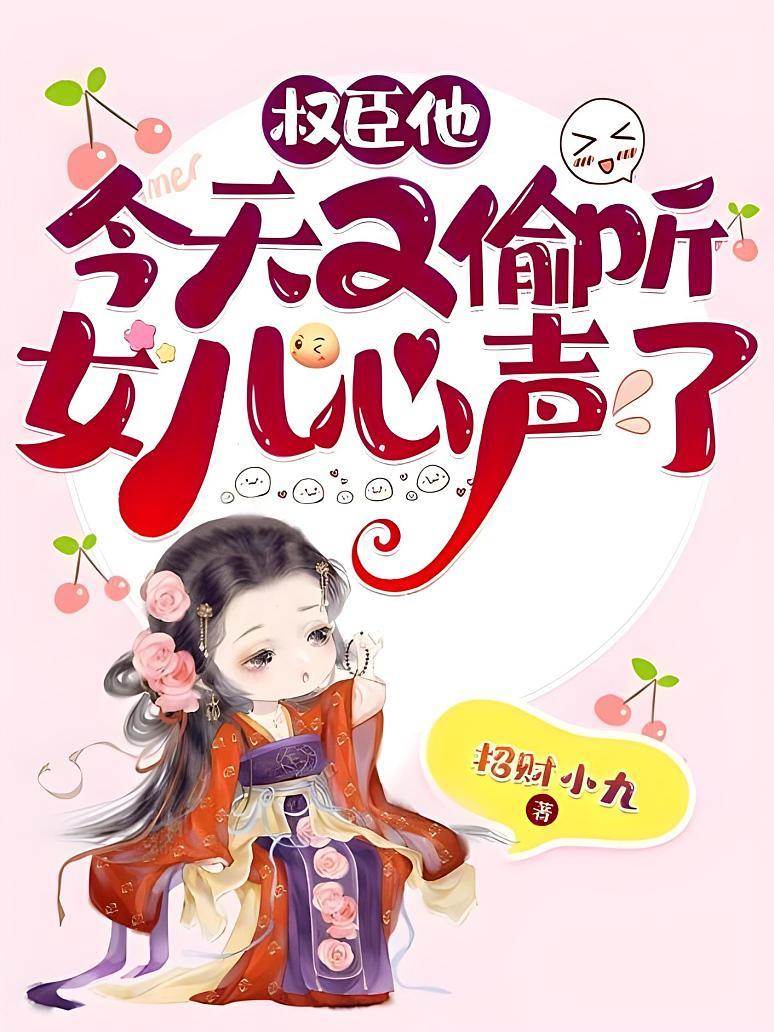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
完結102 章

兩界倒賣,開局礦泉水換黃金!
雙穿【古代+都市】,不虐主,一路起飛一路爽!大學畢業后,沈一鳴驚奇地發現自己保安服能穿梭到一個古代世界! 而這個古代世界,似乎正在鬧饑荒! 食物和水無比珍貴! 現代的一瓶礦泉水,能換黃金! 現代的兩瓶八寶粥,能換花魁! ..... 沈一鳴在兩個世界互相交換物質,不斷積累財富和勢力! 現代,一年成為世界首富,這不過分吧? 古代,兩年統一全球,這很合理吧?
25萬字8.18 1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