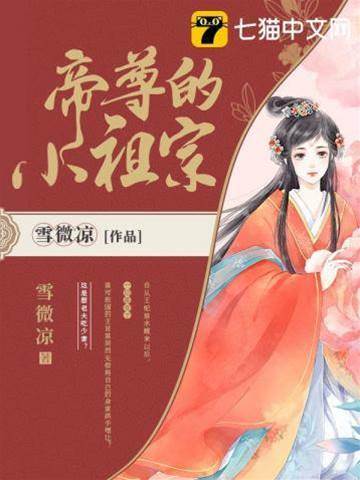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別枝》 第55章
一盞茶的時辰前,宋長訣被抬到云硯軒,李太醫從太醫院匆匆趕來,又是按傷,又是把脈,一番折騰。
隔著兩道珠簾,付茗頌著一白金袍立于前,兩手扣置于腹前,難掩擔憂之。
方才路過宮道時,宋長訣臉慘白,實在可憐。
見如此,遮月寬道:“娘娘,太醫在呢,您不必憂心,無事的。”
正說著,“嘩啦”一聲,李太醫揭開珠簾而來。
付茗頌忙上前兩步,“可是因上回馬蹄踩踏落下的病?”
李太醫心中頗有疑,脈象診斷,這宋大人除了虛一些,并無其他病,可他時不時口疼痛,咳嗽,分明又是有病……
究竟是哪一出了問題?
思此,他眉心擰起,拱手回話道:“應當是如此,從脈象看不易察覺,許是傷及臟。”
李太醫也只能作此解釋。
付茗頌一雙杏眸睜大,抿了抿,“李太醫前陣子診脈,難道未曾發覺宋大人子有異麼?本宮可記得,你說是大好了。”
向來不會說重話,可這話里,責備的意思卻不言而喻。
因而這話一落下,李太醫便匆匆下跪,“微臣疏忽,娘娘責罰。”
一眾宮人低下頭,連呼吸聲都下意識放輕了些。伺候新主子這麼些日子,還未曾見過怒。
須臾,付茗頌和下臉,輕輕道:“起吧,宋大人的子,還李太醫能好生照料。”
李太醫連連應是,退到一邊寫了藥方,吩咐宮人上藥房采藥、煎藥。
—
宋長訣坐于榻上,將外頭的言語一字不落的聽進耳里,在付茗頌道“本宮可記得,你說是大好”時,若有所思的扯了扯角。
李太醫來宋宅診脈,宋長訣回回以病容待之,怎可能大好了?
Advertisement
他抬眼,過珠簾的隙,能模糊瞧見子姣好的側臉,輕輕抿住的……
約有時的影子。
宋長訣起,珠簾又是一聲輕響,年蒼白著一張臉,朝拱手道:“微臣子不濟,幸得娘娘路過。”
付茗頌搖頭,請他坐下:“若非救本宮,宋大人又怎會落下病。”
宋長訣又握拳咳了兩聲:“微臣該做的。”
遮月遞上一杯茶給他,又悄聲退到一旁。
宋長訣斷斷續續說了好些話,大多是在謝付茗頌挑選的宅子,以及請李太醫瞧病這事,不過說兩句咳兩聲,也實在人于心不忍。
遮月常常隨付茗頌去書房,大多時候都在書房門外候著,時不時也聽說過這宋大人的事兒。
聽說是個足智多謀、渾才干之人,但也聽說,是個淡漠冷然之人,現下看來,分明還算和氣。
見他茶盞空了,遮月又上前添滿。
末了,室忽然靜了一瞬。
宋長訣角抿一條直線,輕放在上的手微微握。
他忽然低聲音道:“微臣那日,瞧見娘娘馬前遇難。”
付茗頌不知所以,好奇的抬眼他。
“微臣曾有一家妹,與娘娘有幾分神似,”他抬起臉,“若是還在,如今應當十六了。”
付茗頌一怔,倒是沒料到宋長訣會同說私事,一時間忘了應答。
宋長訣笑笑,復又低下頭,“微臣唐突了。”
“令妹……”付茗頌皺眉,思索措辭。
“時家中起火,死了。”
“咯噔”一聲,付茗頌手中的茶盞手落下,茶水了裳,還愣愣的盯著宋長訣看。
不知宋長訣的話中,哪一個字中心窩,只覺得心口生疼生疼的,緩不過氣,亦說不上話。
Advertisement
“娘娘!”遮月驚呼,忙撿起地上的完好的杯盞,用帕子去上的茶漬。
聞恕來時,便見這兵荒馬中,宋長訣眼神復雜的凝著他面前的姑娘。
驀地,他側眸過來,一臉坦,沒有毫心虛。
—
將至十月的天,清冷蕭索,但宮中到底還是添了不生機的綠植,反添春意。
然而,這一路宮攆而過,不僅未春意,還平白多了冷意。
男人下頷繃,紅抿,眉宇沉沉。
元祿深不好,皇上這分明是了怒。
他頻頻抬眼去瞥皇后,卻見著前方直發愣,半點危險都未察覺。
元祿心下疲憊,悄聲嘆氣。
直至宮攆半道打了個轉,付茗頌才回神,四下一,扭頭問:“不回昭宮麼?”
聞恕眼都未抬,半個字都沒回。
付茗頌早習慣于帝王的喜怒無常,便也未放在心上,只是苦惱的低頭瞥了眼茶水沾的子。
不過片刻,便又出了神。
一路行至景宮,進到室,宮遞上干凈的袍,付茗頌到屏風后頭換上,正轉出去時,遮月輕拉住袖口。
遮月的聲音約莫只有蚊子那般大聲,輕輕道:“娘娘,皇上臉不大對,您小心些。”
付茗頌訝然,點頭應下。
須臾,宮人悄聲退至門外。
付茗頌踩著雙高腳的銀白繡花鞋,走在木質的地上發出一道道清脆的響聲。
這才發覺,方才一路上,聞恕似是沒同說過話。
“皇上?”付茗頌走至他后,輕輕拉了拉男人的袖。
“噔”一聲,聞恕將手中把玩的扳指擱在小幾上,抬頭,角揚起一道滲人的弧度。
他開口道:“私會外臣,朕的皇后可真是好大的膽子。”
Advertisement
付茗頌他一句“私會外臣”砸懵了神,認真道:“一眾宮人,還有李太醫在,怎私會?”
這罪名,哪里是能擔得起的?
聞恕瞇了瞇眼,從座上起,居高臨下的看著:“還會頂了。”
那種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的語氣和神,一貫是付茗頌最怕的。
一下住了,輕輕咬住下,無辜又委屈。
驀地,聞恕笑了。
他上下打量一眼付茗頌剛換上的裳,慢條斯理道:“說什麼了,還將茶打翻了,嗯?”
他說話間,走近了兩步。
不待答,男人掌心已經近腰側,“宋長訣子冷清孤僻,究竟能與你說什麼?”
這下,付茗頌再是溫吞,也明白過來他發的是哪門子的怒火。
但對聞恕口中的“子冷清孤僻”存疑,雖與宋長訣接不多,可幾次下來,除卻覺得他上自帶幾許悲涼,其余給人覺,尚且算的上溫和。
當然,這話付茗頌不敢講。
抬手了男人的側頸,解釋道:“宋大人世可憐,年時便死了妹,許是眉眼與臣妾有些相像,才多說了幾句無關痛的話。”
聞恕一頓,宋長訣,哪里來的妹?
他不聲的捉住的手:“宋長訣親口說的?”
點頭應:“宋大人也是可憐人。”
趁他臉緩和下來,付茗頌指尖輕,在他掌心撓了一下,那討好哄的意味再明顯不過。
如今,已經知道如何給虎順了。
聞恕低頭看,“下不為例。”
他兩手指擒住的下,警告似的在下咬了一下,惹的人溢出幾聲。
待到付茗頌那張小臉他紅,他才肯罷手。
“在這等著。”
Advertisement
他撂下這句話便出了景宮,回到書房后,將暗閣里一摞函底下,有關宋長訣的那疊拿了出來。
仔仔細細過了眼,也沒找到任何有關宋家的蛛馬跡。
忽然,他著紙卷的手輕輕頓住,一種悉的覺戛然而生。
當年,他亦是這般一張張,一卷卷的看過去,不過卻是宋宋的卷宗。
那時他迫切的想要了解的曾經,大多卻只有年后的蹤跡。
有關的年,不過寥寥幾筆帶過。
時隔一世,那些當初看來不重要的名字,只在腦中留下模糊的影子。
聞恕皺眉,究竟是什麼被忽略了?
見他走了神,幾張紙飄至桌腳,元祿輕聲提醒道:“皇上?”
男人恍惚回神,低聲應了聲“嗯”。
末了,他又抬頭道:“宣沈其衡覲見。”
—
九月二十六,正值休沐。
長青街兩旁的樹禿禿的,只剩一地枯黃的落葉,可卻毫不顯冷清。
小攤上熱氣騰騰的煙霧,絡繹不絕的行人,吆喝聲,招呼聲,無論四季如何,這長青街永遠是京城最繁華熱鬧的一。
盛喜樓地長青街正中,恰是最好的地段,加之又有京城第一酒樓的名,幾乎是日日人滿為患。
今日尤甚,朝臣群,最上這盛喜樓來把酒言歡,攀、談八卦,時不時還能換些的消息。
宋長訣被幾位大人圍著灌了幾口酒,一人坐在窗口吹著冷風,清醒了幾分。
沈其衡舉著茶盞過去,“解酒。”
宋長訣睨了眼,并未拒之。
“宋大人初為,可還適應大楚的僚氛圍?”他指的是吃酒這種場合。
“尚可。”
沈其衡點點頭:“也是,令尊也曾為,耳濡目染,宋大人適應的應當比常人要快。”
這時,宋長訣才掀起眸子看他一眼。
“說來慚愧,當初查宋大人的底細,竟是查不出更深的,不過據我所知,宋大人一家三口,與我倒是相同,未曾有兄弟姐妹,年定是有些許無趣吧。”
沈其衡不顯山不水,可每個字都打在節骨眼上。
誰知,宋長訣卻是揚起角,朝他笑道:“那卻不是,我曾有一妹,名喚宋宋,長到八歲那麼大,小小的一團,誰見了都喜歡。”
沈其衡沒料到宋長訣會直言,不由錯愕一瞬,他真有一妹?
可暗探傳回的消息,并未提及這點,難不是了線索?
不知是不是飲了酒的緣故,宋長訣難得多了兩句話。
“可惜一場大火,我沒能護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747 章

鬼面梟王:爆寵天才小萌妃
一道圣旨,家族算計,甜萌的她遇上高冷的他,成了他的小王妃,人人都道,西軒國英王丑顏駭人,冷血殘暴,笑她誤入虎口,性命堪危,她卻笑世人一葉障目,愚昧無知,丑顏實則傾城,冷血實則柔情,她只想將他藏起來,不讓人偷窺。 “大冰塊,摘下面具給本王妃瞧瞧!”她撐著下巴口水直流。 “想看?”某人勾唇邪魅道,“那就先付點定金……” 這是甜萌女與腹黑男一路打敵殺怪順帶談情說愛的絕寵搞笑熱血的故事。
316.4萬字8.09 152892 -
完結1039 章
絕寵世子妃
前世被親人欺騙,愛人背叛,她葬身火海,挫骨揚灰。浴火重生,她是無情的虐渣機器。庶妹設計陷害?我先讓你自食惡果!渣男想欺騙感情?我先毀你前程!姨娘想扶正?那我先扶別人上位!父親偏心不公?我自己就是公平!她懲惡徒,撕白蓮,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重活一世,她兇名在外,卻被腹黑狠辣的小侯爺纏上:娘子放心依靠,我為你遮風擋雨。她滿眼問號:? ? ?男人:娘子瞧誰礙眼?為夫替你滅了便是!
196.7萬字7.75 191914 -
完結107 章

蕓蕓卿州
魂穿貧家傻媳婦,家徒四壁,極品後娘貪婪無恥,合謀外人謀她性命。幸而丈夫還算順眼,將就將就還能湊合。懷揣異寶空間,陸清蕓經商致富,養萌娃。鬥極品,治奸商,掙出一片富園寶地。
17萬字8 27651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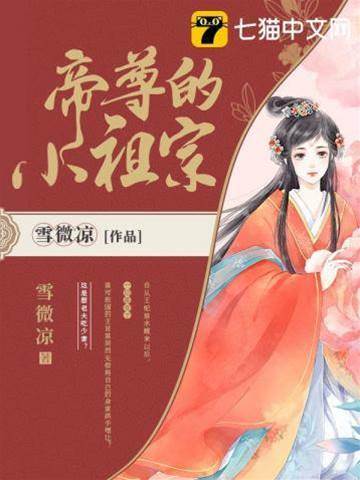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