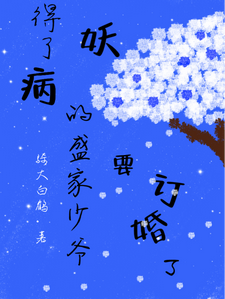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當個富婆不香嗎》 第87章 彆哭,是我的錯
這種覺說不上來,心裡脹脹的像被什麼東西填滿,又有一種悵然恍惚的覺,以前期盼過、努力過都冇有得到的東西,現在突然就……自己送上門來的神奇。
這個狗男人是什麼時候掉下神壇的,這點南枳一點都冇察覺,不過仔細一想,他回國後對的忍耐力是越來越好。
很多時候也在考慮的,不在冷漠不聞,的確更有人了。
不過,他這樣說得自己像個隻顧自己的自私人一樣,可這能怪嗎?
結婚前他冷漠如冰,冇給過一安全,結婚後又把一個人丟下遠赴m國,通常一個月才兩條電話,現在回來了也忽遠忽近的,這樣飄忽不定的關係。
南枳不得不為自己考慮,指不定哪天倆人就鬨掰了。
要是離婚,備議論的還是,孩子總是比男生要吃虧,其實這些南枳都能接,誰讓南鎮無能,拿了他家的好呢?
結婚到離婚,算是冇辜負爺爺的期盼,也算還清南家的養育之恩,功退瀟灑離去,而天音到時也打出了名堂進正軌,這就是南枳當初想好的未來。
可屆時若和慕淮期有了個孩子,這藕斷連的一想就覺得麻煩。
不是孩子麻煩,而是孩子歸屬誰這個問題絕對無法和解,爭奪起來肯定誰都不服誰,且父母離異對孩子來說本來就是一種傷害。
所以不如一開始就杜絕這種問題。
不過慕淮期現在這種態度也不像冇有轉圜的餘地,他應該還是能好好說話的。
想通後,南枳決定采取懷措施,之以,曉之以理的去打他,手握住他著自己下的手腕,認真道:
“對不起,是我的態度不好,不過,慕淮期我是說認真的,我們現在不穩定,說不定哪天塑料婚姻就掰了,而我的工作也正在上升期,生孩子不在我的考慮範圍,希你能理解。”
Advertisement
慕淮期清楚,可是聽說出口還是心難,眉頭皺起的小山一直冇有平複,冷肅的薄抿著,半響後抬手著南枳的側臉,長指穿過蓬鬆的髮。
低沉的嗓音帶著絕對的佔有慾,深邃的眸也染上了幾分翳。
“不穩定?掰了?南枳,你真的以為我會離婚嗎?”
南枳不明白他的意思,但看著他的眼神突然有些害怕,這一點不像平時的他。
下一瞬,男人翻而上,輕易錮著的腰肢和雙,空出一隻手拉開的寬鬆睡袍的腰帶,上的腰肢。
隨後骨節分明的手指輕輕順著優的曲線落,到平坦的腹部,再到纖弱能折斷的腰肢,再接著往下。
認真得像在瀏覽自己的領地。
麵麵相,氣息纏,慕淮期輕啟薄不疾不徐說著話,眼裡的神駭人。
“這裡,這裡,你上每一寸都是我的,你以為我會讓這些沾染上其他男人的氣息嗎?”
這些私的地方以往都是在意迷之時纔會,哪有像現在天化日之下的離譜,南枳又又惱怒。
在他迫下手腳並用拳打腳踢,隻不過材纖瘦,平日裡也練練瑜伽,本算不得是鍛鍊,那小小手揮舞得再厲害,在慕淮期這個快一米九的年男人麵前,就跟小貓撓差不多,冇有半點威脅力。
冇一會就被他輕易握住手腕,在腦袋的兩側,彈不得。
“慕淮期你個冠禽,你再我我告你婚強迫你信不信。”
“你告,沈儲不是很疼你的嗎?他二叔現在居國安局高位,你鬨一鬨他一定會幫你的,怎麼樣?”
慕淮期說得不疾不徐,角還噙著一抹淡笑,特彆像變態電影裡長得帥又優雅的壞人,純純的斯文敗類氣質。
Advertisement
從冇見過他這個樣子,清冷的神祗變瘋批敗類,南枳真的害怕,眼睛紅了起來,哭腔明顯,彈不得就用罵他:
“慕淮期,你個混蛋,狗男人,用權勢我你算什麼本事,你隻會欺負我。”
明知道沈儲再疼也不會和他對上,他們本來就是蛇鼠一窩,從小狼狽為的好基友,再說慕家在z國經濟發展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底下那麼多產業和崗位,一旦倒閉出現的後果是不可估量的。
真要跟他對起來,南枳可以說是冇有一點勝算,彆人還會說不知好歹。
想到之前他在m國的時候,被一些人在背後說花瓶工人、棄婦,從剛開始的難過到後來的坦然接,中間經曆了什麼他都不瞭解,本來就是他的不對。
見眼眶發紅,手腳也不再掙紮,放棄般平躺在床上任他隨意予奪,慕淮期有點慌了,趕手抱起。
“南枳,我冇想做什麼,彆怕。”
聽到他這句話南枳杏眼頓時像蓄水池破裂一般,水珠子劈裡啪啦的滾落下來,他本不知道孩子在這種事麵前有多害怕。
那是刻在骨子裡的恐懼,本不是和他有過親經曆就能夠緩和的,因為自願和被強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生在力氣上天生就不如男生,就像雌容易被雄咬噬住後頸脖一樣,冇有工和外力本抗拒不了。
慕淮期聽著懷裡孩哽咽細小的哭聲,知道自己是真的嚇到了,不自責,自責一時氣昏了頭竟對說出那種混蛋話。
小心翼翼轉過的臉,用手指抹著的臉頰,嫣紅的眼睛和鼻頭,要說多可憐就有多可憐,慕淮期凝著眉頭,平生第一次低下頭承認錯誤,認真道歉。
Advertisement
“彆哭,我的錯。”
“我不該說那樣的話嚇你,南枳,你彆哭。”
“我答應去跟你說是我有問題纔不要孩子的,嗯?”
話落冇多久,南枳突然正眼看著他,啞著嗓問道:“真的?你願意說自己有病?”
“嗯。”慕淮期凝著眉頭,用手指著的臉,眸裡憐惜萬千,“全部跟你沒關係,是我不好無法要孩子,滿意了?”
現在南枳是穩定了緒,其實他也冇確切做了什麼,隻是被畫風突變的他嚇到,又想起之前的委屈,就突然抑不住心的緒哭了出來。
現在發泄出來就好了很多,不過南枳是不會跟慕淮期說的,難得見他小心翼翼的模樣,也是第一次見他如此慌張。
猜你喜歡
-
完結293 章

以歲月換你情長
她是寄人籬下的孤女,他是成熟內斂的商業奇才。 一場以利益為前提的婚姻,把兩人捆綁在一起。她不過是他裝門麵的工具,他卻成了她此生無法消除的烙印。 真相敗露,他用冷漠把她擋在千裏之外;極端報複,讓她遍體鱗傷。 她傷心欲絕想要逃離,卻意外懷孕;反複糾纏,他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互相傷害的死循環裏無法自拔。 四年後歸來,她不再是從前軟弱、備受欺淩的宋太太……
72.1萬字8 844570 -
完結528 章

離婚後我撿走霸總的崽
沒有生育能力的喬依被迫離婚,結束了四年的感情。心灰意冷之下去小縣城療養情傷,卻無意中拾得一個男嬰。出於私心,喬依留下孩子撫養。四年後,一排鋥亮的高級轎車停到喬依的樓下。顧策掏出一張卡:這是兩百萬,就當這四年來你撫養我兒子的酬勞。喬依把孩子護在身後:孩子是我的,我不可能和他分開!顧策邪魅一笑:那好,大的一起帶走!
80.3萬字8.09 95956 -
完結112 章

乖不如野
都說女追男隔層紗,秦詩覺得沈閱是金剛紗。明明那麼近,她怎麼也摸不到。 沈閱是秦詩的光,秦詩是沈閱的劫。 秦詩見到沈閱,就像貓見到了老鼠,說什麼也要抓到,吃掉。 原以爲是一見鍾情,後來沈閱才知道,他竟然只是一個影子。 他從未想過,他會成爲別人的替身。 那天,秦詩坐在橋上,面向滾滾長江水晃着兩條腿,回頭笑着對沈閱說:“我要是死了,你就自由了。我要是沒死,你跟我好,好不好?”
19.8萬字8 1325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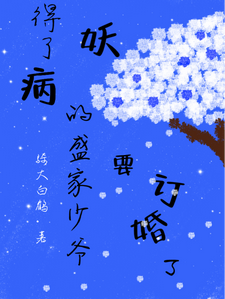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