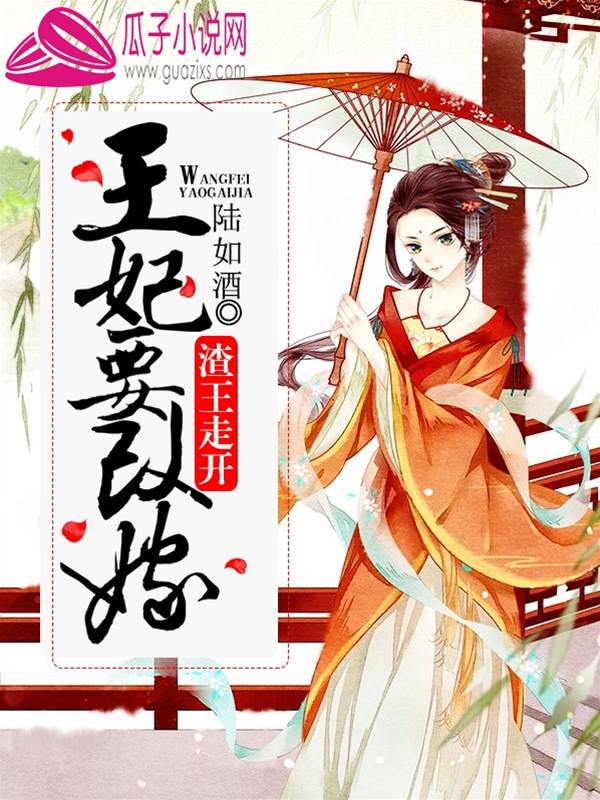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青珂浮屠》 第284章 消息
——————
做菜, 許青珂是會的,但做菜的區別在于——能不能吃或者好不好吃。
做的菜能吃,也不難吃, 但秦笙是自小養在鐘鼎勛貴士族中的嫡親大小姐, 平凡食于是不適的吧。
反正許青珂下意識想照顧好這位兒時唯一留下的故人。
值得最好的。
所以站在灶臺前想的是自己養母做的那些味佳肴,奈何這些年縱橫權, 卻是對廚藝得過且過,且好多年沒下手, 頓時失了自信, 何況……
秦笙笑的時候, 其實是看到了的手的。
之前許青珂將包扎了的手藏在寬大袖子里,秦笙沒發覺,此時看到了, 目定了一會,卻不上前噓寒問暖,只輕輕說:“你不得水,不用洗菜, 給我生火吧,我來弄。
許青珂驚訝,若有所思, 但也沒拒絕,只是坐在了灶爐后面生火的時候,才輕描淡寫說起了在宮里的事。
無非差點被冒犯。
不說,秦笙大概也猜到了, 因為看到了許青珂脖子上的印記。
礙于這種事比較私,對于子而言總是難以啟齒的,所以秦笙選擇不問。
沒什麼比安生活著更重要的,何況看許青珂的神態,也不像是是被完全吃盡了便宜。
但許青珂自己主說了又不一樣……
只是代了自己,好方便問秦笙另一件事。
“彧掠教你的?”
本在洗菜的秦笙作頓了頓,臉微紅,嗯了一聲。
“那段時日都是他弄的吃食,但后來他傷,我就學著弄了,不太好吃,勉強糊口。”
既提到彧掠,就忍不住問了,“他如何了?我當時已經昏迷,并不知后來如何,他可是……”
這段時日,最怕的就是他遭遇不測,但知道他生還的概率很小,因這群人太強太強了。
Advertisement
但哪怕懷著一點點希,也要偽裝出無比強大的模樣。
不能給青珂帶來更大的絕。
——————
“他還活著,只是回阿戈拉部落去了。”余下的,許青珂沒說,秦笙也猜不到。
們素來不喜高估自己對男人的影響,但可以預判對方對男人的影像。
許青珂揣度這次秦笙才是真正惹怒彧掠這頭草原孤狼進而殘忍報復父親兄弟的主因。
不然從前也不是第一次被父兄暗算,為何這次才發作。
但弒父在中原看來到底也是不好的,何必把這種責任冠在秦笙上,所以許青珂不再提。
這飯菜一出來,許青珂吃了幾口,問秦笙:“你以前煮的時候,他都吃了吧。
秦笙再次臉紅,顧左右而言他,“不太好吃是嗎?我也覺得不太好吃……”
“看來是吃了。”許青珂淡然說。
秦笙越發了,抬手就要打。
明明是階下囚,卻是怡然自得,這兩個人多奇怪啊。
但不知何時到的弗阮只淡淡瞟了們一眼。
兩都很冷漠。
剛剛的笑仿佛只是鏡中花水中月。
進了廚房,弗阮看了下飯菜,說:“不太好吃。”
仿佛他吃過。
秦笙可不會為此尷尬歉意,左右也不是給這人吃的,若是給他吃的,活該煮□□了。
“你去給我下碗面。”弗阮對許青珂命令。
秦笙錯愕,許青珂也皺眉了,這人弄什麼幺蛾子?
許青珂沒的時候,弗阮微笑補充,“吃飽了才好上路,沒吃飽,我就不去敦煌了。”
秦笙已經知道景萱的事,聞言頓時覺得這位閣主國師真真是妖孽一般。
晴不定,兵行鬼招。
但也致命。
許青珂起,好在菜還有多,加一個蛋,加上這廚房許是早上做過面,面條還留有一些,放點面條下去煮也不為難人。
Advertisement
一碗面好了。
跟秦笙就起走了。
弗阮并不介意兩個階下囚的冷淡,只顧自用筷子夾起幾面條放進里。
咀嚼了下,他幽幽吐出一口氣。
“還不如人家的菜。”
————————
“此人太詭異,看似好人,實則無無心,難為你這些年與之周旋,但我總覺得他……”秦笙的話戛然而止,因為許青珂正倚著門,背影被月襲染得有幾分落寞。
秦笙想,被養在邊那麼多年,手把手教育長大,明知養大了要跟自己復仇……
這弗阮的心態也是詭異。
可對于許青珂而言,恐怕也不能那麼容易釋懷。
不過約覺得許青珂還有事瞞著。
不能說的。
————————
弗阮第二天就走了,走之前還特地來見許青珂,說了一句讓許青珂十分錯愕的話。
“魁生跟你小姨走了,倒是你的小男人又來了,如今還放出了消息。”
“你猜猜是什麼消息。”
聰明人就喜歡考聰明人。
許秦珂眉梢上揚:“《江川河圖》”
“不假思索,看來早有準備。”弗阮輕笑了下,最后一句話輕飄飄的。
“《江川河圖》換人,是江山還是人,讓一個帝王跟一個勝似帝王的人為你取舍,許青珂,希師傅回來的時候,你不會跟著這兩個男人跑了。”
弗阮就這麼走了,從始至終都沒把邊上的秦夜看在眼里。
但秦夜手中卻有秦川的旨意。
關于帶回許青珂的旨意……
“是怎麼回事?”許青珂問秦夜,秦夜想起秦川的吩咐,卻說:“大人可以回去問君上,君上會親自跟您說。”
現在外面已經有傳言起,再過幾日恐怕要傳遍諸國。
Advertisement
那師寧遠的用意無非是要救回許青珂,但估計沒人會想到他會用這麼“明正大”的方式。
許青珂也沒想到。
江川河圖的確有用,給嚴松的預定計劃是以此為引,顯然上師閣下改變了計劃。
一種更瘋狂更危險的計劃。
突兀的,許青珂想到了一個地方。
淮水。
————————
“君上,那師寧遠已放言手頭有完整的《江川河圖》,要跟我們換許相。”
“君上,此賊膽大包天,不可不除。”
“君上,此人若真的有完整的《江川河圖》,那可是大功于社稷的絕啊!”
朝堂紛擾,民間沸騰。
那師寧遠是用了手頭所有在諸國的基,將消息大范圍傳播,用不著兩三天就舉世皆知。
若是無人知,秦川大可暗殺此人,管它什麼《江川河圖》還是什麼,可如今淵國境子民皆知,而諸國也知。
若是換,有可原,畢竟無利不起早,這世上沒有一個人的價值能跟《江川河圖》并論。
若是不換,說明帝王者高傲強大不愿屈服?不,只會盛傳君王獨寵許青珂,為甘愿放棄可助益問鼎天下的至寶,朝堂百姓不會允,天下人也會看輕淵的強大。
——他們的王,已經為一個人無限度折腰,還能帝國一統?
師寧遠已經將自己的選擇擺出來,于是著秦川選——是一統帝國的野心跟威嚴還是許青珂?
歹毒啊,不愧是上師,狼狽敗走才多天,轉頭就給他們殺了一個如此鋒利的回馬槍。
明森等老臣慨,卻也等著君王的選擇。
他們也想知道自己一心輔佐的帝王是不是已經把許青珂看得比帝國野心還要大,若是如此……
那這許青珂是必然不能留在淵的。
Advertisement
——————
鏗鏘!桌上件全部被掃落在地,宮人們戰戰兢兢不敢言語。
秦兮進書房后正好看到這一幕,眉頭一皺,揮手讓其余人出去了,書房中只剩下兄妹兩人。
“哥,你失態了。”
秦川坐在椅子上,看向自己的妹妹,憤怒制了一大半,但仍有一半在靈魂深。
“我失態了,大概是因為察覺到了自己的卑劣,我不該猶豫不決。”
秦兮原本設想過很多該說的話,卻在此時不懂了。
不該猶豫不決?
那是不該為何猶豫?
秦兮蠕……“許青珂?”
秦川沒有直接回答,卻睜開眼看著自己唯一至親的妹妹。
“懦弱跟強大只在于一線之差,比如失去還是擁有。”
秦川站起來,握住了自己的佩刀。
“師寧遠不會如愿的。”
——————————
因為《江川河圖》的再現世,本就暗洶涌的諸國局勢越來越復雜,淵要一統帝國,需要它來助益,其余諸國何嘗不是用它來抵擋淵的鐵矛。
于是,所有人都在找師寧遠。
也許也只有許青珂才知道他在哪里。
淮水。
所謂秦淮河邊,夜游香海,師寧遠在淮水邊上靜觀諸國局勢變化,但他最留意的也就兩個地方。
淵是肯定的,還有一個是哪里?
“蜀?”已經回到他邊的某個高手朋友問他。
“蜀是的地方,銅墻鐵壁,就是弗阮想要手,也得費些時日跟手段,自然不是。”師寧遠喝著酒。
“靖國?那太子軒是個人,就是心太大,想魚與熊掌兼得,還有燁……那齊惶這些時日可是游走淵朝堂,拉了好些關系。”
一個武林人分析朝堂局勢也是頭頭是道,可見如今這諸國政治到了何等鋒利的時候。
“你比北琛還笨”這就是師寧遠的回答。
顯然,這位武林高手都猜錯了。
都不是?!那不就是……不可能啊!
“晉國?!!!”武林高手驚疑不定,師寧遠卻一飲而盡。
“彈琴的那廝靠不住。”
猜你喜歡
-
完結325 章

攝政王冷妃之鳳御天下
不可能,她要嫁的劉曄是個霸道兇狠的男子,為何會變成一個賣萌的傻子?而她心底的那個人,什麼時候變成了趙國的攝政王?對她相見不相視,是真的不記得她,還是假裝?天殺的,竟然還敢在她眼皮底下娶丞相的妹妹?好,你娶你的美嬌娘,我找我的美男子,從此互不相干。
62.7萬字8 16261 -
完結668 章
毒妃傾城:王爺掌中寵
夏吟墨手欠,摸了下師父的古燈結果穿越了,穿到同名同姓的受氣包相府嫡女身上。 她勵志要為原主復仇,虐渣女,除渣男,一手解毒救人,一手下毒懲治惡人,一路扶搖直上,沒想到竟與衡王戰鬥情誼越結越深,成為了人人艷羨的神仙眷侶。 不可思議,當真是不可思議啊!
120萬字8 17247 -
完結150 章

殷總,寵妻無度
姜綺姝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當她慘遭背叛,生死一線時救她的人會是商界殺伐果斷,獨勇如狼的殷騰。他強勢進入她的人生,告訴她“從此以后,姜綺姝是我的人,只能對我一人嬉笑怒罵、撒嬌溫柔。”在外時,他幫她撕仇人虐渣男,寵她上天;獨處時,他戲謔、招引,只喜歡看姜綺姝在乎他時撒潑甩賴的小模樣。“殷騰,你喜怒無常,到底想怎麼樣?”“小姝,我只想把靈魂都揉進你的骨子里,一輩子,賴上你!”
37.1萬字5 11927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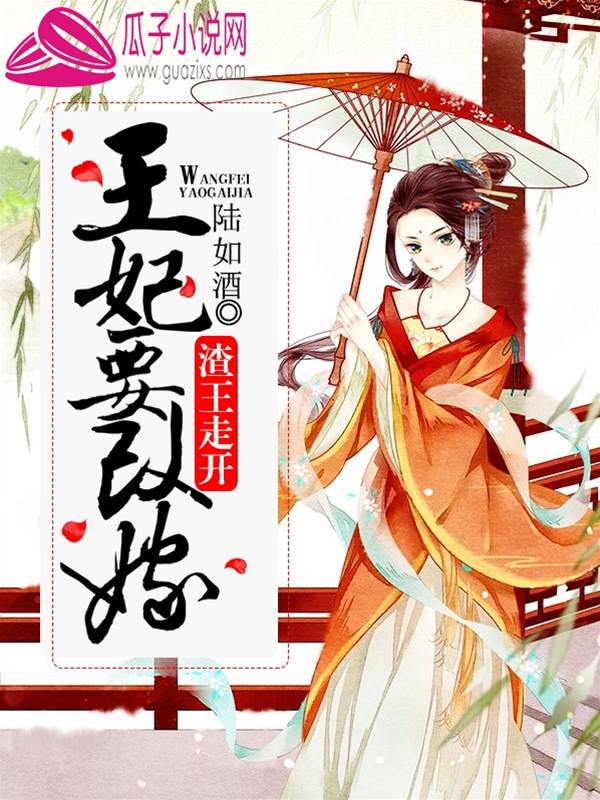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137 章

鶴帳有春
穆千璃爲躲避家中安排的盲婚啞嫁,誓死不從逃離在外。 但家中仍在四處追查她的下落。 東躲西藏不是長久之計。 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生個孩子,去父留子。 即使再被抓回,那婚事也定是要作廢的,她不必再嫁任何人。 穆千璃在一處偏遠小鎮租下一間宅子。 宅子隔壁有位年輕的鄰居,名叫容澈。 容澈模樣生得極好,卻體弱多病,怕是要命不久矣。 他家境清貧,養病一年之久卻從未有家人來此關照過。 如此人選,是爲極佳。 穆千璃打起了這位病弱鄰居的主意。 白日裏,她態度熱絡,噓寒問暖。 見他處境落魄,便扶持貼補,爲他強身健體,就各種投喂照料。 到了夜裏,她便點燃安神香,翻窗潛入容澈屋中,天亮再悄然離去。 直到有一日。 穆千璃粗心未將昨夜燃盡的安神香收拾乾淨,只得連忙潛入隔壁收拾作案證據。 卻在還未進屋時,聽見容澈府上唯一的隨從蹲在牆角疑惑嘀咕着:“這不是城東那個老騙子賣的假貨嗎,難怪主子最近身子漸弱,燃這玩意,哪能睡得好。” 當夜,穆千璃縮在房內糾結。 這些日子容澈究竟是睡着了,還是沒睡着? 正這時,容澈一身輕薄衣衫翻入她房中,目光灼灼地看着她:“今日這是怎麼了,香都燃盡了,怎還不過來。”
20.8萬字8.33 149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