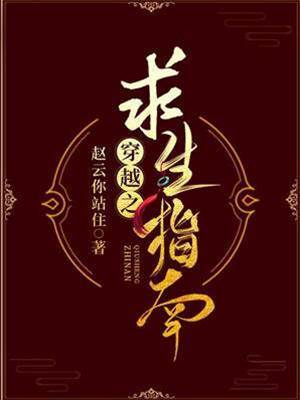《雅騷》 第259章 夜船無人私語時
秦淮碧水,斜煙柳,茉莉、建蘭香氣隨風約,叩門良久子卻道郎不在,張萼大為掃興,問薛:“你家郎去哪裡了?”
薛道:“竟陵譚先生到了金陵,我家郎去白鷺洲碼頭拜見譚先生去了。【全文字閱讀】”
張萼惱道:“哪個譚先生?”
薛道:“是我家郎的老師,寫詩的。”
張岱道:“應該就是譚元春了。”
從青浦來金陵的船上,王微與張岱、張原論詩時極為推崇竟陵鍾惺和譚元春,張原說鍾、譚的詩不過爾爾,王微很不服氣——
張原道:“罷了,我們回船去吧。”轉便走。
張岱、張原跟上,小廝福兒還站在院牆邊與薛嘀嘀咕咕說些什麼。
張萼氣忿忿道:“這郎假惺惺,水xìng楊花無憑準。”張萼生氣,那自是因為他對王微是很在意的,興衝衝來訪,卻被告知去見另一才子名士去了,張萼當然不快活。
張原笑道:“三兄還真當作王修微眼yù穿盼我們來啊,結識我們之先,已經結名士半江南了,譚元春曾教寫詩,也是老師,去拜見老師也是應該的。”
張萼翻白眼道:“這郎老師倒是多,又是陳繼儒又是譚元春。”
張岱道:“譚元春如何比得陳眉公,差得遠了。”
……
“汗草、茉莉花,十文錢一束,十文錢一束——”
兩個趿著木屐、穿著無袖單的十四、五歲年各挽一個草籃,高聲唱賣而來,沿河家便有jiāo婢卷簾,攤錢爭買,賣花年是慣常來的,一時紛紜笑謔,香澤盈盈——
張原三人跟著那兩個賣花年緩緩而行看熱鬧,忽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兒從一棟梅竹掩映的屋宇裡走了出來,這孩兒前發覆額,眉目如畫,sè白皙可,右掌心墊著一方帕,帕上有兩疊銅錢,脆生生道:“屐小哥,汗草、茉莉花我家各買一束。”
Advertisement
“小蔻,我給你留著呢,這兩束最好,含苞未放,放在枕頭邊,夜間就開了,分外香。”
一個年殷勤地將兩束花到這孩手中,孩左手接過花束,先嗅了嗅,嫣然一笑,右手一傾,那兩疊錢叮叮脆響落年的草藍中,說聲:“多謝兩位屐小哥。”腰肢一扭,蓮步輕盈,梅樹竹蔭中——
兩個年草籃裡還有些花草未賣完,卻不立即離開去別賣,站在梅竹院牆下發呆,聽牆那孩脆生生的笑聲——
張萼笑嘻嘻上前道:“這孩才十一、二歲,你二人就想非非了,簡直是禽。”說到“禽”二字,臉一板。
兩個賣花年頓時漲紅了臉,又驚又怕,拔tuǐ就跑。
張萼大笑,跟過來的薛也笑。
張原笑道:“三兄嚇唬小孩子。”
張萼道:“也不算小了,我十五歲就已嘗yù滋味,嘿嘿。”轉過話題道:“方才這孩兒著實jiāo俏,再有兩年定然又是一個勾hún攝魄的妖,不知是誰家孩?”便問薛?
薛道:“那是湘真館李蔻兒,李雪姑娘的妹子。”
張萼喜道:“這便是李雪的居所啊,妙極,李雪有妹如此,可以想象李雪的jiāo容——大兄、介子,既然王微不在,我們便到這湘真館看一看如何?”
薛撇道:“雪姑娘與我家郎一起外出了,不信你們敲門試試。”說罷,轉回幽蘭館去了,這子走得極快,轉眼就沒影了。
梅竹掩映下的院門已經關閉,曲中舊院要到華燈初上時,
宴歌弦管、聲凌,方顯繁華,而此時是炎熱的午後,賣花年一過,又顯冷冷清清。張原道:“回去吧,莫再去討閉門羹吃,李雪是曲中名,不事先約好,哪能就見得到。”
Advertisement
三人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經過曲中市肆時,見潔異常,香囊、雲舄、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琴瑟,皆是上品,張原三人買了兩壺細酒、一盒湖州岕茶、一罐餳糖和幾樣金陵小菜,讓馮虎用個籃子拎著,回到止馬營碼頭浪船上,留在船上除了四名船工外,還有張岱的小廝茗煙和穆真真、素芝和綠梅這三個婢,來福、能柱、武陵幾個都去了鳴山下那房子,船上有些已經搬到那邊房子去了,穆真真問張原:“爺,這八隻箱子何時搬過去?”穆真真知道這八隻箱子的重要。
張原問張萼:“三兄,我們今夜能到新租賃的房子睡覺嗎?”
張萼道:“今日怕不行吧,來福、能柱還在那邊收拾呢,明日去吧。”
張原便對穆真真道:“這箱子明日一起搬過去。”
傍晚時,焦潤生和宗翼善來請張原三人去澹園晚宴,張原帶了一副昏眼鏡送給焦老師,上次來時忘了帶來,焦竑試了眼鏡,大悅,讀書寫字不用仰著脖子了,席間焦竑問了張原、張岱在貢院考試的況,聽二人分別背誦了那篇“樊遲問知”的製藝,誇獎了兩句,又叮囑張氏三兄弟在國子監要勤勉求學,勿犯監規——
張原到焦潤生書房給父親張瑞寫了一封信,先向父親稟明自己近況,再問父親是否已辭去周王府掾史長一職,何時離開開封,他可以渡江去迎接——
張原將信封好,請焦潤生用府驛遞將信送到開封周王府,焦潤生答應明天就將信傳遞出去。
二鼓時分,焦潤生、宗翼善送張原三兄弟出了澹園,焦潤生道:“後日便是三位張兄正式國子監之期,以後怕是沒那麼方便出來了,家父說顧祭酒要嚴明監規,整頓南監。”
Advertisement
張萼愁眉苦臉道:“倒霉,遇上這麼個瘟,我這人最不耐拘束,來金陵本就是為了六朝金、秦淮風月而來,不是來坐監的,若管得我狠了,我早晚大鬧一場。”
張岱、張原面面相覷。
焦潤生知道這個張燕客是何等人,笑道:“國子監對於納粟的例監生一向寬容,燕客兄若不坐監,盡可托病居外,掛個名即可。”
張萼喜道:“原來可以通融,甚好,甚好。”看了一眼大兄張岱,嬉皮笑臉道:“我先坐幾天監看看,若忍不了,我就陡生大病,要出外求醫了,只求大兄不要向大父提起。”
張岱白眼道:“這瞞不了的,大父與南京六部員多有書信往來。”
張萼道:“那我不管,總不能悶死在監中。”
張萼是野馬,要張萼循規蹈矩太難了,與其讓他與南監學起衝突,還不如托病出監逍遙自在,反正也不能指張萼在國子監能學到什麼聖賢之道——
張原道:“三兄先監新鮮幾日再說,實在不行還是出監的好。”
張岱搖頭道:“還未學,先想到退學,這也算得一樁奇聞了。”
張萼隻把大兄這話當作誇獎,哈哈一笑。
兄弟三人別了焦潤生、宗翼善,回到浪船上,卻聽穆真真說王微姑派了人來請三位爺去幽蘭館,已回說三位爺去焦狀元赴宴未回——
這時已經是亥末時分,當然沒有夤夜去幽蘭館的道理,兄弟三人各自沐浴歇息,張原回到艙室,見穆真真在燈下磨墨,抬頭含笑道:“爺,練字嗎?”
張原每晚臨睡前要寫兩百字小楷,正好沐浴後待頭髮晾乾,這已習慣,穆真真知道爺這習慣,所以便把墨磨好,爺沒寫完的墨就用來寫華山碑大字,要把字練好,以後還要給爹爹寫信呢——
Advertisement
張原“嗯”了一聲,盤tuǐ坐在小案邊,提筆臨摹王思任老師書寫的《神賦》,穆真真跪在他後用布巾輕輕給他拭乾頭髮,待頭髮差不多幹了就松松的挽個髻,因為張原不喜歡披頭散發睡覺——
張原全神貫注臨摹王老師的小楷,寫到神,渾然忘我,筆尖在松江譚箋中雖只有微小的點劃移,卻有墨字潺潺流麗、凌空飛舞、縱揮灑的覺,這種覺很妙,沒練過書法的難以會。
下三鼓,張原將後半篇《神賦》臨摹畢,硯裡的墨也用了,轉頭對穆真真笑道:“你沒墨寫了,今天不要寫了,夜深——”
說到這裡,張原突然閉了,表有些奇怪——
秦淮河的宴歌弦管在這午夜也已曲倦燈殘、星星自散,只有市聲傳到耳邊,船上很靜,張岱、張萼早已睡下,四個船工早起也早睡,這時也已進夢鄉,這船上還沒睡的應該就中張原和穆真真兩個人了,往常,來福的鼾聲早已在屏風那邊撕來扯去了,而今夜,屏風那邊悄然無聲,武陵和來福都在鳴山下收拾屋舍未歸,這艙室只有張原和穆真真兩個人——
穆真真顯然比張原更早意識到這一境,這時見爺這麼奇怪地看著,臉瞬時就紅了,有些口吃道:“爺,早些歇息吧,明日是爺的生日呢,婢子已買了面餅來,明日早起為爺做長壽面。”
若不是穆真真提起,張原自己都忘了明日六月十九就是他生日了。
——————————————————
本想一氣寫完這個節,卻有事耽擱了,小道現在也熬不得夜,明天再寫吧,盡量寫好點。!。
請記住本書首發域名:風雲小說閱讀網手機版閱讀網址:
猜你喜歡
-
完結136 章
黑月光拿穩BE劇本
城樓之上,窮途末路後,叛軍把劍架在我脖子上。 他大笑問澹臺燼:“你夫人和葉小姐,隻能活一個,你選誰?” 係統看一眼哭唧唧的葉冰裳,緊張說:宿主,他肯定選你。 澹臺燼毫不猶豫:“放了冰裳。” 係統:哦豁。 我:哦豁。 係統安慰道:澹臺燼肯定是知道你家大業大,暗衛們會救你。 澹臺燼確實這樣想,不過那日後來,我衝他一笑,在他碎裂的目光下,當著三十萬大軍,從城樓上跳了下去。 連一具完整的屍體都冇留給他。 這是我為澹臺燼選的be結局。 景和元年,新帝澹臺燼一夜白髮,瘋魔屠城,斬殺葉冰裳。 而我看透這幾年的無妄情愛,涅槃之後,終於回到修仙界,今天當小仙子也十分快活。 #據說,後來很多年裡,我是整個修仙界,談之色變,墮神的白月光#
44萬字8.33 16307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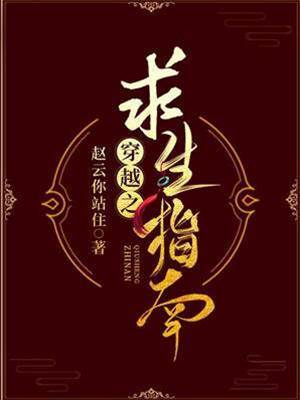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