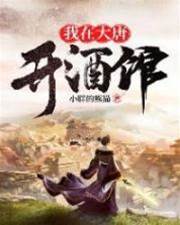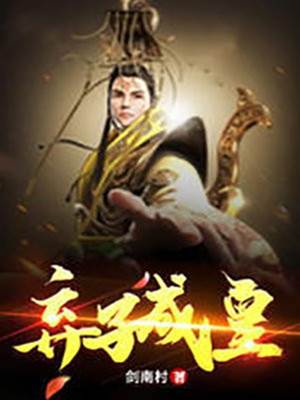《伐清》 第60節 人心(上)
盤踞江南的蔣國柱的實力比張朝雄厚得多,雖然未必比得上兩省在手的張長庚,但因爲距離四川較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抵銷了鄧名軍力上的優勢。因此在鄧名最初的判斷中,蔣國柱將會是此行最難解決的麻煩。不過鄧名最開始保守地估計會在湖廣和江西遇到有限的抵抗,所以明軍抵達江南時已經到損耗,還需要在後方部署兵力防備二張作。
可現在的況比計劃要好得多,湖廣和江西不但沒有抵抗而且還互相陷害,導致明軍兵不刃地抵達到江南邊境,因爲沒有發衝突還拿到了保證金。鄧名更不需要在後方留下大量警戒部隊,參戰的夔東軍都和川軍一起東進——讓夔東軍留在後方很可能引起他們的不滿,還冒著和張長庚衝突的危險;而如果讓川軍留守又會大大削弱鄧名的力量。
“上次和虎帥下江南的景象,我至今仍歷歷在目。”規模龐大的明軍艦隊駛過江西、江南邊境時,鄧名登上了李來亨的坐艦,好整以暇地和後者回憶起往事來。
“僅僅四年,長江上最強大的艦隊就在提督的麾下了。”李來亨也不慨起來了。上次他率領軍隊前來時,還需要化妝綠營掩人耳目,即使那時鄭功已經把東南清軍折騰得神魂不定,南京擁有的艦隊也不是李來亨手下那些民船能抗衡的:“提督那時已經到南京了,而我還在安慶周圍東躲西藏,每次看到韃子的鉅艦從我的船隊旁駛過的時候,即使只有幾艘,心也會砰砰地跳,生怕被他們識破份。”
那種印象十分深刻,即使過了好幾年李來亨也記得很清楚。而現在佈長江的龐大明軍艦隊就算是想化妝清軍都做不到,因爲誰都知道清廷本沒有這樣一支艦隊了。李來亨、劉純是最早趕來的;黨守素、馬騰雲也在鄧名離開湖廣前追上了鄧名;而在九江停留時,王興也乘船抵達——這次還是郝搖旗留守襄,監視張長庚和河南綠營,而賀珍生病了,所以漢水流域的明軍只派來了象徵的部隊。
Advertisement
當初制定計劃的時候,鄧名就敲定要等部隊完集結後,再跟在銀行家們後面進江南境,讓這些侵的金融尖兵能夠得到軍事後盾的保護。現在雖然比預料的況要好,但鄧名也沒有必要改變計劃,銀行家一個個府縣走過去,推銷著戰爭債券;在一個府完任務後,明軍就會跟上,以保證在銀行家過知府老爺的門檻時,推銷對象能同時接到他轄地邊境上的軍告急報告。
七百艘大小船隻,裝載著三萬餘名夔東軍、兩萬五千名帝國水陸兵和兩萬兩千多名四川隨軍勞工。九萬人馬的規模比上次李星漢等人下江南的聲勢還要浩大。當鄧名的旗艦離開安慶府,在池州府下轄的東陵停泊下時,後衛部隊仍在池州府的府城前等候,等著去巢湖聲援前往合推銷債券的銀行家的偏師返回。
銅陵的知縣在認購了他那份債券後喬裝打扮,來到鄧名的軍營中拜見,鄧名也勞一番,稱他上次貢獻的黃銅質量很好,還特意讓一個三堵牆衛士把頭上的黃銅頭盔摘下來給銅陵知縣過目。
此時太平府的知府也親自趕來拜見鄧名。雖然明軍還沒有離開廬州府,不過知府老爺覺得禮多人不怪,登門求見起碼落一個態度良好。知府出發前,來太平府推銷債券的銀行家還沒有到,但知府老爺也早就代手下,一定要全力滿足四川銀行家們的各種要求,至於銀行家的起居待遇則參照退休尚書的標準。
雖然明軍再次寇的消息已經傳遍全府,但太平府境並無毫恐慌緒,不小地主都笑逐開:“去年太平府就免五稅了,今年又能免不吧?這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好了啊。”
Advertisement
府的道路上到都是向江邊涌來的人羣,其中還有不寧國府的百姓,他們趕著大車,後面滿載著貨——去年招待明軍過境的人都發財了,尤其是幾十萬百姓搬遷川的時候,在江邊擺攤賣貨的人一個個都賺了個飽。聽說明軍又來到江南了,太平府的老百姓奔走相告,聞風而來,一心想多賺點錢,打下過年的基礎。寧國府不靠江,但也不甘人後,不人乾脆帶著捕魚的傢伙,打算在江邊好好做幾個月生意;還有一些人則是來買東西的,他們聽說每次明軍進江南時都會運來大量貨,綢、川繡、贛瓷的價格都只有家鄉的幾分之一。這種趕大集的機會可遇不可求,明年嫁兒、娶媳婦就盯著這趟買賣呢。
有經驗的太平府漁民則對這種蜂擁而上的行爲不屑一顧,一個人私下評價道:“現在還不是最便宜的時候。去年川軍回師的時候,那才便宜呢,我一口氣就買了五條八新的綠營軍,夠我穿好幾年了。”
“才五條?”另外一個人說道:“我沒花幾個錢就買了十幾件綠營的號,親戚、鄰居分去了不。剩下的都改褂子了,補補穿到老都沒問題。”
眼下明軍還沒有到,但長江邊已經熱鬧非凡,甚至藝人也都吸引來了,唱戲的、玩雜耍的來了好幾撥。現在清廷對東南的聚斂依舊嚴苛,四川其實也在吸金,所以地價在稍微回升一些後停止上漲,徘徊在每畝五兩銀子左右。如果能夠在江邊做一把紅火的生意,比一年在地裡辛勞耕種的所得還要多。
只是這次明軍過境的時間不太好,五月份農田裡的事很多,所以家裡還要留下足夠的壯勞力。尤其是那些距離遙遠的人,一個勁地埋怨明軍怎麼不挑七月份再來,還能順便打劫一下朝廷的運糧漕船——鄧名和漕運總督的協議普通老百姓當然不知道,他們只知道漕船上有銀子、有糧食、有布匹和其他江南土產,明軍搶了不會都帶走,甩賣時百姓們還能買點便宜貨。
Advertisement
江邊的景象給太平府知府一種覺,那就是他府城的廟會都沒有這麼熱鬧過。
“朝廷要收拾人心啊。”化妝的知府不敢暴份,所以也只能在心裡嘆息一聲:“總督大人,要收拾江南的人心啊。”
來到銅陵附近後,知府不用打聽就知道明軍離得不遠,因爲這裡的道上已經是人來人往,五月裡這種現象是極爲罕見的。長江上來往著小販的舢板,到都是他們洪亮的賣聲。岸上說書的,打快板的,彈琴、唱曲的,應有盡有。
知府老爺親眼看到食攤的攤主笑逐開地招待個幾個明軍裝束的顧客,高高興興地從他們手裡接過那種稱爲軍票的東西——知府對這東西並不陌生,從上次侵江南開始,明軍就使用這種戰場紙幣,接者可以持軍票嚮明軍兌換銀錢——甚至在明軍離開後,仍然有兌換工作在繼續,據說是剿鄧總理衙門在負責這件事,這種說法還在衙門的胥吏口中傳得有鼻子有眼的。
當然,剿鄧總理衙門對此矢口否認,要求東南各府的胥吏隊伍不信謠、不傳謠、不抹黑兄弟單位。謠言初起時,總理衙門就發過一份公文,正式否認了他們代兌明軍軍票,更主否認剿鄧衙門會把軍票集中送去川西,從明軍手裡兌換白銀以賺取手續費。蓄意傳播類似謠言的都是潛伏在清廷這邊的明軍細作;發這份公文的人在一個月後被剿鄧總理衙門經部調查後解職逮捕,並宣佈查明他就是潛伏在剿鄧總理衙門的明軍細作,這份造極惡劣影響的公文被回收銷燬。
新的一份公文裡再次對謠言予以否認,並稱即使剿鄧總理衙門真的回收明軍軍票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也是爲了百姓著想,是衙門各級吏在周布政使的召下,主捐出俸祿來幫助窮苦百姓彌補損失。第二封公文帶來的惡劣影響甚至更甚前者,得知此事後,太平府的知府都將信將疑起來。而布政使大人知曉後也是然大怒,他的左右手聞風而,迅速偵破此案,發現發出第二封公文的正是判前一個明軍細作死刑的傢伙,是一個潛伏更深的明軍細作。
Advertisement
就在第二個暴的明軍細作和被他死的同夥一樣被正法後,剿鄧總理衙門果斷改走東南督的上層路線,很快太平府就接到兩江總督衙門下達的公文,以後嚴在任何公文中提及“軍票”兩個字,否則一律以明軍細作論。有小道消息說,這個令是周培公親自去向蔣國柱總督申請來的。
“去打山東吧!”那個剛接過明軍軍票的飯鋪老闆熱洋溢地向離去的明軍士兵揮手:“多帶點人回來,我做好吃的給你們。”
“一定要去打山東啊。”不百姓都跟著一起嚷嚷,用力地嚮明軍喊著。
在百姓的背後,一個清軍使者騎著快馬匆匆趕往南京,裡面裝著一份給兩江總督的告,其中一份是給朝廷的正式奏章——上下一心力保城池不失,衆志城再創銅陵大捷。
猜你喜歡
-
完結10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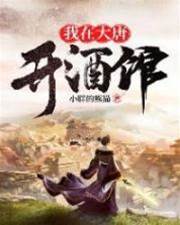
我在大唐開酒館
穿越大唐,張諾隻想安安穩穩地經營好酒館,到時候經濟改善了就買個丫鬟,娶個漂亮媳婦過上好日子,結果,他營業的第一天就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李世民。作為穿越者,他擁有著遠超這個時代的目光與見識,隨口閒扯兩句,聽在李世民的耳中都是振聾發聵。不久後,張諾發現,自己隨便說說的東西,居然就變成了大唐的治國方針……
188.3萬字8.18 93155 -
連載1675 章

將門梟虎
雇傭兵穿越到大楚國,成為百戶所軍戶吳年。家裏頭窮的叮當響,還有一個每天被原主暴打的童養媳。北邊的蒙元人漸漸強盛,頻繁南下劫掠,大楚國朝不保夕。
336.3萬字8.33 109725 -
連載18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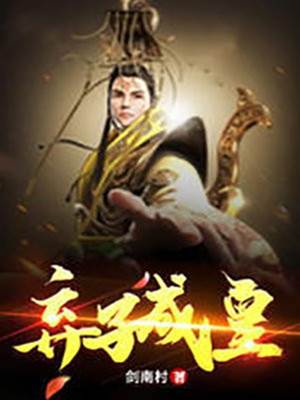
棄子成皇
一覺醒來,穿越古代,成為被打入冷宮的皇家棄子。囂張跋扈的奴才,陰險毒辣的妃子,冷漠無情的帝王……楚嬴劍走偏鋒,好不容易掙脫冷宮枷鎖,轉眼又被發配到邊疆苦寒之地。什麼?封地太窮,行將崩潰?什麼?武備廢弛,無力抵擋北方賊寇?什麼?朝廷不予援助,百姓要舉家南逃?危機環伺,人人都覺得他已窮途末路,然而……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紹,哥前世應用科學專業畢業,最強特種兵出生,種種田,賺賺錢,打打仗,還不是手到擒來?!
335.3萬字8.18 1278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