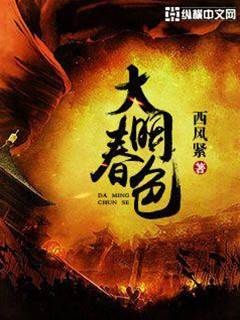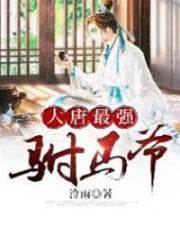《伐清》 第33節 試探
鑑於膠東的現狀,議院的投票權完全是據財產的多來劃分的,只有有財產的人才在縣議院有發言權。如果一羣小地主聯合起來的地產達到議院規定的標準,那他們也可以推舉一個代表來議院參加會議。至於佃農的意見則完全被忽視了,反正他們都是唯東家馬首是瞻,鄧名也無意幫他們立刻取得政治權利——鄧名還要和清廷繼續打仗,不能爲了佃戶去得罪膠東的縉紳階層,他給自己的定是帝國主義者而不是革命者。而城市的大俠也可以在議院中有一席之地,只要他們和縉紳一樣爲扶清滅明軍提供軍費,那他們就可以有代表權,提供不了軍費就沒有。
至於於七帶來的幾萬難民,鄧名極力遊說縉紳議院從中取壯者編組軍。有不縉紳對此到擔憂,因爲現在停火談判已經開始,他們擔心繼續擴軍會引起清廷的仇視。
“雖然我們在和清廷談判,不過你們猜清廷現在打的如意算盤是什麼?”鄧名對大夥兒進行了啓發。
清廷從來就不是靠以德服人來獲取天下的,而是他的兇惡名聲,所以縉紳們很容易就猜到了,清廷多半還是琢磨要在江南和山東戰場都取得勝利,然後把膠東的義軍鎮下去,同時迫使鄧名在談判中讓步——如果實在無法徹底殲滅鄧名的話。
Advertisement
“清廷肯定想著剿滅扶清滅明軍,然後再維持那時的膠東‘現狀’的,所以你們要想保住家命,最好是有攻破濟南,截斷漕運的實力,那樣清廷就該求著你們退回膠水河以東,答應你們提出的條件了。”鄧名努力推銷著能戰方能和的思維模式:“到時候你們只要不貪心山東更多的領土,應該很容易和清廷達招安協議。”
“我們對青州府沒有想法。”縉紳議院又一次被鄧名給說服了,他們紛紛保證對朝廷的領土沒有更大的野心,只是想保住登州、萊州的一畝三分地。鄧名也相信他們的表態。如果不是擔心登州府剿滅了於七就掉頭朝著義軍殺過來,萊州府的縉紳對於離開本府作戰都沒有多大興趣。不過萊州府和登州府的縉紳對青州自治沒興趣,不代表被“解放”後的青州縉紳沒興趣,只是這件事也不到鄧名去心了。
除了一部分可以被招募兵的人外,鄧名打算把剩下的牙山難民安置到沿海地區去。由於沿海地區已經荒無人煙,給閩軍的運輸和籌集糧草工作造了極大的困難,而且也影響四川商人和自治的膠東做生意。
Advertisement
至於安置費,鄧名認爲應該由縉紳議院付出,不過這件事需要鄧名來牽頭,因爲縉紳議院對自己的土地和招安以外的事都漠不關心。
“看起來,只有繼續在膠東維持海令了。”鄧名開始遊說縉紳議院繼續執行清廷的海令,因爲清廷在遷界海的同時,也免去了這些地方的賦稅。
“扶清滅明軍的宗旨是效忠朝廷,既然海令是聖旨,那當然要繼續執行,不然不就是叛賊了嘛。”鄧名把那些住在距離沿海地區比較近的縉紳們召集起來,給他們進行員:“既然海令要繼續執行,那麼自然這些地區不能稅,即使縉紳議院也不能稅,而且海都了,那當然沒有漁民或是海貿。”
簡而言之,如果有一些縉紳組織人手去海區種地、捕魚,自然都是免稅的,甚至就是建立工廠,從事海貿,比如參與鄧名的軍火和食鹽買賣或是參與翡翠和象牙加工,當然也不用納稅。
猜你喜歡
-
完結2240 章
宰執天下
宰者宰相,執者執政。 上輔君王,下安黎庶,羣臣避道,禮絕百僚,是爲宰相。 佐政事,定國策,副署詔令,爲宰相之亞,是爲執政。 因爲一場空難,賀方一邁千年,回到了傳說中“積貧積弱”同時又“富庶遠超漢唐”的北宋。一個貧寒的家庭,一場因貪婪帶來的災難,爲了能保住自己小小的幸福,新生的韓岡開始了向上邁進的腳步。 這一走,就再也無法停留。逐漸的,他走到了他所能達到的最高峰。在諸多閃耀在史書中的名字身邊,終於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643.5萬字8 96940 -
完結10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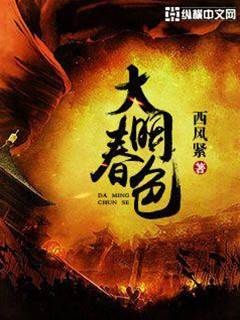
大明春色
大明初年風雲激蕩,注定要身敗名裂、被活活燒死的王,必須要走上叛天之路。恩怨愛恨,功過成敗,一切將會如何重演?
273.4萬字8 7161 -
完結5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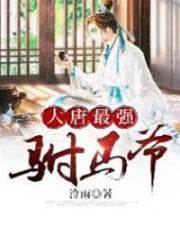
大唐最強駙馬爺
一覺醒來,魂穿大唐。悲摧的杜二少,開局就麵臨著兩個選擇:沿著曆史發展軌跡,迎娶公主,幾年後被李二宰掉;拒接聖旨,不當李二的女婿,麵臨抭旨重罪。失勢的杜二少,拒絕李二聖旨,被貶幽州城守大門。幽州城破、百姓遭殃。關鍵時刻,杜荷趕到,以一已之力,力挽狂瀾,殺退突厥五萬前鋒大軍。浴血奮戰、一戰成名。討伐突厥、橫掃北方;打服高麗,還大唐百姓一個安定、平和的生存環境……
106.5萬字8 369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