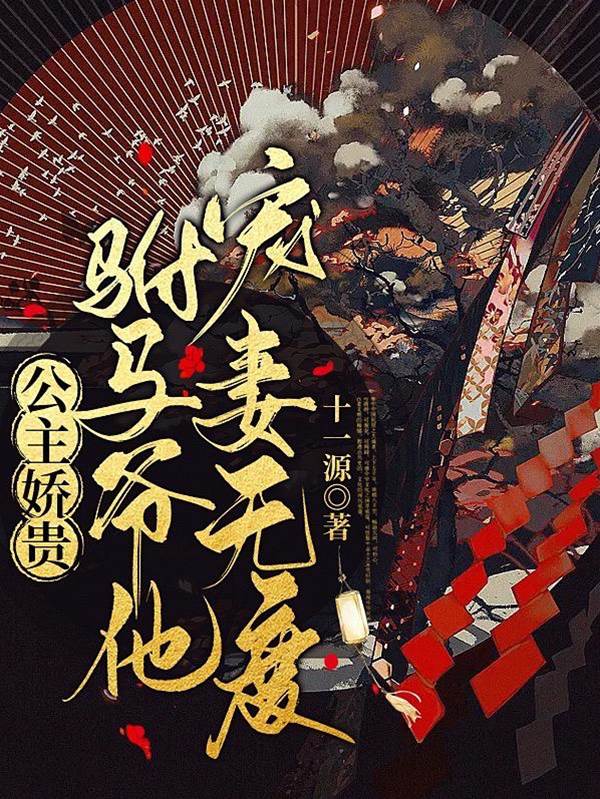《我又不是你的誰》 065 最迷人的最危險
看見沈寰九這樣,我實在難極了。
沈寰九納我懷,親吻我的頭髮後說:“今晚我給你做飯好不好?”
那聲音簡直好聽到不行,我的也變得和浮躁。可心就跟鋼化玻璃一樣,碎了一角就碎了全部。
我無聲無息的從他的懷抱裡而去,抱著歪著頭癡迷地看了他好一會。
到了現在,沈寰九其實沒有義務對我這麼好。一個男人究竟要有怎麼樣的懷才能容忍這麼多。
“我今天閒了一天,還有很多事沒做呢。”我很小聲地說著,像是輕嘆。
但其實現在養場的規模和運作和以往大不相同了,活累活都有人做,就算我不在短期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
圖把眼神去,我扭頭看向正前方。
下很快被輕輕住,沈寰九不依不饒地說:“我在留你,別裝傻。”
我擡頭看他,調皮地笑了笑:“不管怎麼說我還沒離婚呢,去你家,不合適吧?”
“我沒有在和你商量。”他神嚴肅,起提起我拽著往回走。
我的指間是他的手指,他握著很,大有一種再不會鬆開的架勢。
我被帶到自己住了幾年的別墅,所有的一切都沒有變過,還是原來的樣子。
我的拖鞋,睡,牙刷牙杯,全都還在。
“先墊墊肚子。”沈寰九拿了塊速食披薩給我。
我真了,從早到晚還沒吃過什麼東西呢。
拿了它,我做到沙發上,沈寰九帶上圍兜走進廚房忙和。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在這裡醒來下樓,看見沈寰九在爲扶稻做飯,時過境遷後,他在爲我做飯。
我往廚房的方向,雖然不見什麼,但腦袋裡卻很容易就想起沈寰九做飯時的作。
Advertisement
他把飯菜端出來是一個小時後的事,因爲肚子我吃的特別香,更何況是沈寰九做的飯,吃進里的覺怎麼可能一樣?唯一的憾是疼的難,鹹鹹的菜輕皮子就跟在醃似的。
“工作太忙,一般都在外面吃,好久沒做飯了。”沈寰九給我夾菜。
我咀嚼的作慢下來,擡起眼皮看他。
沈寰九說:“三歲,明天一早就準備下起訴離婚的事。”
我低頭:“這個時間點還不合適。”
現在沈寰九的前途很不錯,我這個災星這會離婚又會不會給他帶來新的災難。
“你要是擔心我,大可不用。你現在這樣子纔會讓我很不好。”頓了頓話,沈寰九輕描淡寫地說:“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回去,但明天早上你會見到陳浩東的。”
聽見這句,我狠狠一激靈。
我怎麼會不明白沈寰九對陳浩東的恨意,就算我沒有牽扯其中,是骨灰的事就足夠讓沈寰九把他給撕了。
他能忍到現在,一方面是時機不對,另一方面或許還有別的原因,我不知道。
“別老開這種玩笑,聽多幾次我會當真。”我悄悄著氣。
沈寰九看我一眼,依舊不鹹不淡地說:“狗急了還會跳牆,何況我是個有有的人,是不是玩笑……你今晚回他那去試一試。”
他放下飯碗,作緩慢地收拾著桌前的食殘渣,拿著碗筷說自己吃飽了。
我是個不太忍心浪費糧食的人,碗裡的飯和桌上的菜最後都被我吃進了肚子裡。
“去洗個澡,我帶你出去放鬆下。”他已經洗過澡,換過服,還赤著腳,高大如神的站在我面前。
我下意識看了下牆壁上的掛鐘,晚上八點了,平時這個點陳浩東應該差不多回家了,但我的手機沒有響,也就是說他還在外面。
Advertisement
額頭忽然一陣疼,是沈寰九用手指彈了下。
他以一種近乎命令式的口吻說:“什麼都不要想。”
除了報紙上的報道,我其實並不十分清楚度近一年的時間裡沈寰九經歷了多,更不會意識到屬於沈寰九的時代快來臨了。
就這樣,他帶我出了門。
北京最熱鬧的三里屯是酒吧的天堂。形形的就把都聚集在這裡,夜幕被無數霓虹撕碎,熱鬧的街市無一不在彰顯這座城市的繁華。
沈寰九帶我走進一家,他的手從頭到尾都牽著我。
起初我以爲只有我們兩個人,可到了卡座才知道這裡早就有個局。
真皮沙發上坐著四五個男人,其中有兩個外國人,一個泰國人,剩下的一個是中國人。
這些人看見沈寰九帶著我出現,臉上的表別提多驚訝了。
沈寰九用英文向他們介紹:“sheismywife.”
低啞的聲線搭配標準的口音讓他這句話尤爲蠱。
我愣了下,他是在說我是他太太。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那幾個男人就聳肩,走過來和我擁抱。
“三歲,他們是我新的朋友。”沈寰九給我介紹,然後就拉我座。
我有種無地自容的覺,這幫人開口閉口用英文喊我沈太太,如是一種對我的吞噬。
有人取笑:“難怪有小道消息說你婚,看來是真的。”
我心都揪起來。
沈寰九看我一眼,像是對待孩子似的用手在我腦袋上了兩下,用英文說:“不行嗎?”
泰國人搖頭。
外國人繞繞頭髮說我面,然後就指著我問是不是前段時間報紙上大肆報道的最近養業最有影響力的青年企業家。
Advertisement
“yes。”沈寰九從容地答,順勢拿起酒杯喝了口酒。
他的朋友們提出要和我合影,沈寰九用手擋住我的臉,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我是個小氣的傢伙,只能和我拍。”
然後的結果可想而已,他的朋友們要他罰酒。
沈寰九二話不說連續幹掉了三瓶。
他的朋友們上去跳舞,卡座只剩下我和他。
“都是和你生意上有合作的人?”我挪了挪位置,離他更近。
沈寰九很自然地出手臂搭放在我後面的靠墊上,他的手指有一下沒一下在我後背撓著,很曖昧。
“只是朋友。”沈寰九低笑了幾聲:“那個泰國人揹著好幾出大案,最近在中國小住。”
我嚨頓時跟被卡了什麼似的,語聲有些不上不下。不管我是不是他的誰,哪怕作爲朋友,我也不免提醒道:“不要和太複雜的人往吧,不是好事。”
沈寰九的手指在我後面輕輕打著節拍:“我有分寸。”
他眸似星夜,拿起酒瓶往杯子裡倒了杯酒,一飲而盡。
放下酒杯時,他一下就把我拽到他懷裡,我了子想起來,他用力氣將我按到,我的腦袋被迫臥倒在他疊起的上。
他低頭說:“這裡很黑,沒人會看見。”
氣氛無端因他似笑非笑的話變得沉重起來。
我們就像兩個正在的人,冒著道德和人的譴責大玩特玩著刺激。
我和浮躁的無不在掃清我自己的理智,淡淡的酒氣環繞在周圍,伴隨著刺激的音樂和整個令人淪陷的氛圍,我竟然就這麼臥在他上,反而越來越安寧。
沈寰九玩弄著我的頭髮,我能覺到有時候髮在他手指纏繞一個圈,有時候又是一順到底。
Advertisement
他作輕,像極了一種的挑逗。
這是和他相差八歲的陳浩東所沒有的。
後來,沈寰九的朋友們回到位置,我起子坐正。
沈寰九說要去下洗手間,拜託他的朋友們照顧我一下。
一個熱的外國男生邀請我跳舞,非常紳士的衝我出手。
我知道中西文化的差異很大,西方男人不理解東方的害。他們會覺得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
我著頭皮說自己不太會跳舞,男人不以爲然地說願意教我,於是我只能點頭。
我一隻腳才踏進舞池,雙眼就發了直。
陳浩東和一個帶了口罩的生在舞池中肆意的抱在一塊,我看見陳浩東臉上的笑容,那是在我們婚後難得會有的東西。至我已經完全忘記陳浩東上一次這麼笑是在什麼時候。
我認出了那人,是向小沒錯。
外國男人把手搭放在我肩膀上問我怎麼了,我用蹩腳的英文說有點不舒服想走。但向小卻眼尖地看見了我。
沒了早上最初見到我時的膽怯,上挑著眉,一臉勝利者的姿態,我想陳浩東肯定和說了什麼話纔會讓這麼大膽。
陳浩東瞥向我,先前的那些笑容頃刻間然無存。他就跟見了鬼似的鬆開向小的腰,又看了看我側的外國人。二話不說衝過來一拳頭就招呼了他。
沈寰九的朋友毫無準備下一拳頭被悶倒在地上。舞池裡的人紛紛逃竄,站在較爲安全的位置看著我們。
“扶三歲,你他媽搞外國人!”陳浩東像是抓翅膀似的把我兩隻胳膊扭到了後,疼的我淚花都要翻騰了。
我忍著疼痛,極度冷漠地說:“陳浩東,別說是外國人,我就是找鴨子也比和你睡乾淨。你知道嗎?我現在看見你就想吐。你有什麼資格衝我發火,什麼資格!”
陳浩東的眼睛裡也很溼潤,他就跟了天大的委屈一樣看著我說:“扶三歲,就他媽憑我們結婚了。就憑……你是我最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220 章

她是司爺心上霜
被逼嫁給癱瘓毀容的霍三少,全城的人都在等著她鬧笑話,誰料拿了一副爛牌的她卻出了王炸。“先生,有人說三少奶奶打扮寒酸。”司玄霆:“把這些珠寶送過去任她挑,就說是老公送的。”“先生,三少奶奶被炒魷魚了。”司玄霆:“把這間公司換她的名字,就說是老公給的。”“先生,有人罵少奶奶外麵有野男人。”司玄霆拍案而起:“胡說,她的野男人就是我。”
39.1萬字8 26042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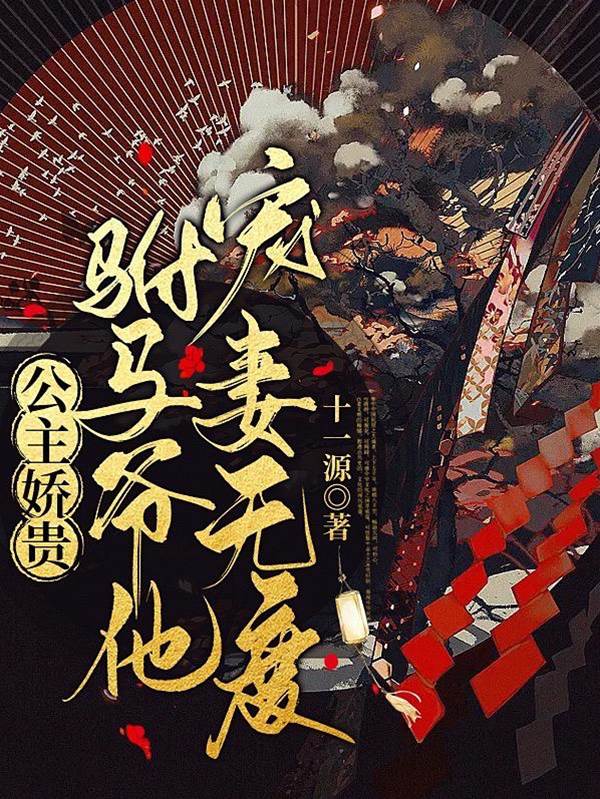
公主嬌貴,駙馬爺他寵妻無度
【1v1 、甜寵、雙潔、寵妻】她是眾星捧月的小公主,他是被父拋棄的世子爺。幼時的他,寡言少語,活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是小公主一點一點將他拉出了那個萬丈深淵!日子一天天過,他成了溫文儒雅的翩翩公子,成了眾貴女眼中可望不可及的鎮北王世子。可是無人知曉,他所有的改變隻是為了心中的那個小祖宗!一開始,他隻是單純的想要好好保護那個小太陽,再後來,他無意知曉小公主心中有了心儀之人,他再也裝不下去了!把人緊緊擁在懷裏,克製又討好道:南南,不要喜歡別人好不好?小公主震驚!原來他也心悅自己!小公主心想:還等什麼?不能讓自己的駙馬跑了,趕緊請父皇下旨賜婚!……話說,小公主從小就有一個煩惱:要怎麼讓湛哥哥喜歡自己?(甜寵文,很寵很寵,宮鬥宅鬥少,女主嬌貴可愛,非女強!全文走輕鬆甜寵路線!)
21.6萬字8 12884 -
完結133 章

霍總請節制,林總監不會跑
【互生情愫、男女主都長嘴、雙潔】衿貴狠厲的霍氏掌權人霍南霆vs實力與美貌并存的珠寶設計師林朝朝。 倆人相遇于國外一場風雪。 不久,林朝朝回到國內入職霍氏集團,倆人再次相遇。 自從男人確定心意后,就主動出擊,強勢入駐她的世界。 得到女人同意,倆人偷偷的開啟了沒羞沒臊的日常生活 直到霍南霆用委屈巴巴的表情說:“林總監,該給我個名分了。” 倆人官宣。 在數月后的婚禮上,林朝朝對他說:“恭喜霍先生,你有娃兒了。” 男人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再后來 男人表情嚴肅地正在開會,懷里的小奶包直接打斷他:“爸比,我要噓噓....”
24.3萬字5 135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