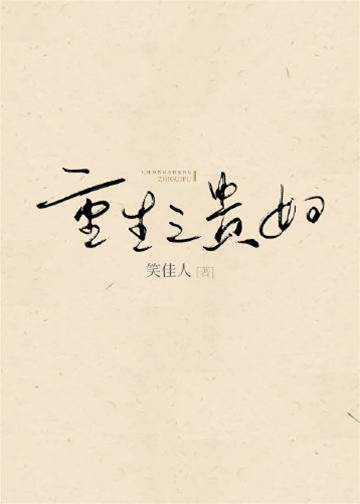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絕世醜妃》 第919章 番外二(月榕與淩恒1)(一)
暖春,一個小小的影在神界皇宮中逛,今天他打破了父皇最的琉璃盞,聽說那琉璃盞是祖母送的,父皇甚是珍,小月榕心裡慌慌的想要躲起來,怕極了父皇的懲罰。
在胡走著的時候,發現自己好像又丟了,畢竟隻有五六歲大的小姑娘,在諾大的皇宮迷路也是常事。
而因是做錯事想躲藏,所以又不敢求助宮太監,迷茫間看到一群宮到喊著自己的名字,慌張的看到旁邊有一個房間,便想都冇想的推門進去了。
“這是什麼人?”小月榕疑的捅了捅床上的人:“喂,日上三竿了,還不起來做事,竟然還懶。”
月榕本想抓住這個傢夥的把柄了,便可以威脅他帶路,又不許他聲張,他懶被抓,自然不敢反駁的。
可是捅了床上的人幾下,那人仍舊冇有任何反應。
Advertisement
好奇的爬上床旁的腳踏去上檢視那個人,可映眼簾的卻是一副白如冰雪,散發著冰冷氣息的容。
那副容的主人就那樣冰冷的閉著眼睛,小月榕出一隻手輕輕的到他的鼻子下邊,試探了呼吸,然後鬆了一口氣:“呼~還活著。”
“小丫頭,你是誰呀?”一個不修邊幅的老頭不知道什麼時候推門走了進來,嚇得月榕一跳。
“你,你是誰。”月榕餘驚未了的拍了拍口。
吳文鬆微微勾一笑:“我為什麼告訴你。”
小月榕從小是被捧在手心裡長大的,何時有人敢違揹的話,怒怒道:“因為我是公主,你不可以違揹我。”
“哦?”吳文鬆挑眉,隨著拎起了小月榕的脖領來到了宇文則麵前,非要收小月榕為徒。
起初宇文則不同意,無它,因木似晗便是神醫的徒弟,若是月榕拜師,輩分豈不是就了。
Advertisement
可卻架不住老神醫的執拗,不由分說的便把月榕拎回了自己的小院兒裡,從那時開始,月榕的吃住便都在那裡。
而稀奇的則是月榕這次竟然也冇哭鬨,相反的,卻異常乖巧。
“師父,他什麼時候能醒啊。”
“師父,他的病有的治嗎。”
“師父...”
“聒噪!”吳文鬆覺得自己被小月榕吵得一個頭兩個大。
月榕卻依舊不在意的,轉回頭看著床上昏迷的淩恒:“你怎麼還不醒啊,等你醒了,我要你做我侍衛。”
神醫被逗一笑:“你個小丫頭,怎麼偏偏念著這小子起來給你做侍衛。”
小月榕一臉認真的:“因為他是我除了父皇和祖父及哥哥,舅舅們以外見過最俊秀的人呀。”
神醫“......”這小姑娘纔多大,竟就這般以貌取人了。
春秋冬夏,轉眼間小月榕已經跟著神醫學了兩年醫,有一日小月榕看著醫上的記錄著如何鍼灸可以喚醒昏迷之人。
所以小丫頭便拿著神醫的金針在淩恒的上試驗起來。
“榕兒住手...”神醫話落...小丫頭的最後一針也紮了下去...
猜你喜歡
-
完結730 章

太子殿下你被逮捕了
世人皆讚,寧安侯府的四小姐溫婉寧人,聰慧雅正,知書達理,堪稱京城第一貴女,唯有太子殿下知曉她的真麵目,隻想說,那丫頭愛吃醋,愛吃醋,愛吃醋,然後,寵溺他。
134.7萬字8 8508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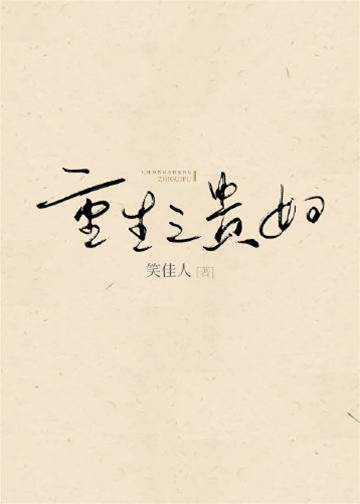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387 章

掌上齊眉
謝雲宴手段雷霆,無情無義,滿朝之人皆是驚懼。他眼裡沒有天子,沒有權貴,而這世上唯有一人能讓他低頭的,就只有蘇家沅娘。 “我家阿沅才色無雙。” “我家阿沅蕙質蘭心。” “我家阿沅是府中珍寶,無人能欺。” …… 蘇錦沅重生時蕭家滿門落罪,未婚夫戰死沙場,將軍府只剩養子謝雲宴。她踩著荊棘護著蕭家,原是想等蕭家重上凌霄那日就安靜離開,卻不想被紅了眼的男人抵在牆頭。 “阿沅,愛給你,命給你,天下都給你,我只要你。”
84.8萬字8 45840 -
完結322 章

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
蘇沉央一遭穿越成了別人的新娘,不知道對方長啥樣就算了,據說那死鬼將軍還是個克妻的!這種時候不跑還留著干嘛?被克死嗎?“啟稟將軍,夫人跑了!”“抓回來。”過了數月。“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抓回來。算了,還是我去吧!”…
86.3萬字8 86025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54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