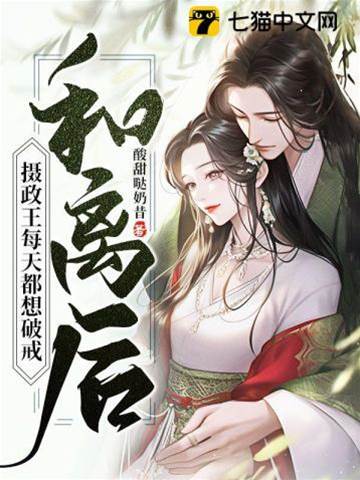《帝色撩人》 卷一:衣冠華陵,步步錦繡 第二百零七章 無罪開釋
欣賞著別人的琴音的同時,舉也在心中暗暗斟酌著自己的琴藝。
若是同樣的曲子,以自己現在的水平能達到何種程度?
思來想去,沮喪地嘆了口氣。
與這些琴士比起來,彈出的大概不是什麼綠水,而是窪中之泥,簡直拙劣不堪。
這般程度,若是當初真頂著師父的名頭四張揚,豈不是損了師父琴癡的名譽?
想著想著,舉又不由得覺得好笑。
那鶴亭溫公對師父實在太過執著,在西山上不過聽了個微末之音,便將嶽淵渟這個所謂的學生排在了琴士之列。
在舉看來,就是排在四百九十位琴師的末位,都是大大擡舉了。
悄悄瞄了衡瀾之一眼,視線落在他的手上。
抓?
還是不抓?
嗯,抓!
猶豫了片刻,一把抓過了對方的手,在那溫暖寬厚的手掌心寫字。
“首共曲之後還有幾?”
衡瀾之看著自己的掌心,挑眉淺笑,同樣在的手心寫道:“一,自選曲。卿卿,琴之一道,戒急戒躁。”
Advertisement
寫完之後,便將的手握,掩到了寬大的袖下,止再做小作。
舉垂下眼簾,看著被握住的手,默默抿了抿脣。
臆間,彷彿有什麼在悄悄地流淌著,躍著。
……
京兆尹府。
“本府現已查明,罪子蔡珩,倚仗家勢,強取豪奪,染指民劉氏,並以暴力致其死亡,即刻著令逮捕,押大牢,以待後審。至於蔡珩指證,鬼醫仇景泓誤診毒殺劉氏一案,乃蔡珩因私怨而構陷嫁禍,仇景泓實屬清白,無罪開釋。”
後衙,京兆尹上遷心事重重地下了帽。
“如此定案,工部蔡侍郎那頭便算是徹底得罪了,我這左右逢源的爲之道算是破了。”
邊的周幕賓輕聲勸:“大人,爲哪有兩全的時候?這次大人雖然得罪了工部侍郎,可同時不也賣了另一邊面子?跟那邊相較,工部侍郎又算得了什麼?”
“哎!”上遷長嘆一聲,道:“你懂什麼?若僅僅是一個工部侍郎,本又何必發愁,可那工部的後頭還有一個忠睿侯,華陵楚家啊!”
Advertisement
隨著宣判一下,仇景泓終於走出了京兆府的大牢。
著耀眼的,他恍惚有種再世爲人的錯覺。
“究竟是怎麼回事?”
雙目適應了,仇景泓低喃了一聲。
他在這京華之無權無勢,此次劫禍,對方是工部侍郎之子,他以爲自己再也出不來了。
現在這般結果實在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帶著滿腹疑,他準備返回自己的醫館。
途徑一條僻巷,錚然之聲豁然響起,四個手持刀劍之人頃刻之間便將他攔巷中,氣勢洶洶,奪命而來。
“你們究竟是何人?”仇景泓險險避過一擊,大聲喝問。
只聽其中一人冷哼道:“哼!怪你不該得罪貴人!”
就在冰冷的長劍即將砍向仇景泓時,一道黑影躍出,“叮”的一聲打開了長劍。
瞬間,便又有四個黑人加了戰圈。
先前四人大驚異。
“何人竟敢與侍郎府作對?”
然而,黑人並不打算與他們多糾纏,甚至沒有隻言片語,招式乾淨利落,直取要害。
不過片刻,四人便已全部倒地。
Advertisement
其中一個黑人下令道:“速將理乾淨,不可留下蛛馬跡!”
“你們是何人?又爲何要幫我?”
仇景泓腹中疑更甚,如果之前還只是猜測,那麼此刻他便能確定。
有一個比工部侍郎府更有權勢的人在背後幫他!
黑人向他抱了一拳,淡淡道:“先生不必顧慮,我家主子對先生絕無惡意,蔡侍郎爲給他的兒子罪,恐怕還會對先生不利,先生最好還是離開華陵城一段時日,等到蔡珩徹底伏法再回來不遲。”
“你家主子是……”
仇景泓還想追問,四個黑人卻已經拖著迅速消失在了僻巷盡頭。
“到底是誰在助我?”
猜你喜歡
-
完結1410 章

傾世獨寵:娘娘又出宮了
一頓野山菌火鍋,沐雲清成了異時空的王府小姐,父母早亡哥哥失蹤奶奶中風,她被迫開始宅鬥宮鬥。 對手手段太低級,她鬥的很無聊,一日終是受不了了,跑到了蜈蚣山決定占山為王,劫富濟貧,逍遙快活。 可誰知第一次吃大戶,竟是被燕王李懷瑾給纏上了。 山頂上,沐雲清一身紅衣掐著腰,一臉怒容:“李懷瑾,我最後一次警告你,我此生隻想占山為王與山為伴,王妃王後的我不稀罕!” 在戰場上煞神一般的燕王李懷瑾此時白衣飄飄站在下麵,笑的那個寵溺:“清清,你怎麼知道我還有個彆名叫山?” 沐雲清氣結:“你滾!”
267.3萬字8 34344 -
完結382 章

深宮策·青梔傳
她的眼看穿詭術陰謀,卻不能徹底看清人心的變化; 他的手掌握天下蒼生,卻只想可以握住寥寥的真心。從一個為帝王所防備的權臣之女,到名留青史的一代賢後,究竟有多遠的距離?一入深宮前緣盡,半世浮沉掩梔青。梧桐搖葉金鳳翥,史冊煌煌載容音。
77.2萬字8.18 25607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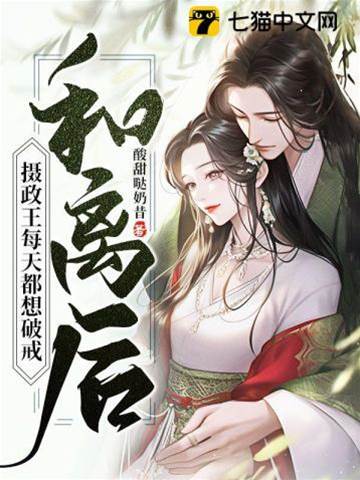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