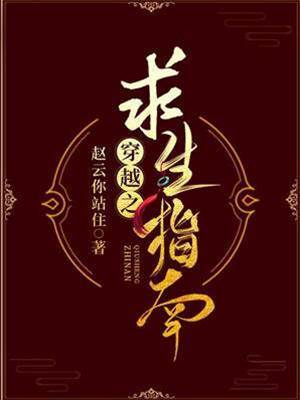《將軍家的丫頭》 第十章醉酒
“你喝這樣!難不我是煞星?”
酒家見他們用的酒多,又都是世家子,早備好了醒酒湯,命使婆子送了進來,兩人的小廝合力給王子瑜灌了下去,又抬上馬車,還沒走到王家府門所在的街上,王子瑜就吐了,不僅吐了自己一,還濺到褚翌上許多,馬車里頭也到都是污穢酒氣。
褚翌著一張臉,聲音比寒冬還寒冬:“回褚府。”
又了王子瑜的小廝過來吩咐一通,回家好給舅舅舅母跟外祖母報信。
褚翌本想將人往錦竹院帶,蹙眉一想,錦竹院里頭個個的結母親,若是給母親若是知道子瑜大醉,不得要訓斥自己一頓,想到這里,直接吩咐小廝:“把馬車趕進書房小院,我今晚在那里住一宿。”
小廝只求這祖宗平平安安的到家,別再起其他的幺蛾子,對于九爺要宿到哪里是沒有一點意見的,往常九爺還經常宿在老夫人的院子里頭呢。
馬車進了小院的時候,天已經半昏黃,隨安正從大廚房那里領了自己的晚飯來,的飯食不錯,有兩個大白饅頭,一碟子小咸菜,還有一份量足足的老廚白菜。
初冬的白菜,瘦正好的五花還有泡的的皮,看著都直流口水。
主廚的大師傅家里有個跟隨安差不多大的閨,長得白白胖胖,一個頂隨安兩個,因此大師傅看見隨安便相當憐憫,飯菜都要按一個半人的量給。
耳房小小的,爐火比燭還要亮,正將白菜放到小鍋里頭熱上,院門的喧囂聲嚇了一跳,慌忙起出去看。
褚翌從馬車跳下來,指揮后兩個小廝抬了王子瑜下來,見了隨安,隨口就道:“你去收拾下書房,今晚我住在這里。”
Advertisement
書房的隔間倒有一張大床,隨安從箱籠里頭拿了兩床棉被,褚翌嫌棄道:“有沒有曬過?”
“九爺,奴婢都是五天曬一回。”隨安手腳麻利的端了炭盆,趁機回到自己小窩把菜從爐子上端下來,免得把白菜烤焦了。
小廝們抬了熱水進來,隨安連忙垂頭出去,這伺候沐浴可不是的活兒,也干不了。
褚翌先讓王子瑜洗漱了,等他上了床,沒等小廝熄燈呢,一個鯉魚打坐直了——王子瑜雖然上香噴噴的沒有酒味,但一呼吸,噴出來的酒味簡直酸爽。
隨安好不容易得了空,慢吞吞的擺好了晚飯,見爐火快要熄滅了,起去小櫥子里抓了十來個栗子,剛埋進去,褚翌來了。
“你在吃飯?吃的什麼飯?”
隨安唯恐他說出諸如“豬食”之類的倒人胃口的話,忙拿了一旁的蓋子將盤子蓋住。
褚翌卻直接走過:“吃的什麼還不許我看?”掃一眼,皺眉:“豬食!”
隨安:“……”
甭看褚翌說是這麼說,可他這會兒看見飯菜,才想起自己今日兒就沒正經吃過什麼東西。
所以雖然仍舊覺得白菜看上去像是被狠狠的過一般無打采,也有點徐娘半老巍巍,但還是坐了下來,嫌棄筷子是隨安用過的,在旁邊的茶水杯子里頭涮了兩下,就自顧自的拿起爐子旁邊烤的脆的饅頭,就著白菜條吃了起來。
直到他吃了兩口,隨安才從震驚中反應過來,慌忙道:“九爺怎麼能吃奴婢們的飯食?您了?奴婢去大廚房,讓大師傅現做些來吧?”
褚翌瞪:“難不我還要忍著等你提飯菜回來?”
隨安默默的把那句“奴婢給您下碗面條”給咽了回去。
Advertisement
褚翌吃完了飯,大刀金馬的往隨安的床上一坐:“今晚我就睡這兒!”
隨安突然臉一紅。
褚翌一見臉紅明白想歪了,頓時惱:“你想什麼呢?小爺豈是你能染指的?還不滾去伺候王爺?!”
隨安心里大呼冤枉,任何一個男人這麼來一句要睡自己的床自己的被窩,能不臉紅?再說,就是想染指,也不會想染指個晴不定的爺!說實話,九爺這樣的可不是良人,從小生在富貴鄉里,人窩里,這樣的九爺,上趕著請染指也不愿意!
臉上的紅暈迅速褪下,輕聲道:“那奴婢把您的鋪蓋拿過來。”
很快恢復了正常,褚翌心里反而有些不是滋味,他當然不是稀罕這臭丫頭,只是,怎麼說呢,反正就是心里燥燥的,怎麼做他都看不順眼。
隨安不等他回話就轉出了屋子。
書房里頭兩個守夜的小廝蹲坐在地上打盹。
王子瑜已經把兩床鋪蓋都卷在下呼呼大睡。
隨安只好開了箱籠重新拿了一床出來,這是最后一床了。
褚翌正百無聊賴的打量的屋子。
屋子很簡單,靠西的墻上掛了兩副畫。一副田園圖,上頭一顆樹,幾塊石頭,樹下一只老母帶了一群小低頭吃蟲,老母肚子大的跟懷胎十月似得,小們眼瞅著蟲子不敢下,畫法拙劣。
另一幅卻是仿的前朝大師的名畫竹報平安,竹子也還罷了,就那竹筍張牙舞爪的,不仔細看還以為哪里的大閘蟹爬出來嚇唬人呢!
這兩幅畫都沒有落款,裝裱的水平也不是一般的差。
見隨安抱著被褥進來,褚翌仰著下問:“這兩幅畫是你畫的?”
隨安答:“是。”心里的小鐵人默默的把盔甲拿了出來,擋在前。
Advertisement
“嘁!這水平,看著眼疼!”
隨安不為所。
伺候的這位爺,院子里頭的丫頭折損率那是全上京都數的著的。本來麼,不好的丫頭都進不了他的錦竹院,能進了錦竹院的丫頭哪個不是心高氣傲?這兩個高在一起?
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哪怕一公和一母!”,要是想過安穩的日子,必須不能為老虎。
整理好床鋪,把自己的鋪蓋放到一邊:“奴婢過去照看著表爺了。”
褚翌從鼻子里頭哼了一聲算是答應,扯了被子過來睡。
隨安重又進了書房,隔間里頭一子酒氣,重新點了兩個炭盆,然后散開一半的帳子,開了半扇窗戶,過了多半個時辰總算把這酒味散了去。
王子瑜的呼吸也更舒暢了些。
小院那邊有人砸門。
兩個小廝了,沒睜開眼,又繼續睡了過去。
隨安打著燈籠去開門,一邊走一邊想或許是老夫人那邊不放心打發了人來看。
開門一看卻不是。
林頌鸞披著一件薄如紙的斗篷,笑如薔薇花盛開:“聽見你這邊還有靜,想是沒有睡著吧?我也睡不著,就過來看看能不能借幾本書……”
隨安笑道:“林姑娘想看什麼書?”
林頌鸞眼珠子一轉,“一時也說不上來,我能自己選選嗎?”
打探書房的心思幾乎昭然若揭,隨安在心里嘆了口氣,面上笑容不變:“這卻是不巧,九爺跟表爺今日都歇在書房,實在不便請林姑娘進去。”
林頌鸞還要說話,遠長廊的拐角拐過一群人來,前頭的婆子打了兩只燈籠,說笑聲打斷了們的對話。
走到近才看出是老夫人邊的大丫頭紫玉。
紫玉笑道:“好丫頭,知道我過來,先迎著了。”年紀長,又自詡跟隨安有共同的,所以說笑起來很是親熱。
Advertisement
紫玉說完才看見旁邊杵著的林頌鸞。不過只這一眼就知道這是誰了,不是奴婢的穿著,卻又裝寒酸,該是林先生的家眷。
心里有了底,面上卻笑著問隨安:“這位是?”
大家都是明白人,揣著明白裝糊涂也不嫌累,隨安又要嘆氣,一下子想起自己今日已經嘆了不,連忙剎住,嘆一口氣活一年,不能早早完蛋。
“這位是林先生的兒林姑娘。”笑著向紫玉介紹。
又對了林頌鸞道:“林姑娘,這是老夫人邊服侍的紫玉姐姐。”
林頌鸞火氣一下子就上來了,這介紹人都是先為尊貴的介紹,隨安先把介紹給了紫玉,那就表明隨安認為紫玉的地位比高。紫玉有什麼地位?不過是一介奴婢!可是良民小姐!
這樣想,卻沒有考慮到自己現在是借居在褚府,紫玉是主家的奴婢,有道是客隨主便,隨安這樣介紹其實并沒有什麼問題。
紫玉剛才占了上風,并不咄咄相,笑著行禮:“林姑娘好。”
林頌鸞坦然了,端了架子輕輕頷首:“原來是老夫人跟前的紫玉姐姐,頌鸞這廂有禮了。”說完才要行禮。
紫玉連忙避開,兩個人寒暄一陣子,紫玉才對隨安道:“老夫人不放心,打發我過來看看。”
林頌鸞見狀告辭。
隨安陪了紫玉先看了王子瑜,王子瑜臉紅潤,睡可,紫玉微微放心,轉眼看見兩個雖然已經站起來,可還迷迷糊糊的兩個小廝,正要教訓,被隨安拉住手,笑著小聲道:“姐姐,九爺怕委屈了表爺,讓我夜里給表爺值夜,他歇在那邊屋里了,我陪著姐姐過去看一眼,說不定九爺還沒睡著呢。”
猜你喜歡
-
完結136 章
黑月光拿穩BE劇本
城樓之上,窮途末路後,叛軍把劍架在我脖子上。 他大笑問澹臺燼:“你夫人和葉小姐,隻能活一個,你選誰?” 係統看一眼哭唧唧的葉冰裳,緊張說:宿主,他肯定選你。 澹臺燼毫不猶豫:“放了冰裳。” 係統:哦豁。 我:哦豁。 係統安慰道:澹臺燼肯定是知道你家大業大,暗衛們會救你。 澹臺燼確實這樣想,不過那日後來,我衝他一笑,在他碎裂的目光下,當著三十萬大軍,從城樓上跳了下去。 連一具完整的屍體都冇留給他。 這是我為澹臺燼選的be結局。 景和元年,新帝澹臺燼一夜白髮,瘋魔屠城,斬殺葉冰裳。 而我看透這幾年的無妄情愛,涅槃之後,終於回到修仙界,今天當小仙子也十分快活。 #據說,後來很多年裡,我是整個修仙界,談之色變,墮神的白月光#
44萬字8.33 16307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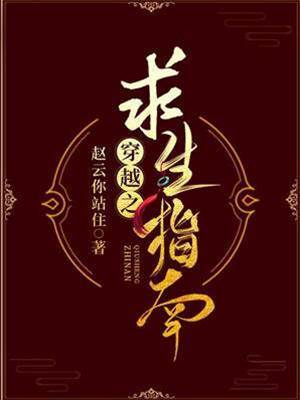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