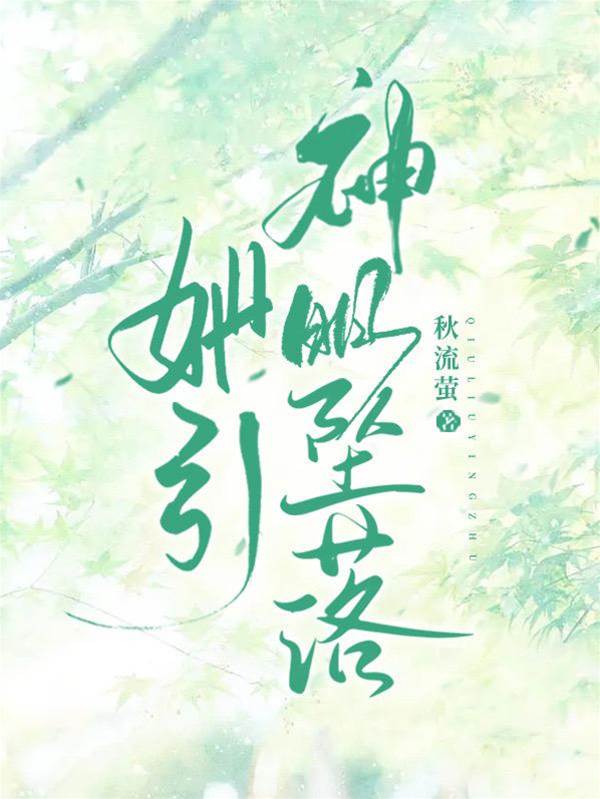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第一名媛,總裁的頭號新妻》 番深723米:然后她伸手把他唇間的煙取下,踮起腳尖吻了上去
<=""></> 再過了十幾二十分鐘游艇就開回了信號區,薄錦墨一手抱著另一只手面無表的查看手機,發了條短信給郝特助讓他在海邊附近找家合適的餐廳,等下了碼頭吃完早餐再送他們回去<="r">。
郝特助過了十分鐘給他回了地點和餐廳的名字。
簡單的吃了點東西,薄錦墨就開車回南沉別墅。
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幸好有七七一直在嘰嘰喳喳說的不停,才顯得一路上沒那麼冷清攖。
男人專心開車,俊的臉沉靜晦暗,基本不發一言。
盛綰綰托腮盯著他開車的側臉,過了好久才湊了上去,下抵在他的手臂上,小心翼翼的問道,“你昨天晚上沒有睡好嗎?”
等了將近半分鐘,才聽男人淡淡的回了一句,“很晚才睡,有點困。”
“哦,那要不然你靠邊停下車,我來開,你休息會兒。償”
“沒事,一會兒就到了。”
拉長著語調,又哦了一聲,但是腦袋始終靠在他的手臂上沒有離開,薄錦墨低頭看了的發頂一眼,任由這麼靠著,也沒說話。
到了南沉別墅區后,盛綰綰領著冷峻跟七七先下車,然后朝車里的男人道,“你先帶小硯進去,我送他們給晚安就回去。”
薄錦墨嗯了一聲,看著走到門前去按門鈴,才驅車繼續往前開了一段。
等盛綰綰回到家時,薄硯已經回了自己的房間在洗澡,男人站在落地窗前,一只手在袋里,另一只手夾著煙在,淡淡的青白煙霧繚繞在他周。
站在沙發旁看著他,抬手把外套了下來擱在沙發上,又挽起了袖子,站在原地看了他好久,直到男人一煙完掐滅了煙頭,又接連著點燃了第二,這才抬腳走了過去從后面摟住他的腰,連在溫熱堅實的背上,“你怎麼了,看上去不開心的樣子?”
Advertisement
其實知道,他不開心的理由其實大致能知道……是不小心把薄祈當他了,或者……他現在是薄祈?
可還是有種莫名的直覺,現在看上去孤獨落寞甚至帶著一點疏離的男人,是薄錦墨不是薄祈。
男人手把從背后拉到了懷里,薄上含著剛點燃沒幾口的煙,低頭看了一眼,把煙取了下來夾在指間,淡淡啞啞的道,“昨天玩了一天又不小心睡在地板上了,不上去洗個澡?”
連薄硯都跑去洗澡了。
盛綰綰仍然是抱著他的腰,仰著臉下抵在他的膛上,慢吞吞的道,“薄錦墨,你有什麼不開心的事……跟我說行不行?”
要是真的認錯了,也跟說吧。
有些心慌慌的,他昨天昨晚明明都好端端的。
他又低頭看一眼,將煙重新送到邊,吸了一口,薄跟鼻息間都隨著呼吸吐出煙霧,將他俊的臉熏染得有些模糊,更是分辨不清他臉上的笑,沒拿煙的手了的臉頰,眉眼深邃黯淡,角卻牽起了淡笑,“我能有什麼不開心的。”
盛綰綰抬起頭,蹙眉仔仔細細的看著他的眉眼<="l">。
然后手把他間的煙取下,踮起腳尖吻了上去。
干燥的煙草氣息混合著尼古丁的味道一起侵襲著的嗅覺跟味覺,扔了煙,雙手環住他的脖子,讓他把頭低下來一點,調更方便親吻的姿勢。
薄錦墨始終沒有。
任由拿走他的煙,任由環上他的脖子,再低眸看著吻上他。
就這麼干的親吻了好一會兒,盛綰綰見他半天沒有反應,有些惱怒的咬了他一口,再又委屈的看著他,“你不想親我?”
Advertisement
男人低頭瞥了眼被扔掉的煙,淡淡的問,“不怕親錯人?”
“你到底要不要親?”
盛綰綰手住他前的服,表愈發的委屈,“我都主親你了你還不理我。”
薄錦墨嘆了口氣,手又把拉進了懷里,下擱在的肩膀上,“今天沒心接吻,下次陪你吻好不好?”
靠在他的膛,著嗓子小心翼翼的問,“昨天不是你嗎?”
如果不是,那真的太糟糕了。
男人一把將打橫抱了起來,邊往樓上走邊淡淡的道,“你覺得是我還是不是我?”
他這麼說盛綰綰心底越發的沒底了,手臂環著他的脖子,額頭蹭著的下,委委屈屈的道,“那如果不是你的話,你跟我說吧。”
薄錦墨低頭看,心臟仿佛被一只手抓住,攥住,但他面上還是很溫淡,“傻瓜,我剛接了個電話,公司出了點事,所以心不好。”
盛綰綰覺得他這個慌說得毫無含量,但也沒有拆穿,只是靠在他的肩膀上,低低的問道,“那你要回公司去理事嗎?”
問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在樓梯下,他一直抱著上去,他才開口回答,“不用,想跟你待在一起。”
說這句話的時候一直看著他,但是薄錦墨并沒有看。
“你抱我去哪里?”
其實是知道他抱是回臥室,只不過按照平常的架勢他肯定會把按在床上肆無忌憚的狠狠吻上一通,能親多地方絕不放過一寸。
可他現在的樣子看上去,冷靜,還有淡淡的疏離,沒有一點想跟親近的意思。
盛綰綰覺得人有時候犯賤的,他平常膩著的時候偶爾煩的,可他這種這副狀態,又覺得心里不安想上去。
Advertisement
尤其是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什麼對不起他傷害他的事。
薄錦墨這樣的男人,怎麼可能會被輕易傷害。
“你一天一夜都沒有洗澡了,我抱你去浴室,你泡個舒服的澡,我去你書房拿筆記本理一點公司的事,你洗完找我。”
他把抱到了浴室,給放水,“你先服,我去給你拿服<="l">。”
盛綰綰看著他穿著一名貴休閑的服蹲在浴缸旁,手試著水溫,把放松的油的倒進去,又看了一眼,溫淡而耐心的囑咐,“滿了就泡澡。”
說完他就走出去,沒一分鐘就拿了一家居服進來,整整齊齊的放在架上。
整個過程中他都沒有跟有過眼神的流,甚至沒有正眼看過。
“薄錦墨。”
一直到他走到了浴室的門口,才徒然的開口住他,兩只垂落在旁的手攥了拳頭,“你要這麼莫名其妙的冷落我嗎?我做錯什麼你跟我說好嗎?”
嗓音帶著很明顯的委屈味道,甚至像是要哭出來了。
男人沒有回頭,淡淡的笑了下,“你不是勉勉強強才肯跟我在一起麼,怎麼才幾天的時間,就膩我膩得好像離不開我了?”
盛綰綰沒說話,他話里沒有指責,但還是覺到了那點味道。
說出來的嘲弄,或者是……自嘲。
莫名的覺得難。
很快,還沒等回話或者做出什麼反應,男人就再度溫和的出聲了,“泡個澡會舒服很多,我先去理點事,理完就來找你。”
他聲音很溫和,甚至堪稱溫。
但只聽出了冷淡。
薄錦墨帶上了浴室的門,離開臥室的時候又帶上了臥室的門,手握著帶上的門把,卻久久沒有松開。
Advertisement
他在門口站了好長時間,然后轉過去了的書房。
書桌上擺著一臺筆記本,但沒打開,走到的書架前隨手了一本書出來,又隨便的翻開了一頁開始看。
視線落在某個字眼上,開始看,一個字一個字的強迫自己看下去。
然后將字詞連句子,消化理解,然后把擁的堵在他腦子里的一切想法全都清空,趕走,只看書,強迫的把腦子里的緒下去,強迫的讓自己冷靜。
盛綰綰坐在浴缸里發呆。
最近他對太好了麼,好到已經不了他一點點的冷淡跟疏離。
前幾天才跟晚安說沒有他也能過得很好,可現在很心慌很不安,想出去問問他到底哪里錯了。
他不說,又怎麼會知道。
可覺得他現在不想見,他只想一個人靜靜的待著。
于是就一直泡在浴缸里,直到水都冷了下來。
穿好服還是沒忍住去找他。
薄錦墨就坐在的書桌前,低頭安靜的看著書,看上去很正常,正微微的松了一口氣,卻徒然見看到了那一煙灰缸的煙頭。<=""><=""><="">
猜你喜歡
-
完結1091 章

失憶后我成了法醫大佬
十三年前全家慘遭滅門,蘇槿患上怪病,懼光、恐男癥,皮膚慘白近乎透明,她成了「吸血鬼」,選擇在深夜工作,與屍體為伴;他背景神秘,是現實版神探夏洛克,刑偵界之星,外形豐神俊朗,愛慕者無數,卻不近女色。第一次見面,他碰了她,女人當場窒息暈厥,揚言要把他送上解剖臺。第二次碰面,她手拿解剖刀對著他,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具屍體。一個只對屍體感興趣,一個只對查案情有獨鍾,直到未來的某天——單宸勛:你喜歡屍體,我可以每天躺在解剖臺任你處置。蘇槿:我對「活的」沒興趣……
196.7萬字8.18 22956 -
完結1233 章
七零年有點甜
何甜甜一直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的人。人到中年,卻發現一直生活充滿謊言的騙局里。重回七零年,何甜甜在小銀蛇的幫助下,開始新的人生。換一個角度,原來真相是這樣!這輩子,再也不做睜眼瞎了。這輩子,再也不要錯過辜負真心相待的青梅竹馬了,好好待他,信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215.3萬字8 54157 -
完結877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
生日那天,深愛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卻是一場復仇。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了記憶,再也不是從前了深愛霍雲霆,死活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這個婚離定了!” 夏初薇:“離婚?好,明天就去,誰不離誰是小狗。”第二天,夏初薇敲開霍雲霆的門。“霍先生,該去離婚了。” 霍先生:“汪!”所有人都知道她愛他至深,但唯有他,他愛她多次病入膏肓。
157.9萬字8 6044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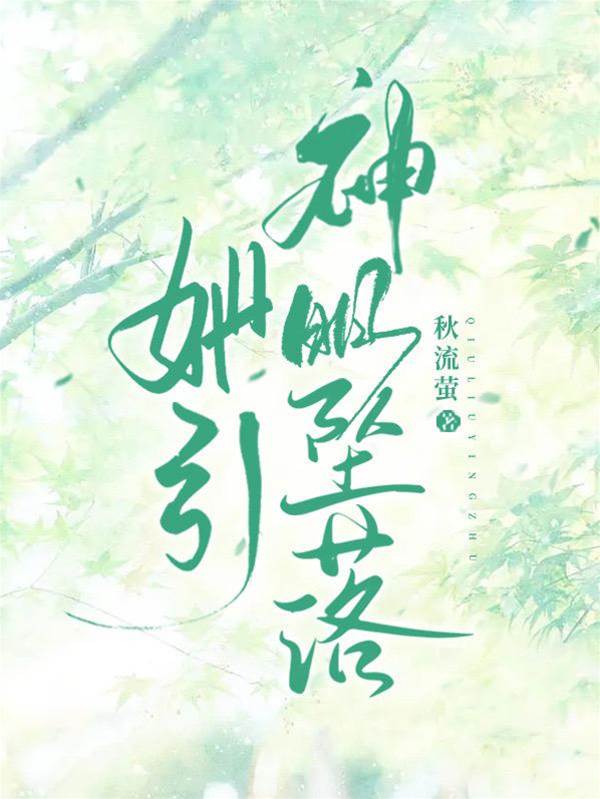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80 章

幸福不脫靶
他連吵架時擲出的話都如發口令般短促而有力:“不許大喊大叫!給你十秒時間調整自己,現在倒計時,十,九……” 她氣憤:“有沒有點兒時間觀念?需要調整十秒鐘那麼久?” 他是個很霸道的男人,對她裙子長度引來的較高回頭率頗有微詞:“你可真給我長臉!”見她呲牙笑得沒心沒肺,他板起來臉訓她:“下次再穿這麼短看我不關你禁閉。” 她撇嘴:“我是滿足你的虛榮心,搞得像是有損安定團結一樣。” 我們的小心願,幸福永不脫靶。
24.6萬字8 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