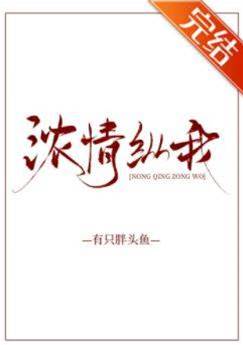《反派同窗他命帶錦鯉》 第59章
聞硯桐直在想, 這三天池京禧到底忙什麼去了。
池京禧慢慢撥開人群走來,他雙眸依舊黑得深沉,可似乎藏著疲憊在其, 沒有以往的氣神。
聞硯桐無意識的摳了摳手指的泥, 眼睛里本看不見周圍的人, 不控制的盯著池京禧。
孫逑和李博遠等人也趕到,來時已經聽說了些許容, 兩人的臉都黑得厲害。
東西,這是賊的行為。頌海書院作為舉國聞名的傳世書院, 絕不可能容忍書院里的學生做出這種行為, 不說賊是犯法的, 單是這消息傳出去, 也足夠世人笑話陣子了。
更何況的還是小侯爺的東西。
吳玉田就是知道這事的嚴重,所以才迫不及待的來了大半個書院的夫子,立地要給聞硯桐定個無法翻的罪。
他快步走到聞硯桐面前,橫眉瞪眼道,“聞硯桐!現在夫子們都過來,你的丑事已經敗了!還不快快把東西挖出來認錯。”
聞硯桐的視線從池京禧的上移開,落在吳玉田上時卻是冷冰冰的,個近距離的對視。
聞硯桐本該驚慌失措, 佯裝害怕的, 但現在心實在是不好,做不出來那麼多戲,于是冷著聲音問道, “我不過埋個小玩意兒,又沒有違反書院法規,也用得著這樣興師眾?”
哪知誤打誤撞的,吳玉田因為事敗之后故作鎮定,則更加自信,指著地上的東西道,“你埋的什麼東西,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嗎?”
聞硯桐慢慢站起來,回答道,“個盒子。”
周圍的人都盯著看,李博遠本想上去參與,卻被孫逑攔了下來,暗暗搖頭。
吳玉田冷嘲,“盒子里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Advertisement
聞硯桐與他對視,正想說話,卻聽聲大,“誰敢欺負我們小瘸子!”
眾人轉頭看,就見牧楊正著快速跑來,下子躥到聞硯桐面前,抬手推了吳玉田把,“怎麼又是你?!”
不知是牧楊手勁大,還是吳玉田板弱,直接被推了個跟頭,摔坐在地上。
傅子獻跟在后面,路跑的急,正微微氣著走來,拉了牧楊把,小聲道,“夫子都在,莫要沖。”
牧楊梗著脖子,“這姓吳的總是散播謠言,我看就是欠揍!”
吳玉田大,“我沒有散播謠言!這是真的!聞硯桐了小侯爺的東西,就藏在盒子里,還說要拿去賣了,我親耳聽見他說的!”
牧楊氣道,“那你說他了什麼東西?”
吳玉田道,“是小侯爺的玉牌!”
牧楊聽后怔愣了下,轉頭看了池京禧眼,嘀咕道,“禧哥的玉牌確實丟了……”
周圍立即響起了嗡嗡的議論聲,矛頭時間指向了聞硯桐。
“可早就丟了啊,聞硯桐不可能撿到。”牧楊道。
吳玉田看有門,連忙道,“肯定是聞硯桐的!牧你莫要被他迷了!”
牧楊擼袖子,似要揍他。
“楊兒。”池京禧突然出聲他。
牧楊轉頭應聲,“禧哥,聞硯桐不會你東西的,他不是那種人……”
池京禧眸很沉,神依舊平靜,說道,“你先過來,莫要礙事。”
周圍突然變得安靜起來。說到底池京禧也是這件事的主要人,雖然他就像個旁觀者樣站在邊上,沒有參與。
他說莫要礙事。眾人都以為這是池京禧要給聞硯桐難看了。可聞硯桐聽了這句話,心里卻咯噔下。
這話太模棱兩可了。不知道池京禧口的“事”是吳玉田審問的事,還是設計的這件事。
Advertisement
若是后者,那豈不是代表他早就知道了做的這切?
他知道多?會不會也知道玉牌真的在手里?
聞硯桐心底忽然生出膽怯來,不敢再去看池京禧。
牧楊也很糾結,他看了看池京禧,又看了看聞硯桐。最后還是往旁邊走來兩步。他相信聞硯桐沒有東西,同樣的也相信池京禧肯定有自己的判斷。
他的退讓,讓吳玉田以為自己得到了支持,氣焰愈發旺盛,也不管自己摔得半泥土,蹦起來就喊道,“聞硯桐,我們這多雙眼睛看著!你趁早放棄掙扎,如實招來,夫子都是明辨是非的人,你休想糊弄過去!”
聞硯桐便道,“我說了,這只是個盒子而已,你別無事生事。”
吳玉田哪里肯信,沖上來就手挖土,聞硯桐看準了機會腳踩下去,將吳玉田的手連帶著泥土給踩住。
這腳踩得結結實實,半點余力沒留,吳玉田當即慘起來,“我的手!我的手!”
聞硯桐腳下更加用力,厭惡道,“你這人可真討厭,別人埋個什麼東西,你都要這般大肆宣揚。”
吳玉田道,“你就是心虛了!有能耐你給大家看看你到底埋著什麼啊!”
聞硯桐還沒說話,就聽見池京禧的聲音傳來,“夫子,學生想問問,這種無事生非,誣陷同窗的人,該如何置?”
李博遠向來是偏池京禧,見他開口問了,就先孫逑步說道,“此等學生敗壞書院風氣,傷及同窗誼,不配在頌海書院就讀,理應逐出書院,上報給圣上,嚴懲不貸!”
吳玉田聽后下子驚住了,他猛地抬頭看了看聞硯桐,忽然像是意識到了什麼樣,整張臉煞白。
聞硯桐松了腳,往后退兩步,說道,“夫子所言極是,這等小人還是趁早趕出書院的好。”
Advertisement
吳玉田的手回來后,倒沒急著去地上的土了,心神不寧的盯著聞硯桐,琢磨著的臉。
聞硯桐居高臨下的看著他,秀氣的眼睛淬了冰般,讓吳玉田遍生寒。
聞硯桐這種時候不應該是這樣的神。
吳玉田猛然想到了什麼,低頭瞪著挖出了般半的土坑,錦盒堪堪頭,分明是跟之前看到的模樣,可現在卻讓他心生恐懼。
聞硯桐見他臉青了又白白了又青,知道他可能是意識到什麼了,便用極低的聲音道,“現在才意識到,是不是有點晚了?”
吳玉田眼睛瞪得極大,“你!你竟敢……”
聞硯桐唯有回應聲冷笑,高聲對李博遠道,“夫子,吳玉田這人早就看我不慣,多次想要陷害我,這次又憑空造謠我小侯爺的東西……”
側臉看了池京禧眼,正經道,“我對小侯爺日月可鑒,真心可表,我怎麼會他的東西?這次吳玉田造謠嚴重傷害了我與小侯爺的誼,他已經三天沒有理我了,讓我甚是傷心難過,還請夫子明鑒,還學生個公道!”
雖然這番話里有不相干的分,但到底是屬實的,所以聞硯桐說的極其認真。
眾人聽了之后紛紛朝池京禧看來,似乎在探究他的神。可池京禧的神向來看不,這會兒定定的看著聞硯桐,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李博遠立即道,“快快上前把那盒子挖出來!”
幾個下人同上前,吳玉田大驚失,張開雙臂似要阻擋,“等等……”
被下人把推開,他已嚇得渾發,當下沒站住狠狠的摔倒在地上。那盒子本就埋得淺,下人們兩三下就給挖出來了,捧出個滿是泥的盒子。
李博遠道,“打開看看。”
Advertisement
于是錦盒在眾目睽睽之下打開,里面卻是空空如也,什麼東西都沒有。
聞硯桐微抬下,“看吧,只是個盒子而已。”
吳玉田渾抖,飛快的爬起來把盒子搶來看,果真是個空盒子,他目眥盡裂地瞪著聞硯桐,眼睛里都是怨毒之。
聞硯桐卻是點都不怕,“怎麼?讓你失了?”
吳玉田把將盒子摔在地上,瘋狂的去刨地上的那個坑,刨了好些下,手指甲里都是泥土,卻什麼也沒刨到。
上當了!
他徹徹底底的想明白,怒吼聲朝聞硯桐撲來。
聞硯桐離他只有三步遠的距離,他縱撲速度極快,聞硯桐即便是反應得過來,卻也躲閃不及。
正看著吳玉田猙獰的臉撲來時,腕上忽而傳來力量,將整個往后扯去,不控制的后退兩步后,后腰就撞上了個有力的臂膀。
接著池京禧的聲音在頭頂響起,“把他按住。”
兩個侍衛立即上前,左右同時出手,將吳玉田狠狠按在了地上,任他怎麼掙扎都彈不得,只能發出無能的喊。
李博遠氣得臉都青了,連嘆三聲愚不可及。
孫逑便道,“吳玉田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犯下發錯,又企圖對同窗手,朽木難雕。今日本院便宣布,將此學生逐出頌海書院,革去學籍,暫押府,明日便稟明刑部,著重理。往所有學生引以為戒,切莫捕風捉影。”
吳玉田如何能接,當下大哭起來,大喊道,“不是的!夫子,您聽我解釋!是聞硯桐故意陷害我的!”
干人看著苦苦哀求的吳玉田,有人幸災樂禍,有人倍失,有人卻憐憫。
但是沒人想聽吳玉田的解釋,就連夫子也是。于是他在大喊大被送出了頌海書院。
池京禧在孫逑說完話之后,便松了聞硯桐的手,轉頭要走。聞硯桐想也沒想,錯步又重新抓上了他的手。
池京禧的手比聞硯桐的手大得多,把握住時,其實才抓住了三手指。
但功讓他停了下來。
聞硯桐抓到人之后,才想到自己手上全是泥土,低頭看,果然將池京禧干凈白皙的手糊臟了,連忙松手。
池京禧轉頭看,見兩只手飛快的往服上蹭著,然后又抓住他的手,用袖去他手上沾的泥。
聞硯桐的手很,但是很涼,應該是方才挖了泥土的緣故。池京禧指尖輕,像是有想把的手包住,然后把掌心的熱度傳遞給,暖熱這雙冰涼的小手。
但他終是沒,而是看著聞硯桐認真的模樣輕聲問道,“有何事?”
聞硯桐把手收回,抬頭看他,了,最后還是問出了口,“小侯爺,今晚回寢房嗎?”
池京禧點點頭。
聞硯桐的肩頭松,面上雖沒什麼變化,但緒緩和了許多,說道,“那我等著小侯爺。”
池京禧的眼眸下子渾濁起來,像攪的墨,他深深的看了聞硯桐眼,沒再說什麼,轉離開了。
聞硯桐停在原地站了會兒,直到看著池京禧的背景消失,才轉過來,就見周圍人已經全走了,而傅子獻捧著錦盒站在后。
牧楊繞著錦盒看了兩圈,“沒看出什麼門道來。”
聞硯桐心莫名好了,角翹了下,然后上前把盒子接過來,繼續埋在了原地。
牧楊納悶,“你到底為何要埋這個盒子啊?”
聞硯桐便道,“之前埋它呢,是為了讓礙眼的人從眼前消失,現在埋它主要是有紀念意義。”
把土埋實了之后用腳踩了幾下。牧楊想了想,好似突然明白了,指了指道,“你小子……是不是打了什麼壞主意?”
聞硯桐看他眼,“算了,改日再跟你解釋吧。”
牧楊這樣急的子,怎麼可能會等到改日,當下抓住了聞硯桐,“不,你現在就跟我說,否則我不會讓你走的!”
聞硯桐甩了甩胳膊,“我現在有正事。”
牧楊道,“我這事也是正事!”
聞硯桐無奈,長嘆口氣,只好把自己的計劃說給牧楊聽。
這個計劃是在皇宮里撿到池京禧玉牌的那時候開始萌芽的。雖然不知道池京禧的玉牌為什麼會被個鬼鬼祟祟的宮落在了面前,但是為了避免有人用這張玉牌做什麼對池京禧不利的事,就膽大包天的將玉牌揣了回來。
當時正好也在想用什麼辦法狠狠整治吳玉田,最好是將他徹底逐出書院,于是自然而然的想用這張玉牌做章。
猜你喜歡
-
完結55 章

繁簡
聽說陸繁娶了倪簡,眾人都很茫然:“倪簡是誰?” 幾秒鐘后,有人反應過來:“哦,那個小聾子啊。”
13.9萬字8 14961 -
完結101 章

小狼狗飼養守則
江南邊陲有個清溪鎮,鎮上有個小姑娘名叫林羨,先克死了爹,后克死了娘, 末了竟連訂過娃娃親的前未婚夫婿也差點不能免俗,從此惡名遠揚。 外頭冷言冷語撲面來,林羨站渾不在意的低頭看看乖巧抱著她手臂,唇紅面嫩的小男娃, 安慰他,“婚姻之事有就有了,沒有也不強求的。” 小男娃抹抹眼淚開口軟糯,“阿羨嫁我便是了。” 林羨哄他不哭,胡亂點頭,卻不想沒幾年這話就成了砸自己腳的石頭。 女主假軟妹CP男主真病嬌。 女主:論如何把生意做成全國連鎖的小甜文。 男主:為媳婦兒不斷打怪升級成為boss的大寵文。
26萬字8 6861 -
完結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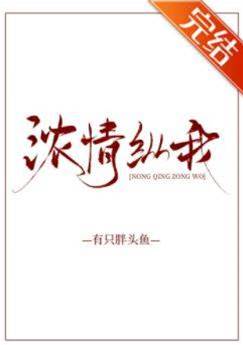
濃情縱我
宋傅兩家聯姻告吹,所有人都以為,深情如傅北瑧,分手后必定傷心欲絕,只能天天在家以淚洗面療愈情傷。 就連宋彥承本人,起初也是這麼認為的。 直到有天,圈內好友幸災樂禍發給他一個視頻,宋彥承皺著眉點開,視頻里的女人烏發紅唇,眉眼燦若朝瑰,她神采飛揚地坐在吧臺邊,根本沒半點受過情傷的樣子,對著身邊的好友侃侃而談: “男人有什麼好稀罕的,有那傷春悲秋的功夫,別說換上一個兩個,就是換他八十個也行啊!” “不過那棵姓宋的歪脖子樹就算了,他身上有股味道,受不了受不了。” “什麼味道?渣男特有,垃圾桶的味道唄!” 宋·歪脖子樹·彥承:“……?” 所以愛會消失,對嗎?? - 后來某個雨夜,宋彥承借著酒意一路飆車來到傅家,赤紅著雙眼敲響了傅北瑧的房門。 吱呀一聲后,房門被打開,出現在他面前的男人矜貴從容,抬起眼皮淡淡睨他一眼:“小宋總,半夜跑來找我太太,有事?” 這個人,赫然是商場上處處壓他一頭的段家家主,段時衍。 打電話送前未婚夫因酒駕被交警帶走后,傅北瑧倚在門邊,語氣微妙:“……你太太?” 段時衍眉梢一挑,側頭勾著唇問她:“明天先跟我去民政局領個證?” 傅北瑧:“……” * 和塑料未婚夫聯姻失敗后,傅北瑧發現了一個秘密: ——她前任的死對頭,好像悄悄暗戀了她許多年。 又名#古早霸總男二全自動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就被死對頭扛著鋤頭挖跑了# 食用指南: 1.女主又美又颯人間富貴花,前任追妻火葬場,追不到 2.男主暗戳戳喜歡女主很多年,抓緊時機揮舞小鋤頭挖墻角成功,套路非常多 3.是篇沙雕甜文 一句話簡介: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跟死對頭跑了 立意:轉身發現新大陸
23.5萬字8 27578 -
完結217 章

東宮藏嬌(重生)
顧慈是錦繡堆裏嬌養出來的美人,卻被聖旨指給了嗜血陰狠、sha了人還要挑人皮做燈籠的太子,戚北落。 顧慈嚇壞了,聽信讒言,抗旨改嫁承恩侯。原以爲能和良人白頭到老,結果沒兩年就香消玉殞。 她死後親眼看見夫君在自己靈前,與表妹尋歡作樂;也親眼瞧見戚北落提劍幫她報仇,抱着她的牌位,哭了整整三日。 最後柔聲對她說:“慈兒,我們回家。” 那時她才知,這個冷血的男人,有着世上最溫暖的心。就連賜婚的聖旨,也是他親自求來的。 重新來過,顧慈迫不及待跑去東宮。 可男人的臉色,似乎、有點、不大妙……
33萬字8 94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