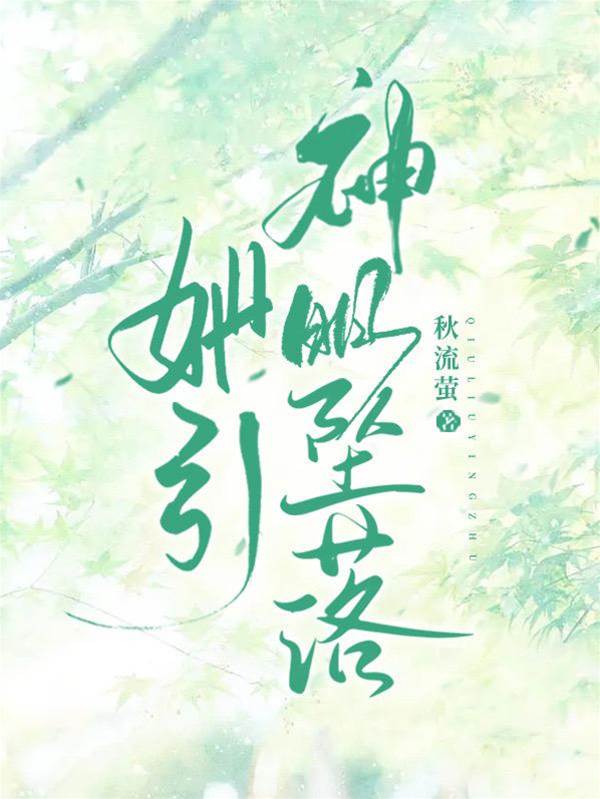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超寵甜妻,腹黑老公難伺候》 第一百三十二章
雪白的臉蛋離開他臉稍許,那雙大眼睛盯著他,不肯眨眼,淚瑩然,盯著他:“不爽爽?”
男人繃里頓漲的激頃刻凝滯。
他的雙手很快放開了。
他站起了。
顧爽爽腦袋挨著床的那一刻,看見他轉走出去。
那麼犟,仿佛是最后的自尊,不眨眼,一直,一直看著他高大的背影消失在臥室門口。
而后,的痛苦的蜷起來,把自己抱得多,哪里也都是冰冷骨的。
那個男人他心里有,但是,還沒有到的地步。
這是他的答案……對嗎?
沈墨城疾步出了臥室,沉重屹立的軀一下子靠在了臥室外的墻壁上。
男人神紛,蕭索為自己點了煙,作急促,他需要平靜。
他傾聽著里某一清晰有力的搏,從睜著那雙黑乎乎的認真大眼睛,問他不開始,什麼東西在搏,跳的突突的,跳的他心慌意,伴隨心深的恐慌。
指間冰涼,往薄送煙,他深深的吸食著能讓他鎮定的上癮東西。
他在心里問自己,對這個孩,除了,是否還有什麼別的地方也像吸煙般上了癮?
否則,的一句問話,何以讓他渾寂靜多年的都打了個?
一煙完,沈墨城仰頭,閉眼讓自己回到黑暗,但頭頂璀璨的水晶線還是能從他睫的隙里他的眼睛,照耀他,刺痛他。
就像里面躺著的那個渾好像會發的孩,亮亮的,照耀他,刺痛他那拒絕再的神經。
是.,寫著好的.,可這個男人,他累了。
在里他像一個風霜殘燭的老人,他或許想,但零件壞損,他走每一步都艱難,都很痛,蝕骨的痛會讓他拒絕再彈。
Advertisement
他可以對很用心,但沒有誰規定必須對用,能給的一定都給,沒有的,暫時不要強求。
讓他努力一會兒,讓他掙扎一會兒,讓他……息一會兒。
……
顧爽爽第二天起,沒有再見到他。
王姐說,先生昨晚臨時出差,歐洲好幾個國家,最后還要去趟加拿大,時間較久。
顧爽爽扛著頭痛在被子里鉆,能夠覺到側他余留的味道。
迷蒙中知道他昨晚抱著睡了一會兒,很短的時間,他起時似乎有覺。
為數不多的幾次醉酒,每次醒來后會斷片。
但這次沒有。
也因此記得十分清楚,最后鼓起心中所有勇氣,任問他不的時候,他沉默的回答。
剛開始,心絕。
每天正常上下學,可這個孩臉上慣有的天真笑容了,好像沒有靈魂,在這個沒有他影的家里穿梭。
后來,陷焦慮,如同每個全心陷進的二十歲孩,諸多的不,失他不,卻又不甘心,甚至開始為他為自己找理由。
你們認識到現在短短幾個月,你的魅力沒有那麼大。
他是個三十幾歲的男人,他不會像你一樣沖,他的很理智。
他有前妻,要割舍需要時間,你要給他時間。
或許你還不夠努力,沒有徹底打他。
你從一個連生活費學費犯愁的麻雀變被他捧護的凰,你錦玉食,你有他的寵,周圍所有人都看得見的寵,你真貪心,你還想一把抓住他的心,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也需要一步一步烙印。
總是這樣安自己,安他們明顯有了隙的關系,告訴自己,還沒到放棄的那一步。
Advertisement
的苦,在他出差二十多天沒有一個電話的行為里,顧爽爽嘗得淋漓盡致。
他真的,沒有一個電話。
顧爽爽日漸消瘦,從胡思想到無可奈何,到最終,按部就班過好自己的生活。
有自尊有驕傲,何必給他一副沒了他就活的不形狀的樣子,那樣的人,也不會有男人。
開始調理自己的飲食,充實自己的學習生活,即便他回來最壞的結果他說要和前妻復合要與分開,呈現在他眼前的,是過得很好的自己,起碼表象,不輸!
……
四月底,他仍舊杳無音信。
顧爽爽參加了學校組織的一個課程競賽,系里領導下來的指標,幾個尖子生和外校藝系的混合,去外省培訓,并有時裝展。
為期一周,機會難得,學習的同時剛好散散心。
四月的最后一天,坐八個小時的火車抵達鄰省Z市,國繁華商業的大都市。
顧爽爽沒有時間瀏覽這個城市的風景。
抵達Z大,前兩天是張的培訓,后兩天是課程競賽,最后一天是矚目的時裝展。
同行來的沒有悉的同學,過得張不安又孤獨。
夜深人靜躺在簡陋的賓館單人床上,總會想念那個溫熱有力的懷抱想念到捂著被子落淚。
習慣真的是可怕的東西,對不夠堅強的人來說更是可怕的東西,只不過枕著他的膛睡了一個月,就依上了。
在家里時還有他睡過的枕頭可以抱著,在這陌生的地方,心空空,什麼也沒有。
第三天課程競賽十點開始。
顧爽爽起的早,被賓館里的蚊子咬得,心不安寧。
五月的Z市清晨,沉浸在一片濃濃的霧靄中,走過賓館出來的那條小巷,要到外頭才有早點攤鋪。
Advertisement
一家賣豆漿的攤點前,顧爽爽掏出小錢包里八錢,要一碗新鮮放糖的豆花。
老板收了錢遞過來包裝好的豆花,顧爽爽低頭整理錢包,一手要接過豆花,卻接不到。
抬頭,卻看見了接過豆花的張青書,笑盈盈地沖道:“太太。”
顧爽爽怔了好一會兒,第一反應是去看高高的張青旁左右,視線延到路邊停泊的車。
好一會兒,慢慢垂下眼眸,搖了搖白白的小手,“張青書,好巧。”
張青目睹眼前小孩臉部表的變化,淺淺勾,賣著關子沒有作聲,卻子一側,做了個請的姿勢。
顧爽爽的心突突一跳,好像明白了什麼。
想的是不要跟過去,可雙腳卻不聽話,反應過來時,已經跟著張青走了好遠。
猜你喜歡
-
完結1091 章

失憶后我成了法醫大佬
十三年前全家慘遭滅門,蘇槿患上怪病,懼光、恐男癥,皮膚慘白近乎透明,她成了「吸血鬼」,選擇在深夜工作,與屍體為伴;他背景神秘,是現實版神探夏洛克,刑偵界之星,外形豐神俊朗,愛慕者無數,卻不近女色。第一次見面,他碰了她,女人當場窒息暈厥,揚言要把他送上解剖臺。第二次碰面,她手拿解剖刀對著他,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具屍體。一個只對屍體感興趣,一個只對查案情有獨鍾,直到未來的某天——單宸勛:你喜歡屍體,我可以每天躺在解剖臺任你處置。蘇槿:我對「活的」沒興趣……
196.7萬字8.18 22956 -
完結1233 章
七零年有點甜
何甜甜一直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的人。人到中年,卻發現一直生活充滿謊言的騙局里。重回七零年,何甜甜在小銀蛇的幫助下,開始新的人生。換一個角度,原來真相是這樣!這輩子,再也不做睜眼瞎了。這輩子,再也不要錯過辜負真心相待的青梅竹馬了,好好待他,信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215.3萬字8 54157 -
完結877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
生日那天,深愛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卻是一場復仇。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了記憶,再也不是從前了深愛霍雲霆,死活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這個婚離定了!” 夏初薇:“離婚?好,明天就去,誰不離誰是小狗。”第二天,夏初薇敲開霍雲霆的門。“霍先生,該去離婚了。” 霍先生:“汪!”所有人都知道她愛他至深,但唯有他,他愛她多次病入膏肓。
157.9萬字8 6044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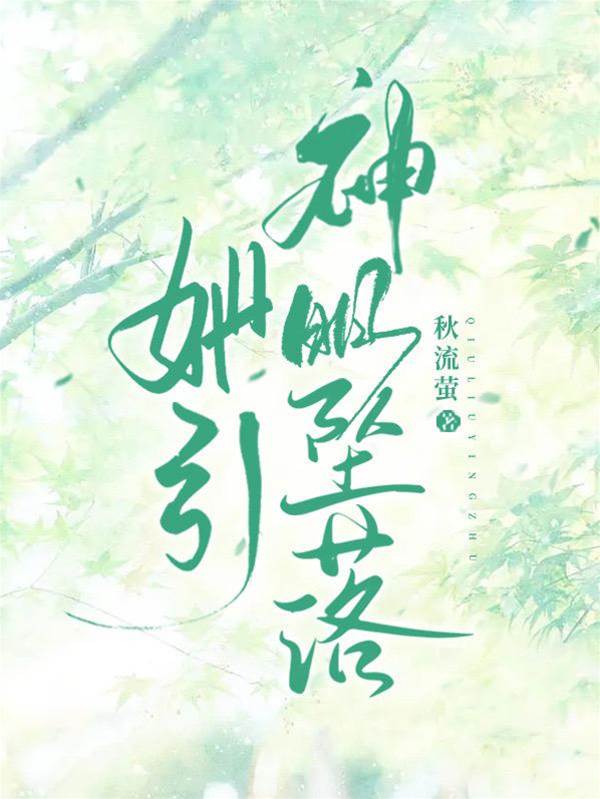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80 章

幸福不脫靶
他連吵架時擲出的話都如發口令般短促而有力:“不許大喊大叫!給你十秒時間調整自己,現在倒計時,十,九……” 她氣憤:“有沒有點兒時間觀念?需要調整十秒鐘那麼久?” 他是個很霸道的男人,對她裙子長度引來的較高回頭率頗有微詞:“你可真給我長臉!”見她呲牙笑得沒心沒肺,他板起來臉訓她:“下次再穿這麼短看我不關你禁閉。” 她撇嘴:“我是滿足你的虛榮心,搞得像是有損安定團結一樣。” 我們的小心願,幸福永不脫靶。
24.6萬字8 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