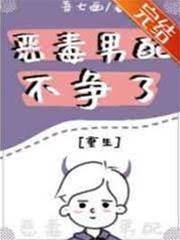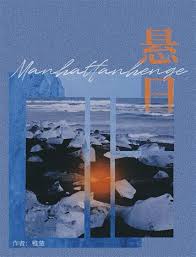《豪門男妻是副業》 27
片刻后,蘇喬吃了五六只基圍蝦,覺有點飽了。啤酒帶來的鼓脹氣還停留在胃里,他了肚子,打了個小小的嗝。
“我不吃了。”蘇喬搖頭,眼神并不集中,看上去像個致的木偶人。
駱云深:“去睡午覺?”
這個提議遭到了蘇喬的拒絕。
他偏著頭,臉上又開始浮現出委屈的神,雖然什麼都沒說,但那意思明明白白的。
不去睡午覺,就要在這里坐著。
他還把椅子又挪了挪,幾乎跟駱云深靠在一起了。
駱云深:“……”
坐在對面的許舜沒有錯過好友面上一閃而逝的無奈神。他“嘖嘖”兩聲,心里暗想:這還是頭次到讓駱云深沒辦法的人。
不過念頭一轉,想起這兩人的關系,又覺得完全正常。
一頓飯吃到最后,桌上的菜基本被清空了。駱星杼跟許舜都像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似的——實際上也確實是這樣——盡力往腹中塞下更多的味,最后雙雙癱在椅子上天消食。
半點社會英的影子都沒有了。
休息了一會兒,做客的兩人站起來,主把碗盤往廚房里收。洗碗有機代勞,他們只需要做勤快的搬運工。
駱云深跟蘇喬兩人還坐在餐桌旁,蘇喬已經歪到駱云深胳膊上去了,像一只吸貓薄荷吸到傻掉的小貓,滿臉通紅地靠著,呆呆愣愣,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收拾完餐桌,準備轉移陣地,去客廳里坐著聊天。
蘇喬跟著駱云深站起來,剛走了兩步,停在原地不了。
駱云深察覺不對,也止住腳步。
“怎麼?”他問。
隨即,駱云深就看到蘇喬臉上出驚慌失措的表。
蘇喬左右看看,在原地轉了個圈。他手去自己背后,一下、兩下……空無一。
Advertisement
“……”
蘇喬眼睛睜大,好像到了什麼巨大的打擊,瀕臨崩潰。
他的神太難過了,眼眶通紅,似乎在下一秒就要落下淚來,顯得脆弱而驚惶,仿佛有什麼彌天大錯沒法補救似的。
駱云深心臟微微一,結了:“……蘇喬?”
下一秒,他聽到蘇喬帶著哭腔的聲音,可憐地說:“我找不到尾了,它不見了嗚嗚……”
“什麼……?”駱云深啞然。
“我的尾,那麼大一條尾。”蘇喬邊掉眼淚邊說。他特別堅強地吸了吸鼻子,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不哽咽。“黃的、帶尖刺的——”
顯然,醉酒使人失去理智。
蘇啾啾不知道在心里給自己加了什麼設定,固執地認為自己應該有一條尾。拖在地上,像恐龍一樣的那種。
駱云深沉默片刻,冷靜道:“你沒有尾。”
蘇喬整個人一窒,隨即落淚更兇了。
“駱先生不講道理。”他氣憤地說。“我明明有那麼——大一條尾!”
他特意用手比了一下,示意自己的尾確實很大,非常大。如果有人說自己沒有尾,那一定是對方的錯!
“不講道理”的駱云深:“……”
兩人就此陷僵持狀態。
旁觀的許舜和駱星杼二人一言不發,換一個眼神:這種時候,貿然開口打擾別人談,是要被雷劈的。
蘇喬在原地站了一會兒,忽然下定決心,自言自語道:“我要去找尾。”
聲音還帶著哭腔,又又,不能更可憐了。
駱星杼看著都著急,恨不得陪他一起去找尾。甭管有沒有吧,先把人哄住了再說。
駱云深顯然意識到現在說什麼都白搭,再多的話都不如一條尾管用。他看著蘇喬,低聲商量:“尾在房間里,帶你進去看看?”
Advertisement
蘇喬立即驚喜地點頭,眼看著他,上來拉著駱云深襯衫一角,顯得很聽話。
“你們先看會兒電視。”駱云深道。
他帶著蘇喬進了房間,一手在對方的肩膀上摁著,讓蘇喬在床沿坐下,隨后把房間門關上。
蘇喬視線跟著他,見男人打開柜,從里面拿出黃小恐龍睡,頓時興高采烈。
尾找到了。
他就記得自己是有尾的嘛,原來駱先生把他的尾藏起來了。蘇喬頭昏腦漲地想。
他上發,踢掉拖鞋,在駱云深的幫助下艱難地穿上了睡。然后轉了兩圈,到確實有東西綴在后面,隨著自己的作在地板上掃來掃去,便放下心來,長出一口氣。
駱云深給他戴上尖牙帽子,低聲說:“現在開心了?”
蘇喬忙不迭點頭。腦袋藏在帽子里,看著面前的人,雖然還不清醒,卻從心里涌上一暖暖的緒,促使他地說:“駱先生,你對我太好了。”
聽他說爸爸公司里的事,幫他出主意。允許自己在婚前搬進公寓里,就因為失眠這個小問題。還給自己剝蝦,還幫自己找尾……
他思緒混,忍不住抬頭親吻駱云深,卻因為沒有力氣踮腳,吻在了結上。
蘇喬并未注意到男人的表忽然變了,他只在對方口磨蹭兩下,認真地說:“謝謝駱先生。”
駱云深靜默良久,才應聲。他拉開與蘇喬之間的距離,說:“躺著休息一下,睡個午覺。”
這回蘇喬沒有表示反對。他拎著尾上床,躺下之后覺得不舒服,就側過,抱床頭的兔子玩偶。
看他這樣睡得不舒服,駱云深道:“換套睡。”
“不。”蘇喬拒絕。“那樣我就沒有尾了。”
Advertisement
你再把我的尾藏起來怎麼辦?他在心里嘀咕。
駱云深:“……”
蘇喬在床上翻來覆去,尖牙帽子蹭掉了,出的黑發。他看看窗外,還亮著,覺得自己不該在這個時候睡覺,可是又很困——
思緒懵懂的大腦不足以支撐長時間思考,蘇喬只想了三秒,就要闔上眼睛。但他總覺得缺了點什麼,忽然掙扎著了,拉住駱云深的手臂。
不止如此,他還困意朦朧地說:“親我一下。”
眼睛都快要睜不開了,仍舊牢牢記得睡前的必要程序。如果這個時候沒有得到屬于他的那個吻,大概睡著了都要掛著一副了委屈的、氣鼓鼓的表。
駱云深在他上親了一下。
蘇喬角就出一個滿足的笑。
他意識已經模糊,無數片段思緒毫無道理的冒出來,臨睡前這段時間,大腦總會不控制地陷混。
一片黑暗的房間、父母痛苦的面容、掛著溫和笑容的蘇羽……
蘇喬咕噥道:“討厭。”
他額頭有點出汗,覺有人手給自己把服拽松了一些,下意識翻,護好自己的尾。
蘇喬眼前出現好多個駱云深的影子。或許是酒使人變得更加坦誠,緒更加激烈,一瞬間,他想起了去公司那天聽到的話。
“……蘇家大兒子年齡上跟駱總更配……”
“……不過駱總他圖什麼……”
駱先生什麼都好,就是有一點。蘇喬迷迷糊糊地想。他不喜歡我。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因為這一點耿耿于懷,明明只是聯姻,就算別人說他們不配,對聯姻這件事也沒有任何影響。
可是……
蘇喬難過地抱著尾,沉默兩秒,酒和困頓之下的缺乏理智使他有了莫名的勇氣。他聽見自己小聲問:“駱先生,你有沒有一點喜歡我?”
駱云深正在等他睡著,然后就可以調高空調溫度,回到客廳去。這時聽見蘇喬的問題,整個人怔住了。
他看著蘇喬。對方臉通紅,眼神渙散,顯然并沒有清晰的意識。不過,倒是很執著,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執拗和,直直凝視自己。
長久的寂靜讓蘇喬有點焦急,他像祈求的小貓一樣,在駱云深手掌下拱了拱,以示討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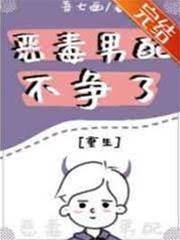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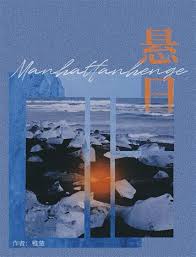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