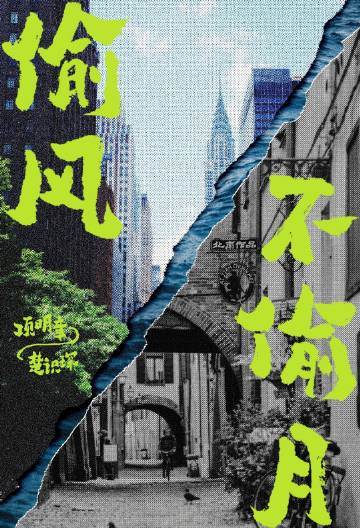《少爺名叫曹娘子》 第36章 分道
這和期的完全不一樣,顧昀一愣,口問道:“為什麼?”長庚答得有理有據:“西域有義父的玄鐵營坐鎮,我去了也只是添,還要煩你費心思地給我添一些子虛烏有的軍功,沒什麼意思。”
顧昀雖然大上就是這麼想的,但長庚這麼當面點出來,他還是有被潑了冷水的覺,勉強維持住臉沒變,顧昀說道:“那……也好吧,回京提前上朝聽政也行,我老師有些門生,你提前去認識一下也……”長庚:“那不是一樣嗎?”說話間,他抬頭看了一眼小長廊盡頭,江南豔天傾斜而下,滿園春花灼灼烈烈。
可是聽姚府的下人說起,雖然看著燦爛,但其實花期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開不了多久就要敗了,這還尚且是開在園子裡的,倘若開在那人跡罕至的荒郊野嶺之,悄悄地綻放,再悄悄地凋零,生死如天地一瞬,邊不過幾只野禽癡,又有誰知道呢?花是這樣,人心裡諸多無謂的憎大抵也是這樣。
長庚:“義父,了然大師邊有很多奇人,我想和他們一起雲遊四方,必不會耽誤讀書和練功……”這不是扯呢嗎?他話沒說完,顧昀的臉已經沉了下來,截口道:“不行。”
長庚側過,默默地看著他。
年逆的眼神裡含著某種說不清的東西,顧昀以前從未留意過,此時驟然遭遇,竟有一點心驚膽戰。
他隨即意識到自己語氣有點生,微微放緩了神,說道:“你出去玩沒問題,等回了京,王伯從侯府調幾個侍衛陪著你四下走走,可有一點,不準去沒有朝廷驛站的地方,每到一個驛站都得給我送封信報平安。”
長庚淡淡地說道:“一路錦玉食,到現世嗎?那我還不如沒事去護國寺跟夫人小姐們燒燒香,還省得人吃馬累費銀子。”
Advertisement
顧昀:“……”這小子居然會頂了!還頂得一派優雅從容暗含譏諷!顧昀方才被江南春浸染的好心忽然間然無存,心想:“怎麼還說不通了,我是把他寵得要上房了嗎?”他語氣開始有點不耐煩起來:“江湖路遠,人心險惡,有什麼好玩的?那和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除了逃命就會討飯,你跟著他萬一路上出點什麼事,我怎麼和先帝代?”“啊,”長庚漠然想,“果然是因為要和先帝代,先帝九泉之下要是聽說我是秀娘不知從哪弄來的小雜種,專門混淆皇家統用的,搞不好正氣得打算還來掐死我呢。”
他每多看顧昀一眼,就覺得心如刀絞一次,罪孽深重一次,恨不能馬上就畏罪潛逃。
可是那個人居然扣著他不讓走。
長庚對著一無所知的顧昀,有那麼一會,心裡平白無故生出一把纏綿的怨毒來,不過很快回過神來。
長庚收回落在顧昀上的視線,平靜地說道:“義父前幾天還跟我說過,只要是我自己想好要選的路都可以,這麼快就不算數了?”顧昀心頭火起:“我說讓你自己想好,你這就算想好了嗎?”長庚正:“我確實就是這麼想的。”
“不行,重新想!想好了再找我說。”
顧昀不想在外面發作他,便沒好氣地一甩袖子,轉走了。
長庚目送著他的背影,拂去上沾上的花瓣,聽見後傳來腳步聲,他不用回頭就聽得出來人是誰,說道:“了然大師見笑了。”
了然和尚剛開始沒敢出來,探頭探腦半天,見顧昀走了,才放心面,比比劃劃和稀泥道:“侯爺是好意。”
長庚低頭看著自己的雙手,手上已經磨出了細細的繭子,只是還沒有經過傷痕的洗禮。
Advertisement
他冷漠地說道:“我不想在他的好意下做一個凡事仰仗他的廢。”
“和尚覺得殿下有幾分偏激,”了然比劃道,“就算是聖人們年時,大多也是在父母長者的庇佑下長大的,以殿下的標準,豈不是天下皆廢嗎?大晚,須得戒驕戒躁。”
長庚沒有回話,顯然是沒聽進去。
了然和尚又道:“我見殿下神鬱鬱,是毒已骨。”
長庚悚然一驚,以為他知道了烏爾骨的事。
卻見了然和尚又道:“人心中都有毒,有的深些,有的淺些,殿下這個年紀,本不該發作得這麼徹底,您心思太重了。”
長庚苦笑道:“你知道什麼?”他總覺得自己周的一切——王爵,虛名,都是秀娘來的,總有一天會有人看出他與這些東西的不般配,讓他出馬腳來,讓他失去一切。
這樣惶惶不可終日慣了,長庚始終覺得自己在京城是個局外人。
顧昀站在四殿下的角度上為他籌謀前程,他心裡一點真實都沒有。
每天照鏡子都知道自己是條泥裡滾的“地龍”,別人卻偏偏要給他犄角鑲鱗,費盡心機地將他打扮真龍,殊不知裝飾再多,也是不倫不類,他始終是條上不得臺面的蚯蚓。
既然這樣,不如索離遠點,省得將來難堪。
唯有一個顧昀,帶給他的喜怒哀樂都那麼刻骨銘心,沒有一丁點摻假,他沒法自欺欺人地輕輕放下,只是時常覺得自己不配。
長庚沒有自怨自艾很久,很快回過神來,問道:“對了,大師,我一直想向您打聽,我小義父到底有什麼病癥?那次東海之行他很不對勁,卻不肯告訴我。”
和尚慌忙搖頭:“阿彌陀佛,和尚可不敢說。”
長庚皺了皺眉:“他自己逞強不算,你還幫他?”“侯爺豈是那無謂逞強的人?”了然笑道,“此事他若是自己不願提,不是怕別人知道他的弱點,大概因為此乃他上逆鱗與心頭的毒——誰敢安定侯的逆鱗?殿下繞了我的小命吧。”
Advertisement
長庚若有所思的皺起了眉。
顧昀好不容易從大漠黃沙裡開小差出來兩天,本想好好領略一下江南風,出去遛個馬、遊個湖、看幾個人什麼的,走之前玩夠本,結果被長庚兩句頂得沒心了,悶在屋裡不肯出去,反正他看長庚也來氣,看姚鎮也來氣,看了然更是氣不打一來。
姚家兩個熊孩子還不肯消停,你一聲我一聲地吹竹笛子,十裡八村都聽得見,好像一對聒噪的八哥。
顧昀一聽那沒調的聲音,就想起長庚把笛子從他手裡出去的樣子,更來氣了——以前不是有什麼東西都先給義父的麼?怎麼說變就變呢?可憐天下父母與子的緣分看起來脈相連,卻原來都不能長久。
何況不是親的,連脈相連都沒有。
傍晚的時候,一個玄鷹落在院子裡:“大帥,沈將軍來信。”
顧昀將一口氣憋回去,接過來一看,只見沈易那碎子寫信倒是頗為簡潔,就仨字——急,速歸。
沈易自從靈樞院中出去跟他出生死,什麼陣仗沒見過?沒事萬萬不會討嫌寫加急信催他。
玄鷹:“大帥,您看……”顧昀:“知道了,不必回,我們明天就啟程。”
長庚那邊本還沒說好,顧昀本想曬他兩天再說,可沈易催得急,沒辦法,只好在屋裡走了兩圈後,起找了過去。
長庚正在院裡練劍,顧昀旁觀了片刻,忽然回手出玄鷹的佩劍,玄鷹上甲未卸,重劍足有人年人掌那麼寬,被他拎撣子似的輕飄飄地拎在手裡:“小心了。”
話音未落,一劍已經橫掃而出,長庚紮實地接住,竟一步沒退。
“長進了,”顧昀心想,“手上也有些力氣了。”
他猛地一掀,借著手中劍之力翻而起,大開大闔一劍如滿月。
Advertisement
長庚不敢接,腳下連錯幾步,卻卸不下他這一劍之力,顧昀手中笨重的重劍如靈蛇吐信,眨眼間已經刺出三劍,長庚橫劍而擋,人已退至角落,側躥上梁柱,整個人在空中打了個旋,一腳踩上顧昀的重劍。
顧昀了聲好,驀地松開劍柄,長庚腳下驟然失去支撐,踉蹌了一下,顧昀探手一抓,重新抓住劍柄,輕輕往下一,正在了還沒站穩的年肩膀上,玄鐵劍讓他起了一脖子皮疙瘩。
顧昀笑起來,用重劍拍了拍長庚的肩膀,回手將重劍扔給後的玄鷹:“不錯,功夫沒懈怠過。”
長庚活了一下發麻的手腕:“比義父還差得遠。”
顧昀大言不慚道:“嗯,那是還差得遠。”
長庚:“……”正常況下不應該先自謙再語重心長地教導兩句嗎?他怎麼還順桿爬了!有這麼不謙虛的義父嗎?顧昀:“你要是到西北大營來,我可以親自教你。”
果然還是為了這個,長庚忍不住失笑。
說起來也是奇怪,有的時候,一個人真想得到什麼東西,汲汲求機關算盡也求不到,忽然覺得不想要了,那東西反而會糾纏著找上門來。
長庚婉拒道:“我在侯府的時候,曾問過師父,義父小時候練劍習武也是在侯府,為什麼能那麼厲害,師父告訴我,功夫紮實,主要看自己肯下多大工夫,功夫厲害,主要是戰場上生死一線的況多了,誰教都一樣。”
顧昀笑容消失了。
長庚:“義父,我三思過了,還是想出去見見天地。”
顧昀皺眉道:“京城和邊疆的天地不是天地嗎?你還要見什麼,大梁裝不下你了?你還想遊到西洋去嗎?”又要吵,玄鷹在後面一聲不敢吭——高大的天空殺手抱著自己的重劍,假裝自己是一座忘了收的煤堆。
長庚不吭聲了,只是深深地看著顧昀,有那麼一瞬間,很想把自己心裡抑的事嘔吐一樣地倒出來,後來忍回去了——他設想了一下顧昀可能有的反應,覺自己可能承不了。
顧昀:“你不用說了,我不想知道你那些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哪來的,明天就讓那和尚滾蛋,你老老實實回京城,既然不想去西北,那就待在家裡,哪也不許去!”長庚很想沖顧昀大吼一聲:“侯府不是我的家。”
可這話已經到了邊,又被他一口咬兩半,咽下去了,他本能地怕說出來傷顧昀的心——盡管不知道顧昀有沒有心可以傷。
“義父,”長庚靜靜地說,“這次累你從西北趕來,我心裡很難過,但你要是不講道理,我也只能任以對。
我能跑一次,就能跑兩次,你不可能永遠看著我,侯府的家將關不住我的。”
顧昀氣懵了,侯府一直是他心之歸,無論多不想返京,一想到可以回家,總歸還是有所期待的,他這時才知道,原來在長庚眼裡,那裡就像監獄一樣。
顧昀:“你盡管試試。”
兩人再一次不歡而散。
玄鷹連忙追上去,顧昀還沒走遠,本不避諱長庚聽見沒聽見,冷冷地吩咐道:“你明天不用跟著我了,跟著四殿下上京城,不能讓他離開京城一步!”玄鷹:“……是。”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算了,連門口飛的黑鷹一塊燒了禿,真是無妄之災。
第二天清早,顧昀頂著火氣就走了。
他沒再見長庚,臨走的時候,缺德的安定侯神不知鬼不覺地潛了姚大人家五歲小孩的院中,將人家放在秋千上的竹笛走了,那小孩醒來以後發現笛子憑空消失,傷心得嗷嗷哭了一整天。
顧昀比來時還迅疾地趕了回去,落地後跟沈易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給我準備藥。”
沈易神凝重:“你現在還能聽見嗎?”“能,”顧昀道,“快不能了,有話快說。”
沈易從懷中出幾張紙:“這是沙蠍子的口供,沒給別人看過,我親自審的,等大帥回來定奪。”
顧昀一邊走一邊一目十行地翻看,突然,他腳步停住了,驀地將手中的紙折了起來。
一瞬間,他的表有點可怕。
沙蠍子進犯古路只是順便,他的目標竟是樓蘭,他手上有一張樓蘭的藏寶圖,所謂的“寶”,竟是千頃的紫流金礦。
猜你喜歡
-
完結221 章

電競團寵Omega
全息电竞联赛是Alpha们的秀场,凋零战队Polaris为了凑齐职业重返赛场,居然招了个第二性别是Omega的巫师。小巫师粉雕玉琢,站在一群人高马大的Alpha选手里都看不见脑袋,时不时还要拽着队长林明翡的衣角。全联盟都觉得昔日魔王林明翡掉下神坛,要笑死他们不偿命。 后来,他们在竞技场里被夏瞳用禁制术捆成一串,小巫师用法杖怼着他们的脑袋一个个敲过去,奶凶奶凶的放狠话:“给我们队长道歉!不道歉的话就把你们全部送回老家!道歉的话......我就唱歌给你们听!” 众俘虏顿感上头:“靠,他好可爱!” - 作为全息电竞行业里唯一的一只Omega,夏瞳不仅是P队的吉祥物,还是所有战队想挖墙脚的对象,迷弟迷妹遍地跑。 拿下联盟赛冠军的第二天,一个西装革履的Alpha敲开了P队俱乐部的大门。 “夏瞳是我走失的定制伴侣,请贵俱乐部即刻归还,让他跟我回去生孩子。” 林明翡赤着精悍的上半身,叼着烟堵着门,强大的信息素如山呼海啸:“你有胆再说一遍?” #让全联盟的团宠给你回去生孩子,你是不是没被人打过! #再说他现在是老子的Omega! 看着沉稳实则切开黑的大帅比X看着傻但打架超狠的小漂亮。 →1V1,苏爽甜,弃文勿告,感谢尊重。 →社会制度游戏规则全是鬼扯,千万别考据。 →求不养肥,养着养着可能就死了...
48.6萬字8 14032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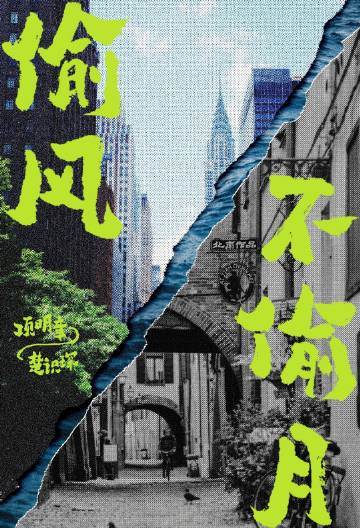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連載136 章

我是卷王穿越者的廢物對照組
時書一頭悶黑從現代身穿到落後古代,爲了活命,他在一個村莊每天干農活掃雞屎餵豬喂牛,兢兢業業,花三個月終於完美融入古代生活。 他覺得自己實在太牛逼了!卻在河岸旁打豬草時不慎衝撞樑王儀仗隊,直接被拉去砍頭。 時書:“?” 時書:“操!” 時書:“這該死的封建社會啊啊啊!” 就在他滿腔悲鳴張嘴亂罵時,樑王世子身旁一位衣著華貴俊逸出塵的男子出列,沉靜打量了他會兒,緩聲道:“學習新思想?” 時書:“……爭做新青年?” 謝無熾面無表情:“6。” 這個朝代,居然、不止、一個、穿越者。 - 同穿古代卻不同命,謝無熾救時書一命。時書感激的找他閒聊:“我已經掌握了這個村子的命脈,你要不要來跟我混?吃飽到死。” 謝無熾看了看眼前衣著襤褸的俊俏少年,淡淡道:“謝了。我在樑王座旁當謀士,生活也挺好。” “……” 感受到智力差距,時書忍了忍:“那你以後要幹嘛?” “古代社會,來都來了,”謝無熾聲調平靜,“當然要搞個皇帝噹噹。” 一心一意打豬草的時書:“…………” - 謝無熾果然心思縝密,心狠手辣。 時書驚慌失措跟在他身旁當小弟,眼睜睜看著他從手無寸鐵的新手村黑戶,積攢勢力,拓展版圖,逐漸成爲能逐鹿天下的雄主。 連時書也沾光躺贏,順風順水。 但突然有一天,時書發現這是個羣穿系統,只有最後達到“天下共主”頭銜,並殺光其他穿越者,才能回到原來的世界。 “……” 一個字:絕。 時書看看身無長物只會抱大腿的自己,再看看身旁手染滔天殺孽、智謀無雙的天子預備役謝無熾。 ——他還不知道這個規則。 時書深吸了一口氣。 當天深夜。 時書拿著一把短刀,衣著清涼,白皙肩頭微露,誠惶誠恐爬了謝無熾的牀。
60.9萬字8 4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