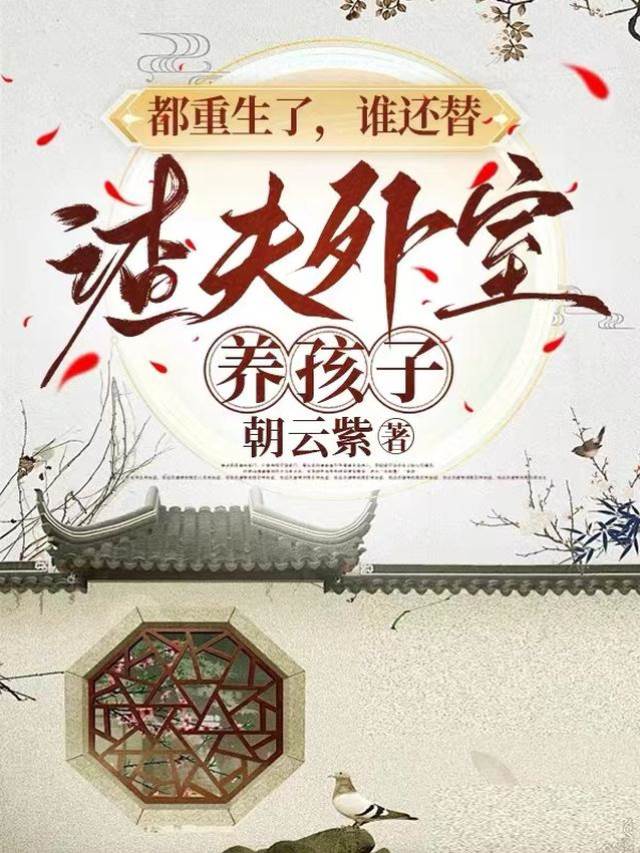《娘子且留步》 第119章 貴姓
“翠仙,今天怎麼這麼大的火氣,誰惹你了?”
雅間里,男人笑著問道。
先前那位轟人出去的子,便是翠仙閣的老板翠仙。
冷哼一聲:“沒人惹我,我就是煩這些沒事嚼舌子的,大男人扯老婆舌,誰不煩啊,你說是吧?”
男人哈哈大笑,用手里的折扇輕指:“你呀,這張還是這麼厲害,你也不怕把客人全都嚇跑了?”
翠仙一甩帕子,瞟他一眼,說道:“嫌棄我了?那你別來啊。”
男人又笑,看著翠仙的目里滿是寵溺:“這麼多了,你一點都沒有變。”
“不敢變,擔心變了,你就認不出我了。”翠仙說著,一屁坐到男人的上......
李食記里,雪懷還在剝蛋,直到那個站在后的人忽然開口,被嚇了一跳,手里的蛋掉到盆里,裂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誰讓你進后院的?”
雪懷像活見鬼似的瞪著晏七,四下看看,后院里只有和晏七。
“我問你在嗎?有個婆子,嗯,就是你家新招的婆子,說你在后院,就把我領進來了。”
晏七一臉無辜,他也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地進了后院。
雪懷再次四下看了看,低聲音問道:“我娘看見你了嗎?”
晏七搖頭:“我不知道。”
雪懷站起來,推著晏七往外走:“趁著我娘還沒有發現,你快走。”
“......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說完就走。”晏七被推著只能往門口走,快到門口時才想起來的目的。
“那也不能在這里說,我娘看到會剁了你。”
雪懷用手刀朝著晏七揮了揮。
晏七錯愕,這麼嚴重?
Advertisement
“那到哪里說?”
“老地方,你快走,夠夠夠!”
“夠?夠什麼?”晏七還要再問,人已經被推出了后院。
待到呂英兒過來拿剝好的蛋時,發現只有蛋,剝蛋的人已不知去向。
所謂老地方,就是街口單伯攤子的斜對過,以往晏七總是在這里“偶遇”雪懷。
雪懷估著晏七快到了,這才出門的,來的時候,晏七已經等在那里了。
“什麼事,你快說,我還要回去剝蛋。”
一路跑過來,雪懷鼻尖上滲出了細的汗珠,小姑娘臉蛋紅撲撲的,生機。
“坐下吃幾個茶葉蛋吧,我請。”晏七說道。
沒等雪懷坐下,單伯便把一大碗茶葉蛋放在小破桌子上。
“這麼多?”雪懷覺得和蛋真有緣,在自家鋪子里剝蛋,出來說幾句話還要繼續剝蛋。
單伯憨憨一笑:“這位公子要的,吃不完就帶走。”
好吧。
“我有點事,要有幾天不在新京。”晏七說道。
“就這?”雪懷覺得晏七真是沒事找事,他平時也經常好幾天不面,再說,家的新攤子就要開起來了,那麼忙,哪有空去管他。
“我還有幾句話,想和你說。”晏七凝神看著雪懷,像是生怕雪懷不讓他說。
“那就說吧。”雪懷一副你說不說的樣子。
晏七就是覺得這副樣子很有趣,也很耐看,就是總想多看幾眼。
“你之前說得沒錯,我家的確門第很高。我父母非常開明,我聽說有些人家男是分開排行的,可我家不是,我有四個哥哥兩個姐姐,但是活下來的只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我父母特別疼孩子,也特別開明,不像有的人家那樣事事都讓兒聽他們的。
Advertisement
我大哥娶的是他的青梅,我大姐嫁的是的竹馬,我大哥和我大姐從小在一起讀書,后來我大哥的伴讀做了我的大姐夫,我大姐的伴讀做了我的大嫂。
我二哥喜歡研究佛法,沒有親的念頭,我父親也便隨他去,還說只要他不剃度,其他怎麼都行。
我三哥十六歲就親了,沒人催他,是他自己要親的,我三嫂比他大了三歲,原本已經在和別人議親了,我三哥橫一,生生把我三嫂搶過來的,他們兩人特別好,親七八年了,兩人從未分開過。
我是家里最小的,我來新京之前,我娘便說不能因為打仗就耽誤了我的親事,我一個人在外面,若是遇到喜歡的姑娘,不用千里迢迢帶到他們面前,若能寫信說一聲當然好,若是不能,那就全由我自己做主,該親就親,該......總之,就是全由我自己做主。”
今天下過一陣雨,路邊有個淺淺的水沆,一駕騾車經過,車子軋在水沆里,雪懷拉了晏七一下,晏七連人帶凳子一起移到雪懷邊,沒讓泥水濺到上。
“你怎麼不說了?”雪懷問道。
晏七怔了怔:“我說完了。”
“就這?沒有別的了?”雪懷看著晏七,因為剛才那麼一拉一避,兩人離得很近,雪懷的睫又長又,微微上翹,一一宛若蝶翼。
“......沒了。”他準備了一路,還在擔心香菜會嫌他啰嗦,沒想到人家嫌他說得太。
“哈。”雪懷點點頭,起便走。
晏七連忙上前一步,攔在雪懷前面,急急問道:“你還想聽什麼,你問,我答。”
“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雪懷問道。
Advertisement
“嗯......能說的我全都說。”晏七又補充了一句。
雪懷哈了一聲,看著晏七的目里多了幾分玩味,看上去有那麼一點玩世不恭。
晏七沒有避開,迎著的目,像個學堂里的小小蒙,等候夫子的提問。
“你貴姓?”
晏七......
為什麼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此犀利?
晏七端起裝茶葉蛋的瓷碗,晃了晃,倒出幾滴湯。
晏七出食指,就著那湯在破桌子上寫了一個字。
雪懷看了,發出了今天的第三聲“哈”。
也不知是在嘲笑還是在冷笑。
晏七掏出一塊雪白的帕子在桌子上抹了抹,湯便全都蹭到了帕子上。
“你什麼名字?”
好吧,這個問題相較于上一個,要簡單多了。
晏七再次端起那只大碗,故技重施,在破桌子上寫了一個“晏”字。
雪懷噗哧笑了。
這一次終于沒有“哈”,不過也差不多。
“好笑嗎?”
“好笑啊,我在書上看過,說是晏子個頭很矮,還曾經奇怪為何你沒有傳,呵呵。”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奪嫡
他將她囚禁。背叛,滅族,辜負。她死于一場蓄謀已久的大火。燒到爆裂的肌膚,寸寸誅心的疼痛和撕心裂肺的呼喊,湮沒在寂寂深宮。重生歸來。她卻只記得秋季圍獵的初遇,和悲涼錐心的結果。人人避之不及的小霸王,她偏偏要去招惹。一箭鎖喉搶了最大的彩頭,虞翎…
45.9萬字8 106515 -
完結4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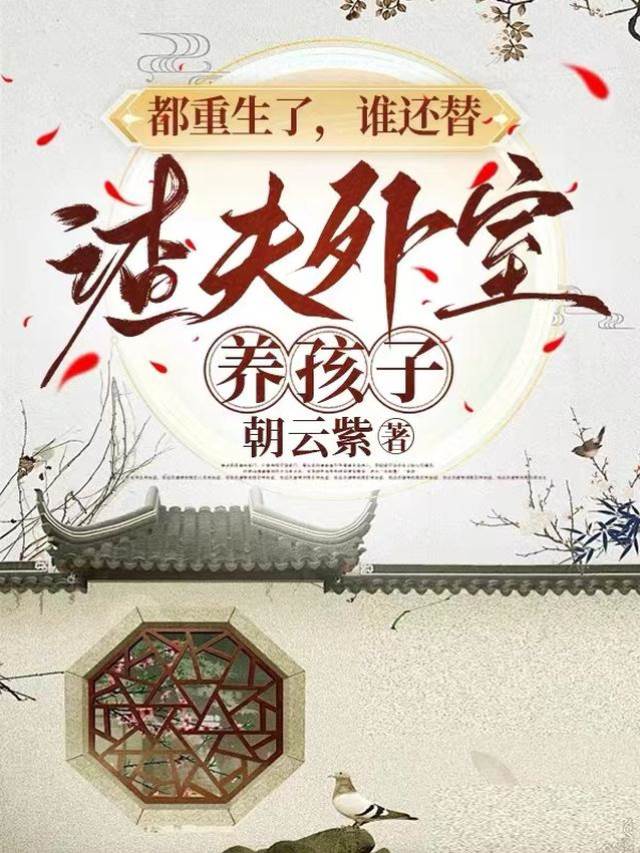
都重生了,誰還替渣夫外室養孩子
上輩子,雲初輔助夫君,養大庶子,助謝家直上青雲。最後害得整個雲家上下百口人被斬首,她被親手養大的孩子灌下毒酒!毒酒入腸,一睜眼回到了二十歲。謝家一排孩子站在眼前,個個親熱的喚她一聲母親。這些讓雲家滅門的元兇,她一個都不會放過!長子好讀書,那便斷了他的仕途路!次子愛習武,那便讓他永生不得入軍營!長女慕權貴,那便讓她嫁勳貴守寡!幼子如草包,那便讓他自生自滅!在報仇這條路上,雲初絕不手軟!卻——“娘親!”“你是我們的娘親!”兩個糯米團子將她圍住,往她懷裏拱。一個男人站在她麵前:“我養了他們四年,現在輪到你養了。”
85.6萬字8.18 28810 -
完結222 章

霽月清歡
這日大雨滂沱,原本要送進尚書府的喜轎,拐了兩條街,送入了永熹伯府。 毫不知情的寧雪瀅,在喜燭的映照下,看清了自己的新婚夫君。 男子玉樹風逸、軒然霞舉,可一雙眼深邃如淵,叫人猜不透性情。 夜半雨勢連綿,寧雪瀅被推入喜帳,亂了青絲。 翌日醒來,寧雪瀅扭頭看向坐在牀畔整理衣襟的夫君,“三郎晨安。” 衛湛長指微頓,轉過眸來,“何來三郎?” 嫁錯人家,寧雪瀅驚愕茫然,可房都圓了,也沒了退婚的餘地。 所幸世子衛湛是個認賬的,在吃穿用度上不曾虧待她。 望着找上門憤憤不平的季家三郎,寧雪瀅嘆了聲“有緣無分”。 衛湛鳳眸微斂,夜裏沒有放過小妻子。 三月陽春,寧雪瀅南下省親,被季家三郎堵在客船上。 避無可避。 季三郎滿心不甘,“他……對你好嗎?” 寧雪瀅低眉避讓,“甚好,也祝郎君與夫人琴瑟和鳴。” 季三郎變了臉色,“哪有什麼夫人,不過是衛湛安排的棋子,早就捲鋪蓋跑了!雪瀅妹妹,你被騙了!” 寧雪瀅陷入僵局。 原來,所謂的姻緣錯,竟是一場蓄謀。 衛湛要的本就是她。
32.7萬字8.25 149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