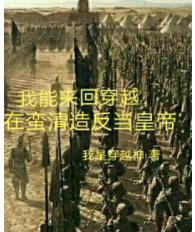《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091 你不該生來這世上
佛安堂這三個字,時至今日,司季夏還記得很是清楚。
他甚至記得那間屋子裡坐著一個與莫阿婆完全不一樣的老婦人,莫阿婆是慈祥和藹的,每一次見到他都會笑著他的腦袋,給他吃藏著的零兒或一兩顆餞,或是一些散碎的芝麻糖,雖然都是不值錢的小東西,可對他們這些窮人家來說,這已經是頂頂好吃的東西了,所以每一次見到莫阿婆,他都會很開心很開心。
可佛安堂裡那個老婦人一樣,看起來明明長得比阿孃大不了多,卻偏偏讓人太夫人太,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張鋪著綢緞的寬榻上,面上沒有一一毫的慈祥與笑意,冷淡就像屋子裡供著的佛像一樣,他剛見到時,還以爲也像佛像一樣沒有溫度不會說話也不會笑,可偏偏這樣一個怎麼看怎麼讓人覺得可怕的老人家在看到他時,那冷淡的一張臉上神變幻得很是厲害,甚至還把他喚到跟前,了他的腦袋,問了他的名字,還問了他幾歲了。
只是,他也注意到了,那老婦人在看到他的右肩是震驚的,還有……同與憐惜?
再然後,他便被帶出了那屋子,那老婦人只留了阿孃在裡邊,們說了很久很久的話,從晨日直到正午,他便在屋外從晨日站到正午,因爲沒人理會他,就算院子裡有人,都離得他遠遠的,就像他每一次和阿爹還有阿孃下山時一樣,幾乎所有人見著他都會避開,就像他是什麼瘟疫毒藥一般,他很傷心,但是他也習慣了。
他還記得,那一日的日頭很大很大,屋外無可讓他遮,他也不敢走到前邊不遠的走廊裡,就這麼一直在屋外的日頭下站著,站著站著,他覺得頭暈目眩渾乏力,站著站著,他聽到了屋裡阿孃在哭,站著站著,他就昏了過去,不省人事了。
Advertisement
當他再醒來時,他的眼前除了他哭紅了一雙眼的阿孃,還有一個他從未見過的漂亮年輕婦人。
後來他才知道,那個佛安堂裡的太夫人,是這間做侯府的大宅子裡最有威的人,就連這間宅子的主人都要聽的話,而那個出現在他牀頭的漂亮年輕婦人,是回府來探那個太夫人的,是什麼羿王妃,段晚晴。
那時他在想,是不是這個大宅子裡的人都不喜歡笑,那個太夫人是這樣,這個漂亮的年輕也一樣。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們不是不笑,只是不對著他笑而已。
再再後來,阿孃讓他管那個漂亮的年輕婦人娘,說纔是他的親孃,他不信,然後阿孃給他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他便相信了,再之後,阿孃要走,卻沒有將他帶走,而是讓他先跟他的親孃回家,待過些時日再來接他。
阿孃說的話,他信,雖然他不捨得離開阿孃,雖然他很想很想和阿孃一起回他們山上的小家,但是阿孃說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不方便帶他去,讓他乖乖聽話等著回來接他,要是他不聽話的話,阿孃就會生病,就會難過。
他不想阿孃生病,不想阿孃難過,所以他聽話,跟他的親孃“回家”了,回去等著他的阿孃來接他。
只是他等了很久很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曾經很多很多時候他在想,若是當年他沒有到過段氏侯府,沒有隨阿孃進了那佛安堂,沒有見過那太夫人,或是他哭著求阿孃把他帶走,是不是他就不必經歷那之後的種種苦痛。
他甚至想過,若是當年沒有隨阿孃離開山上的家就好了,就算他早早死在山上的家裡,也比他獨自一人在寂藥裡過了一年又一年要強。
Advertisement
可這世上從來就沒有假若。
這東陵段氏侯府有著他最苦痛的回憶,他當初離開了,就沒有想過要再回來。
可如今他卻不得不回來,只因爲一件事。
因爲他想知道他是誰,怪也好,野種也罷,他只是想要知道他是誰,不管這個答案是好還是壞。
即便阿暖不在乎他是誰,他也還是想要知道,連自己爲何生於這個人世都不知曉,他覺得他本就不能心安理得地陪在阿暖邊,倘他的世會給阿暖帶來災禍,他當如何自,如何面對阿暖?
段晚晴死了,羿王爺被押在京永無自由,他們皆不願告訴他他究竟是誰,那他想要知道的事,便只能從段氏侯府這兒來探知了。
段晚晴留下的墨玉佩,有他想要知道的答案,只是,他讀不懂,他需要有人幫他解答。
而這個人,除了十三年前他曾見過一次的佛安堂裡的那個太夫人之外,或許這天下間再無人能幫他解了,他曾想過或許這個太夫人不在這世上了,但現下看來,老人家似乎還健在。
佛安堂還是在原來的那個地方,由偏門到佛安堂的路司季夏只在七歲那年走過一次,可他還記得這條路怎麼走,這條路與他不想回首的過往一般,深深烙刻在了他心底,不是他想忘,便能忘得掉的。
這一路從偏門方向走往佛安堂,司季夏避開府中人的耳目,與冬暖故無聲無息地了佛安堂所在的院子。
此時的院子裡靜悄悄的,沒有任何人影,只有一盞風燈在佛安堂前的廊下輕輕搖晃著,至於人影,都堆在了院子的月門外,皆不安地看著院方向,卻是沒有一人敢擅自進月門。
Advertisement
可見人人都怕了那太夫人的話,就怕自己敢進這院子就會惹得太夫人撞死在佛安堂裡一般,只能焦急地等待著能勸得太夫人離開這佛安堂,離開這侯府的人到來。
也因爲如此,司季夏帶著冬暖故進到這院子裡來時,並未有人發現,他們便這麼堂而皇之地走到了門扉敞開的佛安堂門前。
只是司季夏的腳步很慢很慢,慢得似乎他的每一步都帶著極致的沉重,當他走到佛安堂敞開的門前時,他不再往裡去了,就在門外停下了腳步。
他停,冬暖故也停,他不說話,冬暖故也沉默著,因爲此時此刻,不是說話的時候,有些事,不是想幫他,便能幫得了的。
就像他的這個心結,打下這個結的時候沒有,需要解開的時候,也幫不了他,能做的,只能是站在他旁,給他面對一切事的勇氣而已。
“誰!誰在外面!?”就在司季夏在佛安堂外停下腳步時,屋突然傳來婦人冷厲的質問聲,隨之只見一個四十五六歲模樣的婦人突然出現在門檻裡側,速度頗快,可見是有些拳腳功夫的,這婦人本是一臉凌厲地想要叱呵來人,可在看到站在門外的司季夏時,只一眼,便怔愣住了。
這個婦人司季夏還記得,十三年前就已經在太夫人邊伺候了,名字他已不記得,雖然老了很多,但是髮型不變,便是連上穿著打扮都不變,認出,不難。
司季夏見著這突然出現的婦人不驚也不怔,只對著這婦人微微頷首,客氣道:“在下司季夏,求見太夫人一面。”
“你你你……你是——”婦人盯著司季夏的臉,驚愕萬分,震驚得連話都說不清,就好像還記得司季夏似的。
Advertisement
婦人抖著聲音半天說不出接下來的話,司季夏便又重新道了一遍:“在下司季夏,求見太夫人,勞夫人代爲傳告。”
就在這時,屋傳來了老嫗蒼老緩慢的聲音,雖緩,卻帶著的威嚴,“青姑,是誰在外面?老說過不見任何人,讓他們走。”
青姑沒有回答屋裡太夫人的話,只是瞪大了眼將司季夏上下打量了一遍後匆匆轉回了後的佛安堂。
冬暖故還握著司季夏的手,他的五指在輕,可見他的心並不像他的面一般平靜。
佛安堂裡不知青姑與那太夫人說了什麼,不過頃便聽到有柺杖點地而發出的篤篤聲從屋裡傳來,司季夏的手得厲害了些,冬暖故則是將他的手抓得的。
廊下的風燈猛地晃了晃,青姑攙著一名背微佝僂,頭髮全白的老嫗出現在了司季夏視線裡。
只見老嫗眼眶一直抖不已,直直盯著司季夏的臉半晌,後直直地盯著他右肩,半晌才著蒼老的聲音道:“是你……是你回來了……”
“這是段氏的報應,報應啊……”
司季夏雙肩一,定定看著面前的太夫人,與此同時將冬暖故的手抓,以此讓他能更深一些地到掌心的溫度。
佛安堂的擺設還和十三年前一模一樣,佛龕還是在原來的位置,便是門邊擺放的那一盆花兒,都還是一樣的觀音蓮,不曾變過。
唯一變了的,只有這佛安堂的人而已。
司季夏記得,這位被稱爲太夫人的老婦人原本看起來不過四十一二的模樣,如今不過是十三年過去,蒼老得就好像時間過去了三十年一樣,的頭髮已蒼白,面上已滿布皺紋,便是連背都佝僂了,若非有手上的柺杖作爲支撐,只怕連路都走不穩了。
司季夏說不出自己再見這個太夫人時的覺,只覺歲月自來就是一種奇怪的東西,使人生,使人活,使人蒼老,使人死。
太夫人還是如從前一般,坐在那張鋪著綢的寬榻上,司季夏與冬暖故便坐在寬榻前倚牆而放的太師椅上,青姑站在寬榻旁,看著司季夏還是有些不能回過神,面上還盡是不敢置信的神。
因爲椅子與椅子間隔著小幾,冬暖故的手不能握到司季夏的手,司季夏的手便只能放到膝上,輕輕握拳,看向那一臉嚴肅的太夫人,緩緩道:“太夫人……還記得我。”
這個高門裡的人還記得他,這讓司季夏有些震驚,且記得他的不只是太夫人一人,那青姑似乎也還記得他,而且記得很清楚,否則不會在見到他的時候便出那般震驚的神。
們……爲何如此記得他?
“你和你母親長得這般相像,老如何不記得你?”太夫人似嘆非嘆地道了一句,司季夏覺得看他時候的眼神還是和從前一樣,有同,還有憐惜,此刻似乎還有……悔恨?
“我的……母親?”聽到“母親”二字,司季夏輕握拳的手驀地一抖,面微微發白。
“是啊,你的母親。”太夫人本是緩緩說著話,卻忽地擡高聲音,看司季夏的眼神也突然變得凌厲,語氣變得有些森然道,“老知道你會回來,總有一天會回來,回來報復侯府,如今你的目的達到了,你是回來看侯府的下場的對不對!?”
“侯府變如今這般景,正是拜你所賜不是!?”說到這一句,太夫人的目忽然變得猙獰起來,大有要撲上前來掐上司季夏咽的衝。
佛龕裡的佛祖像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眉目慈善地看著眼前的一切,可他從不說話,從不管人間疾苦百姓苦難。
司季夏怔住了,他以爲……以爲這個府邸裡,至還有這個曾經過他頭頂問他名字的太夫人會不反見到他,原是他想錯了,想錯了……
冬暖故眸倏冷,只覺心口怒火中燒,正要站起時,司季夏擡手抓住了放在小幾上的手。
冬暖故微微一怔,只見司季夏朝一笑,未語,只是將的手抓得的。
冬暖故覺得的心揪疼得很是厲害,因爲在司季夏眼裡看到了哀涼,讓覺得陪他來這一趟侯府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猜你喜歡
-
完結1849 章
大唐之神級敗家子
携系统穿越大唐的赵辰本想做个咸鱼。 没事的时候,种种地、钓钓鱼。 哪想有日,一自称老李的中年男人突然跑过来,说要带赵辰回宫当太子。 赵辰:“当太子什么的没意思,不如我出技术你出钱,咱先在家打打铁!” 老李头大手一挥:“打铁好啊,锻炼身体,要钱管够。” 赵辰:“不如咱挖运河,造福百姓。” 老李头:“好,给钱。” 赵辰“不如咱铺路……” 老李头:“给钱。” 赵辰:“不如……” 老李头:“给……啥,国库空了?” 看到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了十年的国库,现在竟然连老鼠都饿死几只,老李头气的大骂赵辰败家。 却不想第二天,老李头便见万国来朝,说要朝见太子殿下……
341.3萬字8.18 255000 -
完結188 章

我的主君是反派
故事發生在一個不在于歷史一種的朝代~陵國。陵國國主寵愛最小的皇子引起后宮皇后的嫉妒。 “你們聽說了嗎!咱們陵城最無能的的王爺今天就要迎娶王妃了。” “是呀!還是丞相府的千金。” “看來皇帝還是偏愛于他,只是不知道……” “快快別說了!” 陵城的百姓早就已經議論開了一個無能的王爺迎娶了一個品行不端的千金,這應該是陵城里最熱鬧的事情。 “王爺,王妃還在房里等你。” “不去!” “可是王爺,咱們這可是花了銀兩娶進門的,你不去看一眼,那咱們可就是虧大了。” 凌熙恍然大悟的表情,仿佛娶了一個金山銀山回家。 等待一切任務完成之后,公孫暮雪終于恢復了自己原本的身份,她在屬于自己的國度之中拼命的尋找一個她愛的男人,卻再也不是他。什麼?兩塊錢!刷卡一塊八,投幣兩塊,我讓你幫我刷卡,你結果投幣。那兩毛錢我不會給你的。” 方玲轉身,她微微一笑,不管是在哪里永遠不變的就是他那愛財如命的性格。
48.8萬字8 2688 -
完結267 章
六零重組家庭
死在喪屍潮裡的蘇袂,被孩子的哭聲吵醒,甫一睜眼,便被人遞來了枚軍功章和一聲沉痛的「節哀! ” 在黃沙漫天的末世吃了霉變食物多年的蘇袂,乍然看到漫山的青綠,清澈流淌的溪流,和隔壁海島墾荒隊不時送來的魚蝦、黑山羊、海鴨蛋,覺得遵守原主留下的遺願,幫她養大兩個孩子不要太值! 趙恪帶著戰友的軍功章從邊境浴血歸來,收到妻子從瀘市發來的一封離婚電報。 帶著疑惑回家,往日溫柔善良的妻子,陡然變了模樣。 辦理了離婚手續,背著被人打瘸了右腿的長子,抱著剛滿一歲的次子歸隊...... 趙恪覺得當務之急,他應該先找個保姆。
81.5萬字8.18 23192 -
完結264 章
新婚夜,殘疾王爺忽然站起來了
一朝穿越,從王者變成人人可欺的軟腳蝦?不,這不是她的風格!手撕白蓮,虐哭綠茶,調戲美男,一身精湛醫術艷絕天下卻不小心惹上殘疾王爺“閻王懼”!一紙契約,她為他解毒,賺的盆滿缽滿,名利雙收。正準備逃之夭夭,他卻突然從輪椅上站起來,強行將她擁入懷,“調戲完本王不用負責?!”次日,某女扶著腰淚眼汪汪:“騙子!你丫就是個假殘疾!”
47.5萬字8 46731 -
連載3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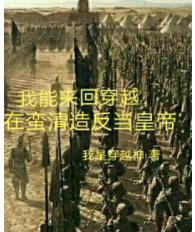
我能來回穿越,在蠻清造反當皇帝
殺伐果斷+冷血+爭霸文+造反+不圣母本書主角每隔一段時間會搞大清洗行動,每次屠殺幾百名上千名不聽話有叛心的手下將領們。對外進行斬首行動。主角建立帝國后,會大清洗
65.6萬字8.33 13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