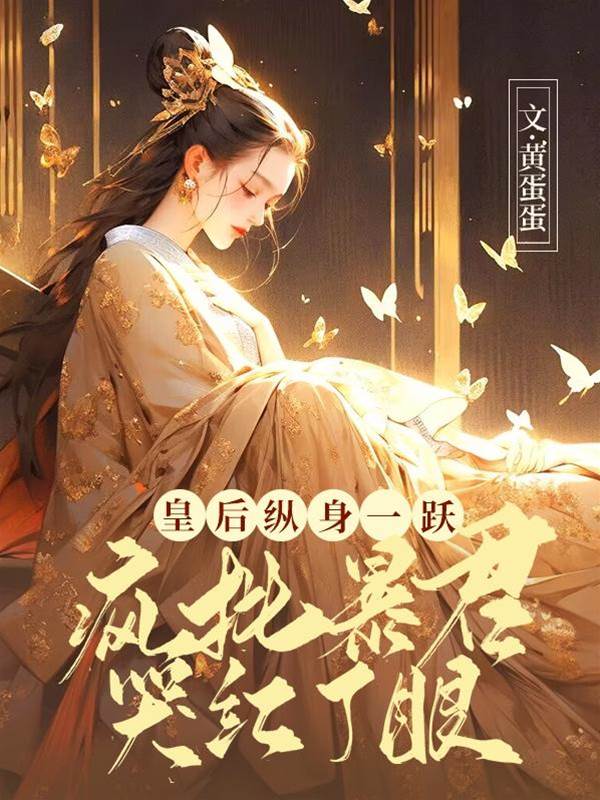《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091 你死她也死
“啊,啊——”樓遠雙手捂著自己綁滿繃帶的臉,渾搐著,在牀上來回翻滾著,喊不已。
他的喊聲有著撕心裂肺的覺,彷彿疼到了人所能承痛楚極點,想要昏蹶,卻又清醒無比的錐心,聲音低沉沙啞得就像一頭想要自我舐傷口都不能的困。
此時的他,很痛苦,很痛苦。
薛妙手擡起打翻點著泌香小銅爐的手,站在牀榻旁冷眼看著沒了泌香的制而痛苦不堪得直在牀榻上翻滾的樓遠,一邊用乾淨的帕子著手一邊對站在一旁面發白得一時間竟是不知該怎麼纔是好的春蕎與秋桐冷冷道:“還杵著做什麼?還不上去用布堵著他的?不怕他不小心咬著舌頭把自己給咬死了麼?”
春蕎恍然醒神,連忙慌手慌腳地從懷裡扯出帕子,就要往樓遠上堵去,然的手才過去,樓遠卻猛地坐起,出手狠快地反掌就劈在春蕎的手腕上,氣勁狠得竟是將春蕎的手腕震麻得良久都擡不起來。
只見樓遠那沒有被繃帶裹住的兩隻眼睛,此刻猩紅得可怖,彷彿失去了理智似的。
“爺!?”春蕎被樓遠那雙滿是紅的眼睛驚到,一時間連聲音都在抖。
然下一瞬,又見得樓遠將雙手死死地按捂在自己臉上,又撕心裂肺地喊起來。
薛妙手見狀,微微蹙起眉,隨之竟是見忽地擡起腳,一腳就踩到樓遠的肚腹上,力道不輕,踩得樓遠的嘶喊聲在那一瞬間有些停頓,繼而竟像瘋了一般擡手蓄氣就要朝薛妙手砍去。
眼見薛妙手躲避不及時,屋外忽然傳來急驟般的琴音,樓遠那就要劈到薛妙手面門上的手刀停頓住,再往前不得。
Advertisement
只見薛妙手又在樓遠肚腹上狠狠踹了一腳,踹得他舉起的手刀收了回去,薛妙手本是微擰的眉心此刻已變擰起,面沉沉,聲音也變得厲起來,看著春蕎道:“把他的堵上,別讓他一時沒把控住把自己的舌頭給咬了。”
說罷,薛妙手又轉頭看向秋桐,聲音依舊冷厲地吩咐道:“還有你,將他的手腳拴拴牢,要是他還想要這張臉,就別讓他。”
“是!夫人!”春蕎秋桐立刻照做了,作毫不敢有慢。
那急驟的琴音還在繼續,直至樓遠的被堵上,手腳被捆牢。
白拂站在薛妙手旁,這纔將掌心按到琴絃上,讓琴聲停止了下來。
樓遠被捆縛著不能彈,雙手反綁在後,讓他本就不到他自己的臉,使得他的雙眼看起來愈加的赤紅。
薛妙手只是神冷冷地看著樓遠那雙像是困一般猩紅的雙眼,忽而竟是笑了,“這雙眼睛,此時此刻看起來還真是漂亮。”
“夫人這個時候不應該誇讚他。”白拂客氣地接話。
“呵呵……是麼?”薛妙手又是輕輕一笑,神又是忽爾間恢復了尋日裡的冰冷,冷聲道,“捱過六個時辰,他就活過來,捱不過,那就是他的命不好了。”
“必須六個時辰?”白拂面無表地看著樓遠的眼睛,問薛妙手。
“六個時辰已經是最短最的時間,沒有六個時辰,就算他活著,他這一世人都要頂著一張潰爛的臉見人,只怕你們沒人願意他這樣吧。”薛妙手又開始拭的手,好似的手不乾淨似的,“這六個時辰很重要,因爲他很可能在這段時間死去。”
Advertisement
白拂抱著瑤琴的手微微一。
“所以,記住了,這六個時辰裡,不能讓他睡過去,不到六個時辰,他臉上的繃帶也不能拆。”薛妙手終於將的雙手得滿意了,隨意地帕子扔在了地上。
“白某謹記夫人的話。”白拂微微朝薛妙手微微欠。
“大琴師可別忘了答應過我什麼。”薛妙手道。
“白某心中記得清楚。”
“既是如此,那我便走了。”
“白某送夫人一程。”
“不必。”薛妙手擡手拒絕了白拂的客套,“留下看著他,讓這兩個丫頭其中一個送我出去便行。”
“那白某便在此目送夫人離開。”白拂倒真沒有客氣,只對春蕎吩咐道,“春蕎,替我送一送夫人。”
“是,白拂公子。”春蕎應聲,走上前來,還未來得及道一聲“夫人請”,薛妙手便已徑自走了。
“守了一夜,秋桐也下去歇著吧,我看著這小子就行。”白拂看了站在一旁的秋桐一眼。
秋桐不放心地看了樓遠一眼,不敢說不,只應聲退下了。
屋裡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牀上的樓遠與牀前的白拂。
白拂又靜靜地看了全上下被捆得牢牢的樓遠一會兒,才拖過一張椅子在牀前坐下,將抱在臂彎裡的瑤琴放到兩上,竟是難得溫和地對樓遠道:“難得我想要對你大發慈悲一次,想聽什麼曲子,我可以爲你上幾曲。”
樓遠只是睜著猩紅的雙眼瞪著他,一聲不吭。
準確來說,就算他想吭聲,也吭不了。
因爲他的上還堵著布帕。
而白拂,似乎也只是隨口一問而已,本就沒有想過要樓遠的回答,是以他自己的話音才落,他便慢慢悠悠地起了琴來。
Advertisement
琴聲幽寧,能讓人狂躁的心緒漸漸平緩下來。
樓遠眸中因疼痛而起的腥紅在這婉轉的琴音中漸漸淡下。
“北霜國的天,馬上就要變了,過不了多日,就要下起大雨了。”白拂慢悠悠地著琴絃,聲音也輕輕緩緩慢慢悠悠的,“你知道我向來不及你聰明,考慮問題也不比你周,你也已經很久沒有爲大人做過什麼了,這一回,你應當來爲大人撐一回傘了,我想你應當不會有何異議纔是。”
“而要爲大人撐傘,你就不能只呆在這桃林別院裡,下雨了,你的裳和鞋子,總會要被雨打溼。”
樓遠在牀上蹭著子,將背蹭到牀欄上,艱難緩慢地坐起。
白拂看著樓遠艱難地坐起,也只是看著,並未上前扶他一把,也沒有要扶他一把的意思。
樓遠眸中的赤紅雖在琴聲中有減退,卻只是許,待他坐起後,才見得他微微點了點頭。
他在同意白拂說的話。
大人是他們的父是他們的師更是他們的恩人,若是有機會在雨日爲大人打傘,他們都將會義不容辭並且義無反顧,就算送上他們的命。
他也知道北霜國很快就要下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雨,比南蜀國的那一場雨來得還要大還要迅猛,也的確像白拂所言,他要想爲大人撐傘,就絕不能只是呆在這桃林別院裡。
所以,薛妙手施附在他上的折磨苦痛,他必須忍過去。
無論如何都要忍過去。
白拂不說話了,只垂著眼瞼專注著琴。
樓遠早已承不了臉上那比被人千刀萬剮還要錐心的疼痛,又是渾搐抖著倒在了牀榻上,連呼吸都在抖,發白的脣漸漸變得乾裂。
Advertisement
白拂並未理會樓遠的痛苦,他還是隻專心地撥弄他的琴絃,似乎此時此刻他的眼裡,只有他的瑤琴而已。
不知過了多久,當樓遠雙手抖得厲害好似要掙手上的繩索抓按上自己的臉而不得,折磨得他又開始在牀上翻滾的時候,白拂將十指按在琴絃上,按停正錚錚有聲的琴絃,這才又緩緩淡淡地張出聲。
“我昨夜找了那個瘋丫頭,與說了幾句話。”
本是在牀上痛苦地翻滾不已的樓遠在聽到白拂這麼一句話時,子微僵,頓在了那兒,而後倏地翻過來,定定盯著白拂看。
“我才一提到那個瘋丫頭,你就不疼不滾了?”白拂眼裡有些鄙夷與不屑,“怎麼,想知道我與那瘋丫頭說了什麼?”
“其實,我與說的話,十個指頭都能掰得過來,因爲我嫌惡,還不想與多說一句話,不過爲了你小子,我又不得不與說上幾句話。”白拂嫌惡融雪,是真的嫌惡,不管是樓遠鍾也好,是李悔說是好姑娘也好,他如今對的覺,也還是隻有嫌惡而已。
或許日後這種覺會轉變,那也是日後的事了。
樓遠又在努力地憑藉著牀欄坐起,白拂則是不疾不徐道:“急什麼,還怕我吃了不?放心,還勾不起我要吃的慾。”
“好了,坐起來了就好好坐著吧,不就是想知道我與說了什麼,放寬心,我沒有在面前說任何一句你的不是,你在心裡,還是那個好得不得了的爺。”白拂一手按著琴絃,一手撥著琴絃,撥出“繃繃”的沉悶聲響,“我不過是與說你快死了而已。”
樓遠微微睜大了眼,眸中那因方纔的悠緩琴音而淡去的腥紅似又開始卷漫上來。
他說不出話,只能等著白拂接著往下說。
“我還說,若要你活著,就要用的命來換。”白拂面平靜,像是在說一件與他毫無干系的事似的,“你猜怎麼說?”
白拂當然不會想要樓遠的答案,只聽他接著道:“毫不猶豫地說願意換,呵呵,這倒是我沒有想到的,沒想到一個一無是的瘋丫頭居然將你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
“然後啊,你猜我又說了什麼?”白拂似乎與樓遠開上了玩笑一般,竟是一問接一問,而明明樓遠本就不可能回答得了他的問題。
只見樓遠一瞬不瞬地盯著他。
白拂忽然輕輕淺淺地笑了,“我說,要是想救你的命,就要到隕王府去走一趟,因爲能救活你的命的東西,只有隕王府裡纔有。”
“再然後,我就讓兩名影衛將帶出府去了。”
白拂說得好像在說一件極爲尋常的小事,而樓遠雙眸圓睜,某種赤紅較之前更甚,一雙眼睛紅得好似池煉獄,正翻滾著沸騰的怒火,蹭到牀邊猛地就站起。
他太過於急切,急切得他竟是忘了他全上下都捆綁著繩索,本讓他走不得。
是以他纔想要擡腳,整個人便朝前重重跌趴在地。
而就在他的下頷就要撞到冷的地面時,白拂迅速躬出手揪住了他頸後的裳拎起他的上半,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纔不至於他的臉撞到地上。
然後就是白拂帶著不屑的聲音冷冷道:“你這副隨便一個人來都能將你踩死的模樣還想著去救你的人?先省省吧。”
白拂說著,手上一提力,將樓遠拎起,用力扔回了牀榻上,而樓遠還不死心,翻子又要坐起,誰知卻是遭來白拂一腳踹在他的肚腹上,踹得他疼得立刻蜷起子。
“放心,邊的那兩名影衛手不差,應當能護住兩個時辰,不過這兩個時辰之後會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我想,依雅慧郡主那子,應當不會急於將殺死解恨,應該會想著法子來慢慢凌至死纔是。”
“我是不會去救,而冰刃一時半會兒也不會知道在哪兒,你要是想要救的話,就自己好好捱過這六個時辰自己去救。”
“捱不過,就你死,也死。”
樓遠雙眼紅得能滴出來。
------題外話------
三更奉上!
明天的更新應該在下午,姑娘們早上勿等~
猜你喜歡
-
完結1212 章
法醫嬌寵,撲倒傲嬌王爺
苏青染,21世纪最具潜力的主检法医,因为一次网购,被卖家免费送了次时光之旅:记得好评哦亲~ 不仅如此,这时光之旅还超值赠送了她一口棺材和里面躺着的王爷。 更不幸的是,她是躺在棺材里给那王爷配冥婚的——女人。 苏青染顿时小脚一跺,“退货,我要退货!” “看了本王的身子,还想退货?” 自此,苏青染便被一只腹黑狐狸缠上。 她验尸,他坐堂,她断案,他抓人,绝配! “今晚,王妃的小兜兜好生诱人,让本王看一看这里面是不是一样诱人?” 破案路上,某王爷打着断袖的幌子一言不合就袭胸。 “滚!” 宠文,1V1,黑吃黑,青酒出品,坑品保证。
165.5萬字8 41155 -
完結660 章

富貴小丫鬟
一覺醒來,穿越成了唐國公府小丫鬟。富貴安逸的國公府,雲舒開啟了一段被富貴榮華庇護長大的悠閒生活。她開始多賺錢,廣買田,一切都是為了未來當個小地主,過著滋潤快樂的日子,只是那個木納的大將軍,就是不知道變通,好像一抓住要的東西就不願意放棄,這不是就賴住她不放了。
157.5萬字8 166920 -
完結453 章

下山後,我玄學大佬的身份藏不住了!
【爆笑+沙雕+輕靈異】 師傅去世吩咐她下山,在城市里祛除惡靈,積攢功德,她天生陰命,此路必定危險重重! 但她沒想到,居然踫到了一個喜歡粘著她的霸星… 師傅卻托夢再三警告,不能讓她靠近霸星,不然兩人必定霉運連連或是丟失性命。 前幾世他們都不得善終,而這一世又會如何? “清辭,我不會讓你離開我的,哪怕失去性命,我都不許!” “程煜,前幾世都是你護著我,這輩子輪到我守著你。”
44.4萬字8 33824 -
完結260 章

農門醫女:十兩銀子買個王妃
蘇千荷是前途大好的醫學院吉祥物,沒想到有一天不幸穿越了。揣著僅有的十兩銀子,撿漏買下古代“豪華別墅”,哪知道還附贈一個病秧子王爺。“恭喜您成功獲得殉葬王妃稱號。”展灃:娘子的救命之恩無以為報,本王只好以身相許蘇千荷:我再也不貪小便宜了,現在…
64.6萬字8 51667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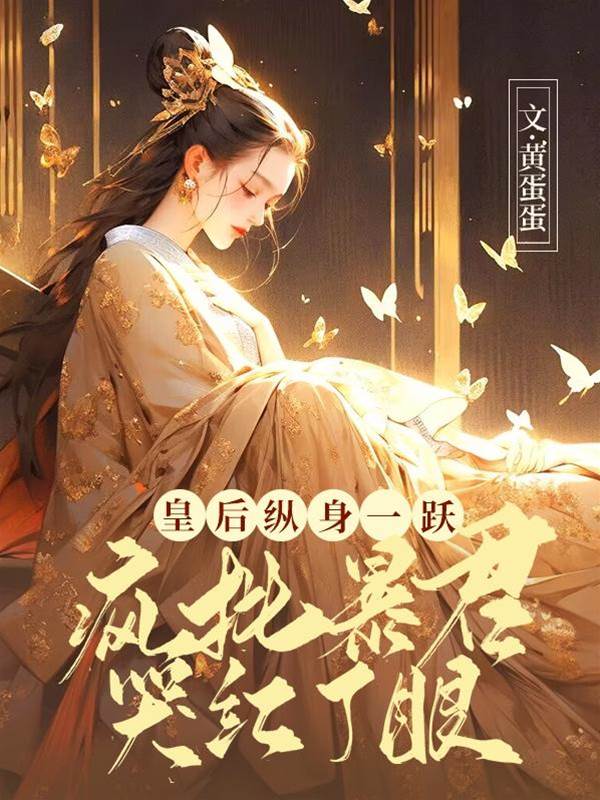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連載136 章

我是卷王穿越者的廢物對照組
時書一頭悶黑從現代身穿到落後古代,爲了活命,他在一個村莊每天干農活掃雞屎餵豬喂牛,兢兢業業,花三個月終於完美融入古代生活。 他覺得自己實在太牛逼了!卻在河岸旁打豬草時不慎衝撞樑王儀仗隊,直接被拉去砍頭。 時書:“?” 時書:“操!” 時書:“這該死的封建社會啊啊啊!” 就在他滿腔悲鳴張嘴亂罵時,樑王世子身旁一位衣著華貴俊逸出塵的男子出列,沉靜打量了他會兒,緩聲道:“學習新思想?” 時書:“……爭做新青年?” 謝無熾面無表情:“6。” 這個朝代,居然、不止、一個、穿越者。 - 同穿古代卻不同命,謝無熾救時書一命。時書感激的找他閒聊:“我已經掌握了這個村子的命脈,你要不要來跟我混?吃飽到死。” 謝無熾看了看眼前衣著襤褸的俊俏少年,淡淡道:“謝了。我在樑王座旁當謀士,生活也挺好。” “……” 感受到智力差距,時書忍了忍:“那你以後要幹嘛?” “古代社會,來都來了,”謝無熾聲調平靜,“當然要搞個皇帝噹噹。” 一心一意打豬草的時書:“…………” - 謝無熾果然心思縝密,心狠手辣。 時書驚慌失措跟在他身旁當小弟,眼睜睜看著他從手無寸鐵的新手村黑戶,積攢勢力,拓展版圖,逐漸成爲能逐鹿天下的雄主。 連時書也沾光躺贏,順風順水。 但突然有一天,時書發現這是個羣穿系統,只有最後達到“天下共主”頭銜,並殺光其他穿越者,才能回到原來的世界。 “……” 一個字:絕。 時書看看身無長物只會抱大腿的自己,再看看身旁手染滔天殺孽、智謀無雙的天子預備役謝無熾。 ——他還不知道這個規則。 時書深吸了一口氣。 當天深夜。 時書拿著一把短刀,衣著清涼,白皙肩頭微露,誠惶誠恐爬了謝無熾的牀。
60.9萬字8 4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