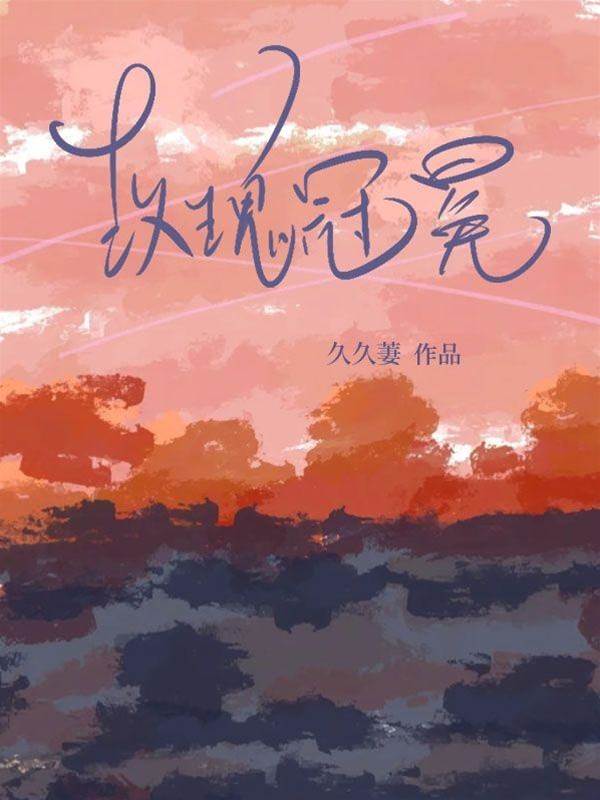《日久必婚:總裁夜夜歡》 第三十二章:你配不上它
歐延冷冷一哼,推開多的管家:“下去領罰!”
“是。”李管家覺得自己委屈的,但是先生都發話了,他也不好再說什麼,快步離開偏廳,還不忘給二位關上門。
簡直是一溜煙的功夫,畫風就變了。
沐染抬起頭,吃驚的看著面前盛氣凌人的歐延。
他怎麼會在這里,不是說不想見到嗎?
歐延只是和沐染對視了一秒,繼而別開了目,朝著一旁的傭人命令:“把鋼琴給我砸了!”
傭人們聞言,均嚇了一跳,這麼貴重的鋼琴,先生居然要砸掉?
有錢人的思維,都這麼奇怪嗎?
見兩旁的人久久沒有反應,歐延怒了,大手一揚,桌上的花瓶陶瓷紛紛碎了一地:“聽到沒有,我讓你們砸鋼琴!”
零星的脆響聲嚇壞了傭人們,一個個紛紛應聲,然后作起來。
不一會兒,一個個便都拿著錘子,重回到了偏廳。
還在愣神狀態的沐染,被這仗勢嚇到了,抬起清澈的大眼睛,張的看著歐延:“歐先生,你這是做什麼!”
“你配不上它。”薄冷的吐出淡淡的一句話,卻是將沐染的地位從天堂打了地獄。
如果心系別的男人,那麼,就不再是他的第一寵兒!
歐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一定要徹底斷絕沐染對藍亦書的念頭!
對上他厭惡的雙眸,沐染渾一,眸里升上濃烈的悲戚。
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貶低。
前段日子,明明是他自己說,要做背后最大的靠山。
Advertisement
是他說的,以后不會有人欺負了……
可是現在,他又在做什麼呢?
沐染咬著下,李管家剛才的那些話,逐漸在心里破滅了。
不可能的!
歐延這麼瞧不起,會為買下路易十五呢?
他剛才,可是親口否認的啊!
歐延轉過,面對著那架宏偉壯觀的歐式鋼琴,冷冽的啟開,吐出毫無溫度的一個字:“砸!”
傭人遵令,一個跟著一個抬起手臂,那五六的錘子即將落下,遭遇歷史存封的天價鋼琴,即將被砸的碎骨!
沐染痛心疾首,急的都快哭了。
在錘子即將落下的一瞬間,大一聲:“等等——”
也是因為這一聲,傭人們的作統一停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還該不該繼續。
沐染驚出一虛汗,在歐延下令之前,慌慌張張繞到他面前:“歐先生,既然你把這架鋼琴送我了,那就是我的所有了,你沒有權利砸壞它的!”
“是嗎?”歐延好笑的看著渾是汗的小人,長指一勾,挑起面頰上的一縷長發,繞在指尖把玩:“連你都是我的,你說這架鋼琴,算不算我的?”
“你……”沐染被他這條挑逗般的作惹怒,一把扯下他的手,怒道:“你無理取鬧!”
大清早的,不是對冷言相待,就是要砸鋼琴,不是無理取鬧,是什麼?
歐延看著怒氣沖沖的臉,真是覺得好笑。
做錯了事的人是,有什麼資格沖他發火?
Advertisement
本來就高昂的怒火,再次燃熊熊烈火,這次歐延擒住沐染的下,一個用力,將狠狠抵在鋼琴上,雙臂攤開,形一個圈,而沐染就是圈中的獵。
“是我無理取鬧,還是你無理取鬧?”男人冷笑著問,玫瑰的薄漾開一抹腥的弧度:“沐染,昨天晚上你去了哪里,做了什麼,要我給你復述一遍嗎?”
此話一出,沐染的背脊當即僵了。
就猶如一只被人牽住線的木偶,舉止言語都由不得自己。
只覺得背后冷異常,堅的鋼琴材質,抵的脊梁一陣疼痛。
“對不起,我……”沐染垂下眼睛,回想昨日的種種,至今仍能到蝕骨的疼痛。
說不下去了,怎樣才能坦然的,把淋淋的傷口攤在他面前?
歐延神冷冽,寒冷的雙眸深深鎖著沐染,從的面部表就能分辨出,現在,恐怕又想到藍亦書了吧!
握住鋼琴邊緣的手,由后落到沐染腰上,他強行和在一起,每一每一毫都合的不分:“你什麼?把過程給我從頭到尾復述一遍!”
著他的溫,沐染為難的紅了小臉,四周可到是傭人,歐延怎麼可以毫不忌諱。
“歐先生……”正要開口,拜托他離自己遠一點,卻見歐延危險的瞇起眼睛:“你我什麼?”
“延……”沐染及時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弱弱的出來:“那個,延,你可以,稍微離我遠一點嗎,這里到都是傭人,影響不太好吧?”
Advertisement
知道小丫頭面子薄,歐延一道冷眼掃過去,還舉著錘子的眾多傭人,立馬裝聾作啞,井然有序的排一隊離開偏廳,把地方騰出來,供他們二人繼續卿卿我我。
偏廳空無一人,沐染這下更尷尬了,周的空氣都是冷的,覺自己即將被凍死,努力鼓起勇氣,對視面前的男人:“你先答應我,不要生氣好不好?”
“你應該知道,我這個人,一向沒什麼耐心。”雙臂突然用力,歐延將沐染抱懷中,將擱在鋼琴上,叉開雙,別在自己腰間。
這個作,可謂是曖昧到了極點……
他就是要一面和他曖昧,一面談論別的男人,要清楚的明白自己的份地位,不要妄想和別的男人有一段天地的,因為沐染,生來就注定是他歐延的人!
,他給不了,也最不屑!
但是論食住行等一系列質,他可以給全世界最好的!
沐染咽了口唾沫,過大到男人炙熱的溫,他們現在的作,就好像是在做不可描述的事,一張小臉不由得得緋紅,垂下腦袋,試圖忽略眼前曖昧的一幕。
可是歐延不準,強扣住的下,將的腦袋抬起來:“回答我!”
猜你喜歡
-
完結32 章
貪財好你
李至誠x周以 游戲公司總裁x大學英語老師 短篇,正文已完結,5.28(周五)入V。 —— 戀愛前的李至誠:有錢又吝嗇的當代葛朗臺。 戀愛后的李至誠:千金博美人一笑的賈寶玉轉世。 戀愛前的周以:跆拳道黑帶、能一口氣抗十八升桶裝水上六樓的猛女。 戀愛后的周以:(只是停電)一咕嚕鉆人家懷里揪著衣角嚶嚶嚶“學長人家害怕~”。
10.4萬字8 5285 -
完結3607 章

妻不厭詐:婁爺,我錯了!
強勢桀驁的商業帝王婁天欽居然結婚了,結婚對象還是一個不知名的狗仔——姜小米。新婚之夜,男人拋下妻子前往醫院看望蘇醒過來的植物人前女友。姜小米跟一個混血男人打了一晚上麻將,理直氣壯:各玩各的。五年后,小女人偎依在男人懷里:“老公,這個月還差點…
518.6萬字8.18 162676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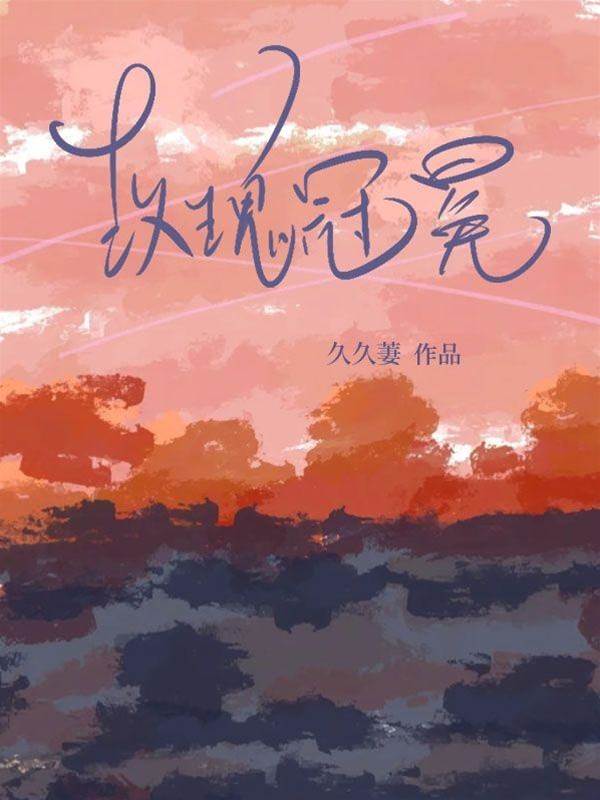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完結532 章

渣男逼我離婚?轉頭高嫁京圈大佬
【重生+寵文+雙潔+男主妻管嚴+女主第一美】昔日大佬姜寧一覺醒來就重生成了嫁入豪門的灰姑娘。 灰姑娘出身農村,是個父母不詳的小可憐。 渣男利用完她,就迫不及待的要跟她離婚,將她趕出豪門! 被人嘲諷: "一個鄉下小村姑也配得上程總?” "大鵝還想裝天鵝?呸!不要臉!” 面對天崩開局,姜寧火速簽下離婚協議書。 離婚的姜寧卻一路開掛: 投行大佬是她! 新晉首富也是她! 更讓人沒想到的是,原本父母不詳的鄉下小村姑,居然搖身一變,變成了失蹤多年的頂級豪門的千金大小姐! * 沈經年是京圈頂級豪門之首沈家家主,也是高不可攀的京圈禁欲佛子。 卻在遇到姜寧后瘋狂心動,與她談起了戀愛。 就在此時,有人翻出了沈經年從前接受記者采訪時稱自己是不婚主義者的視頻。 一時間,所有人都在嘲笑姜寧只是沈經年的玩物而已! 沈家家主不會娶一個離過婚的女人。 就在此時: 沈九爺的微博昵稱,突然改成了:姜氏沈經年。 眾人:? 不可能!站在云端的九爺怎麼會做這種事? 肯定是被盜號了! 很快: 一條視頻刷爆社交網絡。 視頻中,那位自稱不婚的沈家家主當著所有媒體記者的面,單膝跪在姜寧面前,高調求婚,“姜寧,我愛你!你若不嫁,我愿入贅,以妻之姓,冠我之名,生生世世只忠誠于你一人!”
132.6萬字8 62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