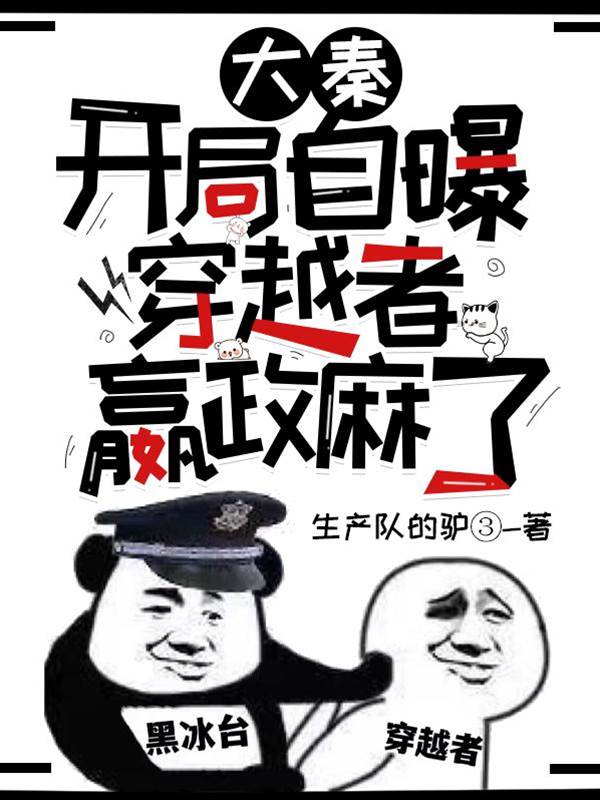《盛寵為后:皇上請別鬧》 第一百七十二章 紛爭難平
事到如今,清月心中只有悔恨,卻不能說出一個不字,因為已經看得很明白,不管自己再怎麼堅持,北辰軒也不可能會改變他的態度,這樣下去只會讓他越來越討厭自己,不希最后搞得自己,為他最不想見到的人。
被自己喜歡的人討厭,恐怕是最能讓一個人痛苦萬分的事了,表很痛苦,眼神里滿是酸楚,把心里面的無奈與絕都寫在臉上,輕輕地低下頭,然后掏出一瓶墨綠的東西,對北辰軒說道:“這就是解藥,只需服用一次,慢慢就可以完全恢復,給你吧,你做定奪就好,我聽從你的安排。”
“清月……”北羽心很是難地說道,很清楚,自己這個丫鬟做那些事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哥哥和,只是要除掉葉蘭心,這樣的話,自己就還能回去做北疆的皇后,而哥哥也可以以此作為威脅,功登基。
“你做的沒錯,算你想的明白。”北辰軒接過那瓶解藥,很是語重心長地說道,“我知道你是想為我們做點好事,可是在這個世界上,好心有可能會辦壞事,你并不是站在我這個位置上,所以考慮問題不那麼全面,也許今天我們可以用解藥來威脅凌傲天,可是以后呢?那是一個打不倒的家伙,永遠不會輕易被打敗。”
“奴婢知錯,以后不會再自以為是,自作主張了,還請大皇子罰我。”清月很是委屈地說道,眼睛里面已經滿是眼淚,看上去無比可憐。
看到這樣,北辰軒心中也是有些心疼,畢竟是為了自己才做這麼多,他一本正經地說道:“現在我就去把解藥給凌傲天,然后和他商量事宜,你們還是別去了,放心在家休息,你們放心,我一定會保證你們的安全。”
Advertisement
“是我做錯的事,怎麼可以讓大皇子為我戴過呢?我還是跟著去吧,那大歷國的皇帝想怎麼懲罰我,我都絕無二話,任憑他罰便是。”清月明白他的心意,頓時心中一暖,原來他也是關心自己的,并不是對自己毫無覺,可是,又怎麼舍得讓心的人去為自己戴罪罰呢?
“不用,我相信這點面子他還是會給的,畢竟從此以后他就是我們最堅實的盟友,你就不用擔心了,快點回去,這些天皇宮很混,要小心為上,發現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就趕快來找我。”
北辰軒抬起手示意不必跟著去,他相信凌傲天還不至于那麼小氣,雖然他那麼妻子,簡直是妻如命,但他絕對不會為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更何況這個人已經知道錯了。
清月不再堅持,心中很是,輕輕地點了點頭,然后就和北羽心一起看著這個男人從眼前離開,這個男人,也許一生都不能夠去,可如果自己還活著一天,就會守護在他邊一天。
這個時候,北羽心也覺到了自己邊這個丫鬟對哥哥的心意,不由得在心中嘆息:“哎,你多,他卻不領,這個世間多的是這樣無可奈何的事,可憐的清月,以后我們倆就好好地相依為命吧,在這世中生存下去已經不容易,就不要再奢求太多虛妄了。”
回到北苑,北辰軒親手將解藥到凌傲天手中,對他囑咐了一下使用方法,然后又開口說道:“你說的沒錯,是那個丫鬟下的毒,不過歸結底,還是因為我而起,所以要怪罪,你就怪我吧。”
Advertisement
“我還沒那麼小氣,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解藥,不為懲罰任何人。”凌傲天很是從容地這樣說道,“只有認識到錯就行,好在事還有挽回的余地,所以我可以原諒你們,我們之間的恩怨這就樣一筆勾銷。”
“凌兄果然氣度不凡,我自愧不如,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從今往后我們就是朋友。”北辰軒開心地說道,然后吩咐手下牽來一匹快馬和食。
北辰軒親自送凌傲天出城,兩個人并肩而行,凌傲天手中牽著馬的韁繩,懷里揣著解藥,他告訴自己,就算是拼了命,也必須把解藥完好無損地送到葉蘭心邊,這瓶解藥,可是關系到和肚子里那個孩子的命,太珍貴。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凌兄,我就不耽誤你時間了,旅途奔波勞累,還請注意。”快走到大門的時候,北辰軒很是客氣地這樣說道。
凌傲天微笑道:“好,那我們來日方長,你放心,答應你的事我一定會做到,只要你有任何需求,隨時找我,我一定支援你,在你去往皇位的路上助你一臂之力。”
“有你這句話就夠了,我和我的這個妹妹目前算是勢均力敵,不分上下,若不是你答應我,我們之間的斗爭還不知道得繼續到何年何月,整個國家就會陷憂外患當中,你算是幫了我的大忙了。”北辰軒很是激地說道。
凌傲天拍了拍馬鞍,然后轉語重心長地說道:“我之所以幫你,不是因為你給了我解藥,也不是因為我們都是男人,歧視你妹妹,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很有抱負的人,希你不要讓我失,要讓你的子民過上好日子,這樣他們才會恩你做出的貢獻,得民心者得天下。”
Advertisement
這些話,都是他發自肺腑之言,自從他登基以來,一直都嚴于律己,嚴于律人,始終把百姓的生活放在心中,為他們著想,這才得到了今天大歷國的繁榮。
猜你喜歡
-
完結1614 章

從我是特種兵開始打卡
穿越到《我是特種兵》的世界,得到輔助引擎的支援,他逐步成為所有士兵的王,特種兵,通訊兵,飛行員等等,在每一個兵種的領域他都做到了極致,成為當之無愧所有士兵的王!
300萬字8.18 51885 -
完結83 章

帶上將軍好種田
重生后的蘇念悠有三個愿望: 1.不要嫁給上輩子那個腿瘸眼瞎臉上有疤的老光棍。 2.帶領全家發家致富,從此走上人生巔峰! 3.咦咦咦,老光棍居然是個帥哥?算了,我還是選擇發家致富!啥?老光棍還是個將軍?這大腿到底抱還是不抱? 裴驍最近只有一個心愿: 那便是→_→讓女主抱自己大腿。 男主:我這金閃閃的大腿,你確定不要? 女主:不,我選擇跟你一起發家致富謝謝。 食用指南: 1、架空文,勿扒 2、1V1甜文,雙處
23.9萬字8 26056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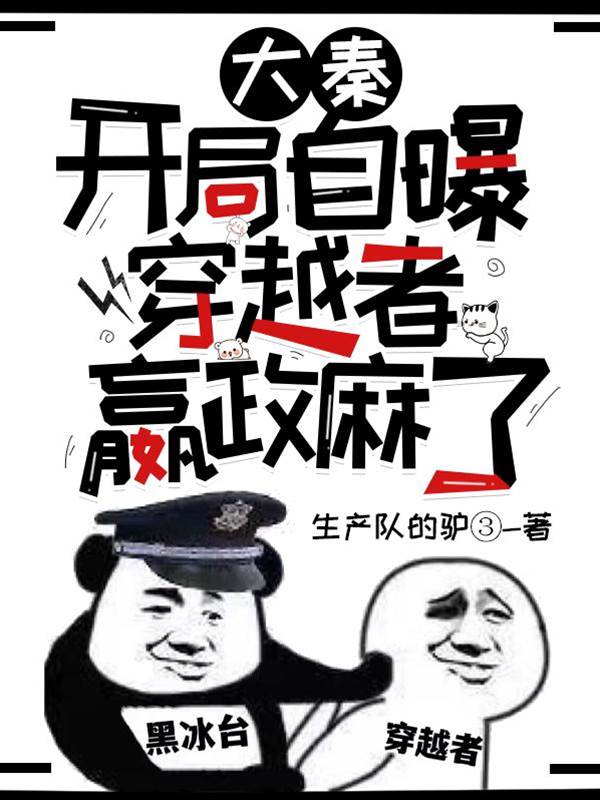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
完結427 章

瞎眼贅婿,老婆竟是當朝女帝
孟輕舟穿越書中,意外覺醒盲目劍聖係統,成為一名瞎眼劍聖。對書中劇情了如指掌的孟輕舟,不願成為主角裝逼打臉的工具人。隻好擺爛享受生活,每天養花遛狗,閑時逗逗丫鬟,陪伴賢惠妻子。卻不想。他住的是皇宮大院,撒嬌的丫鬟是冷豔劍仙,養的花是千年神藥,遛的狗是鎮國神獸,賢惠老婆更是當朝女帝!女帝費盡心機,讓所有人在孟輕舟麵前演戲,扮演一個普通家庭,隻為在閑暇之餘,有一處安心之所。但沒想到,不僅自己隱瞞了身份,孟輕舟也隱瞞了劍聖實力!叛亂藩王:“東方琉璃你沉迷孟輕舟的男色,不理政事,該誅!”孟輕舟:“廢話,沉迷我的男色,就是我老婆的正事!”敵國使者:“要麼割地賠款,要麼國破家亡!”孟輕舟:“我就一畝三分地,你還要搶?劍來!”…當諸國聯合起來,企圖阻止女帝的統一之路,孟輕舟孤身趕赴邊境,解開雙目封印,在睜眼的剎那,劍聖橫空出世!孟輕舟:“我家門前幾畝地,有這麼大吸引力嗎,滿天神魔都來搶奪?”
87.7萬字8.33 333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