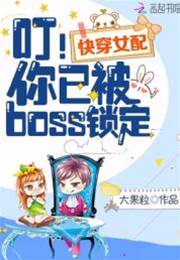《總裁蜜令,獨寵新妻不許逃》 第24章:相敬如賓
“怎麼回事?”紀殊彥不解,輕聲問道,“為何蘇先生不愿上臺?”紀殊彥的目也掃過臺下靜坐著的岳父,原本以為蘇靖是因為妻子早逝,所以不愿獨自上臺。可是看這形,好像并沒有那麼簡單。
蘇夏見問,垂下眼瞼,躲避著耀眼的燈,將眼中失落的淚意抿回心底。
“他……”蘇夏深吸一口氣,努力調整好表,佯作輕松地說道,“從我出生就是這樣了。媽媽去世對我爸的打擊很大。他……不愿意面對我。”
“其實,我也習慣了。”蘇夏努力掩飾著心里的失落,出笑容。
紀殊彥恍然。難怪一直覺得蘇夏跟父親之間很疏離冷落,幾乎沒有聽提起過父親,原來……
他看著蘇夏極力抑心中失落傷的模樣,覺得有些心疼。這個孩子,從小就沒有母親,跟父親又是這樣冷冷淡淡的關系。難怪總是將自己偽裝刺猬一樣,那是因為,沒有人保護啊。
紀殊彥更地握著蘇夏的手,眼睛沒有看,聲音卻溫和地傳了過去。
“別傷心了,以后會好的。”
以后……蘇夏聞言,側頭看了看旁的紀殊彥。以后,就要跟這個人生活在一起了呢。蘇夏分不清自己是什麼心,只含了一縷笑意,聽著紀殊彥父親的祝詞中,那一連串的“白頭偕老,相敬如賓。”
相敬如賓,已經是彼此之間,最好的生活了吧。
蘇夏端茶,帶了溫和恭謹的笑意,分別遞到紀殊彥的父親母親前。
“爸,媽,請喝茶。”蘇夏的聲音清凌凌的,這兩個稱呼喚出來,稍顯生。
紀海夫婦笑著接過,蘇會長也接過了紀殊彥手中的茶,笑意溫和。
蘇夏尚在怔仲間,臺上又只剩下自己跟紀殊彥。
Advertisement
“蘇夏小姐,你愿意為紀殊彥先生的妻子,從今天開始相互擁有、相互扶持。無論是好是壞、富裕或貧窮、疾病或健康,都彼此相、珍惜,直到死亡嗎?”司儀的聲音拉回了蘇夏的思緒。
抬眼看著上目深邃的紀殊彥,聲音輕淺,卻被話筒無限放大。
“我愿意。”
繁瑣而華麗的婚禮終于結束,紀殊彥牽著蘇夏的手向滿廳的賓客敬酒,一圈下來,蘇夏的雙已經酸脹不已,先前扭傷的腳踝也作痛。
“累死了。”蘇夏蹙眉,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來,踩在高跟鞋上疼痛的雙腳立刻解放,蘇夏見四下無人,索把高跟鞋了下來,輕輕按著腳踝。
腳趾已經有些紅腫,高跟鞋的邊沿在腳背上,印出了一圈紅痕。
“吃點東西吧,”紀殊彥也坐下來,目瞥過蘇夏的腳,說道,“一會兒就回家,回去好好休息。”
蘇夏打量著桌上的飯菜,樣樣致,可卻沒有什麼食。累了一天,力幾乎支。
“小夏,爺爺走啦。”蘇會長走到蘇夏邊,溫言說著。蘇夏勉力一笑,目卻著大廳門口,已經快要走出去的父親。
父親終究還是不能釋懷,即便是在自己新婚的典禮上,他也依舊是那一副淡漠疏離的神。
蘇會長安地拍了拍蘇夏的肩膀,離開了大廳。婚宴上賓客已散了,蘇夏實在吃不進東西,也起跟紀殊彥走出去,準備回家。
“你父親的事……你別太難過了。”紀殊彥看著神失落的蘇夏,不知為什麼,安的話口而出。話音未落,紀殊彥自己心中也暗暗吃驚。
蘇夏默默點頭,被紀殊彥輕攙著手,往停車場走去。兩條依然酸脹著,雙腳也在高跟鞋里疼痛。蘇夏提著紅敬酒禮服的擺,走的很慢,腳下的酸疼讓也不抓著紀殊彥的手,借助他手臂的力量分擔重。
Advertisement
“殊彥。”
一個清亮溫的聲在后響起。蘇夏看到紀殊彥形一頓,隨后松開了自己的手。
濃郁的甜香順著風襲來,幾乎掩蓋了旁紀殊彥上貫有的薄荷氣味。蘇夏比紀殊彥先一步回過頭去,站在后的,是個艷的人,角的笑容跟上的甜香一樣濃郁。
蘇夏指尖上的來自紀殊彥掌心的余溫迅速被風卷走。愣愣地看著眼前的人挪包裹在短中的纖細長,一步步踱到紀殊彥前。
“這麼多年了,殊彥,你還是喜歡薄荷氣味。”那人閉上眼睛,嗅著空氣中殘余的一薄荷味道,睫輕輕。
蘇夏看著細膩白皙的和致的妝容,心中暗暗想著,這個人的裝扮,比自己這個新娘都要致。
可是誰呢?
蘇夏不由自主轉頭去看紀殊彥。紀殊彥默然,眼睛盯著眼前的人,片刻怔忡后,眸中竟然流出一傷的神。
“這麼多年了,你也還是喜歡Lolita的甜香。”紀殊彥深深著眼前的人,聲音溫和,像是帶了追憶的愫,慢慢說著,角勾起了一弧度。
“還不是怕你認不出來了。”那人一笑,嫣然無方,出整齊潔白的牙齒。的目落在紀殊彥肩上的一片花瓣上,笑了笑,自然而然地手替他拂去,那花瓣飄下來,沿著蘇夏的緩緩落在地上。
蘇夏的眉峰蹙了起來,一雙眼睛冷清淡漠,盯住這個艷人的瞳孔。雖然自己對紀殊彥并沒有什麼,可他畢竟已經是自己的丈夫,何況,今天還是他們新婚的日子。
這個人的種種舉,讓蘇夏敏銳地捕捉到了心的敵意。很顯然,跟紀殊彥是舊相識了,或許還曾有過什麼,這些,蘇夏都不在意。
Advertisement
可是現在,顯然沒有把蘇夏放在眼里,旁若無人地做出種種過分親的舉。這一點,讓蘇夏心里很不舒服。
“紀殊彥。”蘇夏著紀殊彥開口道,“這位是?”
紀殊彥剛要說話,眼前這個人卻已經上下打量著蘇夏,聲音中像是帶了幾分敵意,似笑非笑地說著:“你就是蘇夏啊。”
“你也可以我紀夫人。”蘇夏雖然不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來頭,可面對這樣貌似不屑的目,也忍不住冷冷地回應。
果然,那個人笑容一僵,目也凌厲了幾分,在蘇夏臉上逡巡著。蘇夏目坦然冷淡地跟對視著,一言不發。
“殊彥,幾年不見,你已經是有妻子的人了。”那人這樣說著,看向紀殊彥的目弱了幾分,神也很是傷的樣子。
“蘇夏,你先回去吧。”紀殊彥避開蘇夏灼灼的目,轉司機過來,吩咐道:“把夫人送回家。”
“紀先生,那您呢?”司機忙問道。
那人見狀,微笑著出手來,將掌心的車鑰匙遞到紀殊彥面前,說道:“好久沒一起兜風了。”
紀殊彥看一眼蘇夏,接過車鑰匙,跟那個人一起走開了。
蘇夏坐在車里,強忍住想要回頭去看紀殊彥背影的念頭。盡管心狐疑,對那個人的警惕讓蘇夏惴惴不安。可是蘇夏依然在不停地告誡自己,不要多管閑事。
這是一場沒有任何牽絆的聯姻,是不該拿尋常夫妻間的心態來約束彼此的。
蘇夏深呼吸了幾次,心漸漸平復下來。
回到家中,看著滿屋大紅的喜字,蘇夏搖搖頭,苦笑了一下,踢掉高跟鞋,赤腳踩在厚實的地毯上面。腳下輕松了很多,一顆心也逐漸松弛下來。
Advertisement
就這樣吧,安安穩穩地生活下去。
此刻,云巔之南咖啡廳。
“姚,什麼時候回來的?”紀殊彥手執銀匙輕輕攪著瓷杯中的咖啡,聲音混著咖啡廳舒緩的輕音樂傳出,平和清朗。
“一周以前。”那個名姚的艷人目盈盈著紀殊彥,笑意有些寥落。“八年了,我幾乎每一天,都在幻想跟你重逢的形。”
姚的睫羽低垂下來,著面前升騰起熱氣的咖啡,無奈而傷地說:“殊彥,這八年來,你一直都沒有再談。可是,我沒想到,我終于回國了,可聽到的關于你的第一個消息,竟然是你為未婚妻買下了全城的婚紗店。”
紀殊彥沉默片刻,還是開口道:“父親為我定下的婚事。只要我接這場聯姻,就不會被迫繼承家業。”
姚聞言眼前一亮,面喜,眼睛牢牢地盯住紀殊彥,說道:“我知道,你不會對別的人心的。殊彥,你知道嗎,我看到你跟那個人站在臺上的時候,我真想……”
“姚。”紀殊彥蹙眉,阻止了姚的話。“別說這些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姚聞言,眼中驀然充盈起晶瑩的淚意,勉強保持著微笑,搖頭說道:“我做不到。這八年來,我沒有一天忘記你。殊彥,即便紀家不愿意接我,我也沒有辦法收回自己的。難道你真的能把我們的過去一筆勾銷嗎?我不信,我不信啊。”
紀殊彥的嘆息聲細微若無,他有一瞬的失神。而后目落在自己無名指的婚戒上,想起了蘇夏的面孔。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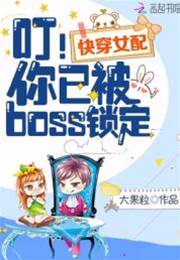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395 章

玄學大佬替嫁后,病弱老公開掛了
最近南星的氣運忽然變差,連喝口涼水都塞牙縫。 她隨手起卦,算出世上竟然有一位與她“氣運相連”之人。 對方正是被仇家下了死咒的傅家三少爺,傅輕宴! 傅輕宴的準未婚妻見他命不久矣,一哭二鬧三上吊的要取消婚約。 南·接盤俠·星主動站出來:“別吵了,我替你嫁給傅三少。” 后來,南星成了傅家的三少夫人,揚言可以用玄術救他的命。 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她嫁入豪門的借口,等著看她守活寡。 然而等著等著,傅輕宴的病好了。 得罪過傅輕宴的人倒是死的死,瘋的瘋,沒一個有好下場。 吃瓜群眾傻眼了。 原來小丫頭真有兩把刷子? 一夜間,風向逆轉。 大家擠破頭都想買南星一張符。 傅輕宴把門一關,“抱歉,我夫人很忙。”
104.3萬字8 11920 -
完結48 章

閃婚老公竟是豪門總裁
唐若雨為了不連累舅舅,答應去和舅媽介紹的對象相親。怎料陰差陽錯地認錯了人,她竟和總裁領證了!唐若雨得知認錯人後,搬去了神秘老公的家等他......而總裁一直以為跟自己領證的就是唐家女兒。後來跟唐若雨接觸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竟喜歡上了她。他能否得知自己結婚證上的就是他喜歡的人呢?
8.8萬字8 49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