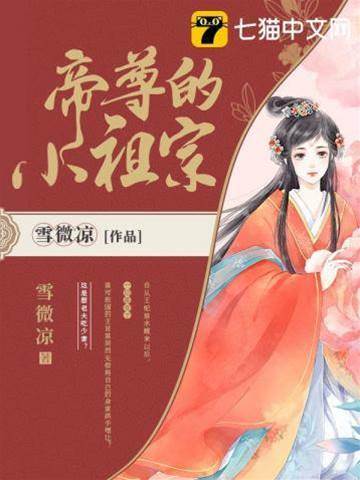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奸臣,勞駕死透一點》 第50章 路橫州回京了?
的嗓子還沒恢復,聲音一片低啞,并未驚門外的人,卻不知道這一轉,便將正片后背暴在來人眼前,腰上那藕帶子顯得格外刺眼。
來人沒有如所愿出去,而是順手關上房門。
“怎麼,不想招供,改變策略對本使人計了?”
才不是!
蘇問春氣惱,咬牙扭頭怒瞪來人,對上蘇時寒似笑非笑的眸。
剛下朝,這人穿著一墨朝服雙手環靠在門上,明明該是清冷肅然的,這會兒不知怎地看著像個登徒子。
“不要過來!”蘇問春警告,抓起里擋在口,腦子一加了一句:“我上有跳蚤!”
是存心惡心蘇時寒的,雖然明知道他對自己沒有誼,也不會被這殘破的吸引,還是下意識的用這樣的方式保護自己。
然而沒料到的是,蘇時寒在聽到這句話以后皺了皺眉頭,竟徑直走到面前。
“你……”
蘇問春心臟劇烈的鼓跳起來,那張紙條就在口,肚兜下面是空的,稍有不慎紙條就會掉下來,萬一被發現……
正胡思想著,男人溫潤的指腹在尾椎骨,輕輕挲了一下,得厲害,心尖都在發,蘇問春頓時失了聲。
“服穿上,一會兒我會讓人送驅蚊蟲的熏香來。”
蘇時寒沉沉的命令,蘇問春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他剛剛的是腰上被蟲子咬出來的疙瘩。
Advertisement
緒大起大落,蘇問春不由得松了口氣,抖開里穿上,正低頭系帶子,蘇時寒忽的傾湊近。
蘇問春本能的后仰避開,卻從他黑幽的眸底看見自己驚慌不安的臉。
“你在怕什麼?”
他問,目灼然,帶著一不易察覺的審視。
他已至廷尉,警覺比尋常人要高出很多,蘇問春又幾乎是他看著長大的,的一些小作自然逃不過他的法眼。
“沒有。”
蘇問春否認,垂眸避開蘇時寒的目,抓著服帶子的手不由握拳。
“沒有?”
蘇時寒不信,還要繼續追問,蘇問春再度掀眸,眼眶卻已發紅,噙滿水霧:“蘇大人,我不像你那麼無,可以把十年的相和承諾都忘得干干凈凈,可不可以請你離我遠一點,不要一直來撥我的心?”
這話說出來,七分真心三分假意。
眼睛一眨,滾燙的淚珠立刻從眼角落,蘇問春這才發現,原來要演戲騙一個人,也不是想象中那麼難。
“……”
蘇時寒怔住,似乎沒想到蘇問春會說出這樣的話,過了一會兒才不自在的命令:“不許哭!”
“又不是什麼得到的東西,說不要就能把它丟開嗎?我現在這麼難過,怎麼做得到不哭?”
蘇問春了戲,不僅沒止住哭,還哭得越來越起勁。
蘇時寒一張臉繃著僵得厲害,盯了蘇問春看了半晌冷聲道:“這招對我不管用,自己穿好服冷靜一下,等你想起什麼有用的線索我再來看你。”說完轉大步離開,但那背影怎麼看都有點落荒而逃的意味。
Advertisement
等人走遠,確定外面沒了聲音,蘇問春立刻抬手去眼淚,背轉借著穿服的姿勢把藏在口的紙條拿出來。
‘三日后,子時一刻,等我。’
這幾個字寫得張牙舞爪,狗爬似的,分明是路橫州的筆跡。
蘇問春驚愕的瞪大眼睛,隨即將紙條一團塞進里,艱難的嚼碎咽下,腦子比之前更了。
路大哥不是在淮山嗎?怎麼突然回京了?他回京了淮山那七萬將士怎麼辦?路伯伯和哥哥呢?他們為什麼沒有阻止他?
這個笨蛋難道不知道沒有令擅自回京是要滿門抄斬的死罪嗎?
無數疑問涌腦海,蘇問春只覺得腦袋撐得幾乎要炸掉,手腳也一片冰涼。
強迫自己穿上服,系腰帶的時候猛地頓住。
路伯伯這些年一直鎮守邊關鮮回京,路橫州更是五歲就進了軍營,就算他真的擅自回了京,哪兒來的本事神不知鬼不覺的把消息傳進來?
從這幾次和林語歡的接來看,蘇問春并不覺得會是真心幫自己的人,這張紙條是沒有發現,還是發現了故意不說?
事關重要,蘇問春沒有太多時間思考,隨意系好腰帶便沖到門邊拍門:“來人,我要見蘇大人。”
“閉!瞎嚷嚷什麼!”
守衛不客氣的踹了一腳門,蘇時寒才剛從這里離開,哪能說見就見?當蘇大人是什麼?
“我突然想起很重要的線索,要告訴蘇大人,你們若是不去通報,過了時候我就不會再說了!”
蘇問春冷聲威脅,心里的不安一點點擴大,若是路橫州真的回京,被抓到以后肯定只有死路一條,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
門外靜默了一會兒,兩人到底還是擔不起這個責任,憤然道:“你別給老子耍花招,要是這次你敢騙我白跑一趟,到時有你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747 章

鬼面梟王:爆寵天才小萌妃
一道圣旨,家族算計,甜萌的她遇上高冷的他,成了他的小王妃,人人都道,西軒國英王丑顏駭人,冷血殘暴,笑她誤入虎口,性命堪危,她卻笑世人一葉障目,愚昧無知,丑顏實則傾城,冷血實則柔情,她只想將他藏起來,不讓人偷窺。 “大冰塊,摘下面具給本王妃瞧瞧!”她撐著下巴口水直流。 “想看?”某人勾唇邪魅道,“那就先付點定金……” 這是甜萌女與腹黑男一路打敵殺怪順帶談情說愛的絕寵搞笑熱血的故事。
316.4萬字8.09 152892 -
完結1039 章
絕寵世子妃
前世被親人欺騙,愛人背叛,她葬身火海,挫骨揚灰。浴火重生,她是無情的虐渣機器。庶妹設計陷害?我先讓你自食惡果!渣男想欺騙感情?我先毀你前程!姨娘想扶正?那我先扶別人上位!父親偏心不公?我自己就是公平!她懲惡徒,撕白蓮,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重活一世,她兇名在外,卻被腹黑狠辣的小侯爺纏上:娘子放心依靠,我為你遮風擋雨。她滿眼問號:? ? ?男人:娘子瞧誰礙眼?為夫替你滅了便是!
196.7萬字7.75 191914 -
完結107 章

蕓蕓卿州
魂穿貧家傻媳婦,家徒四壁,極品後娘貪婪無恥,合謀外人謀她性命。幸而丈夫還算順眼,將就將就還能湊合。懷揣異寶空間,陸清蕓經商致富,養萌娃。鬥極品,治奸商,掙出一片富園寶地。
17萬字8 27651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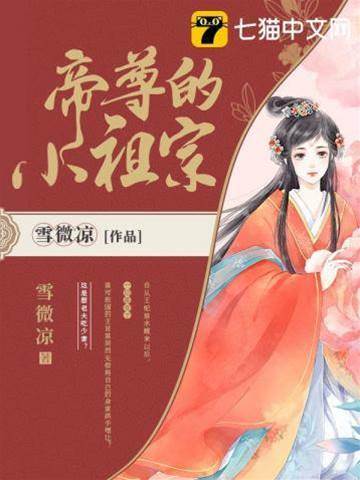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