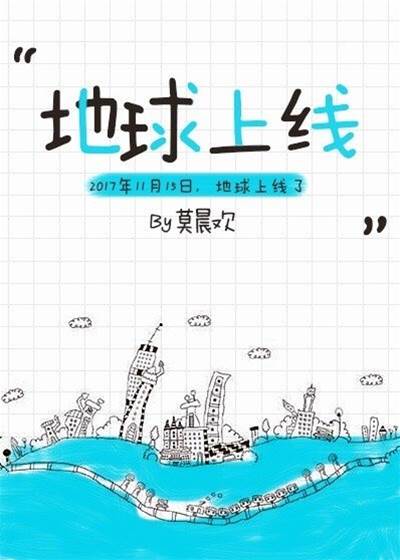《斯年如你》1
出獄年上理智冷漠攻:池崢 多年苦守主倒追傲:斯屹
兄弟年上 滿紙荒唐
年上真兄弟,床上真骨科
文案:
逾越了理超過自然/瞞住了上帝讓你到邊
即使你到你變碎片/仍有我接應你落地上天
(1)
池崢一腳踏出監獄的大門,姿態很放松,像是白日里無聊,到鄰居家串了個門。落在上,不怎麼曬,溫溫的,很舒服。他瞇了瞇眼睛,臉上什麼表都沒有,沒有茫然,沒有無錯,也沒有喜悅。
跟所有從這里走出去的人都不太一樣。
帶了他六年的獄警給了他一煙,語氣淡淡的:“出去了,就別再回來,好好的,要重新做人,知道嗎?”
二十六歲,還年輕,可以重新開始。
池崢笑了笑,那笑容很淺,只是在臉上浮了一下,轉瞬消散。眼睛里墨沉沉,辨不清到底是個什麼緒。
他將煙點上,站在路邊慢慢著,快燃到底時,小路盡頭飄起些許沙塵,一輛舊吉普飛似的開過來。
池崢將煙碾碎,扔進垃圾桶,吉普拉著長長的剎車線停在他面前,四散的灰塵弄臟了他腳上的舊踝靴和上的工裝。
駕駛室的車門砰地一聲推開,跳下一個鐵塔似的黑壯男人,一個熊抱將池崢摟在懷里,激得幾乎哽咽。
池崢讓他抱得呼吸一,屈起指節在那人背上敲了敲,道:“斯屹呢?”
聲音有點沉,聽起來不大痛快。
鐵塔張齊,池崢的發小,高一米九三,重將近兩百,站起來遮天蔽日,卻是一臉的小心翼翼,囁嚅了半天,也沒找到一個像樣的理由。
從小相依為命的親兄弟,什麼理由能讓他連自己親哥出獄都不面?
Advertisement
張齊腦部構造簡單,一腸子通到底,他想不出來。
池崢的表在笑,眼睛里卻沒有毫笑意,他跺了跺腳,自語似的嘀咕了一句:“行,隨我,有脾氣。”
監獄在城南,張齊開車載著池崢一路飛向城北,那里有個放馬營的地方,據說,古時候是飼養戰馬的地方。放馬營是城中村,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才都有,池崢和斯屹就是在那長大的。
六年前,池崢二十歲,是放馬營的老大。
如今六年過去,很多東西都不一樣了。
吉普車一路飛馳,在一棟灰撲撲的兩層小樓前停了下來,樓上七八糟地掛著不牌匾,容理發,養生修腳,看著就不像什麼正經生意。
池崢深吸一口氣,他悉這里的每一條街道,就像悉自己的骨骼。
張齊站在門口替他挑門簾,一邊挑,一邊勸:“池哥,團圓的日子,大家都開心的,別發火,有話好說。”
池崢沒說話,推開張齊邁步朝屋子里走。
里面采不太好,白日里也亮著燈,明晃晃的。
池崢一腳踏進去,撲面一濃重的煙酒味,還有長時間不洗澡的臭味。四五張麻將臺支在那里,稀里嘩啦的洗牌聲響一片。最左邊那張臺子格外熱鬧,里三層外三層,圍著十好幾個,一邊看一邊好,不知道的還以為藏了個馬戲團。
斯屹也在那里,他個子高,皮白,長得還帥,在放馬營這種到灰蒙蒙的地方,不需要干什麼,只是站著就足夠顯眼。
池崢停下腳步,他看見斯屹腳底下踩著凳子面,一手夾煙一手盅,了瘋似的搖得嘩嘩響,然后嘭的一聲扣在桌面上,吼著:“趕猜!是爺們痛快點!別對不起下那東西!”
Advertisement
斯屹用盡全力氣在吼,脖子上的青筋都起來了,一腦門的汗,臉上泅著病態的紅。不等他看清自己手里到底是幾個幾,一道格外沉郁的聲音越過嘈雜狠狠撞過來——
“七個二!”
斯屹覺得耳一震,像是被什麼東西燙了一下。
接著一道頎長的聲音逆走過來,停在他邊,抄手奪過對家的盅,也不晃,直接在桌面上落定。那人看都不看,直接:“七個二。”
斯屹作一頓,目沿著那只握著盅的手一路上爬,腰線勁瘦,肩膀略寬,下頜和的弧度太過凌厲,出些許兇狠的味道,眼睛是純粹的黑,著暗夜似的。
六年沒見,他還是那副樣子啊。
斯屹有一瞬間的怔愣,好像時從沒有變過,那家伙還是浪在放馬營里的子,他還是小小的一個,拉著那家伙的角跟在他后,滿眼崇拜地他哥哥。
哥哥,哥哥……
心跳在劇痛中一團。
斯屹咬后槽牙,佯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笑著:“出來了啊,還是老樣子麼,都沒怎麼變。”
不咸不淡的語氣,聽著都讓人窩火。
被奪了盅的那位是新來的,不認識池崢,啪的一拍桌子,正要站起來,張齊扇似的手掌在他肩上,生生把人了下去,威脅著:“消停呆著,不然,你走不出去這扇門。”
周圍響起竊竊私語的聲音——
“我曹!他怎麼出來了!不是說無期嗎?”
“犯了什麼罪啊要判無期?”
“殺人!自個親爹!夠狠吧!”
“牛!是個茬子!”
池崢和斯屹倆兄弟在是非窩里長大,早就聽慣了閑言碎語,也不惱,只是互相看著,像是要把對方心里那點東西剖出來,弄個明白。
Advertisement
池崢眸沉沉,重復了一遍:“七個二,開不開?”
斯屹突然覺得心火上涌,他恨了池崢這副喜怒無形于的樣子,就好像這世界上沒什麼人值得他放在心里。
他著嗓子喊了聲開,掀開盅砸在桌面上,池崢一同抬手,亮出底牌。
兩個人各拿五枚子,一共十枚,七個二,一個六兩個三,池崢猜得比作弊都準。
斯屹笑了一下,他早就知道自己會輸,在放馬營,沒人能贏得了池崢。
他還在捆紙尿的時候,池崢就開始搖子了,他的他的服他的糖,都是池崢弄回來的。
是池崢一手將他帶大,給了他天堂,也給了他地獄。
斯屹笑得很大聲,眼睛里似乎有淚,芒一閃而過,他說了句愿賭服輸,飛快地了上和子,只穿著站在那里。形流暢,略瘦,很勻稱,皮雪白,一看便知小時候被人養得很好,連道印子都沒留下。
他挑釁似的看著池崢:“我們剛剛說好的,輸的人服。”
被奪了子的那位對家一臉懵——啥時候有的這規定?我怎麼不知道?
池崢臉上什麼表都沒有,也不生氣,他將盅擱回到桌面上,轉朝外走,再沒看斯屹一眼。
張齊嘆了口氣,下外套扔在斯屹上,低聲道:“當齊哥求你,別再折騰你哥了,還嫌他過得不夠苦?”
說完這話,也跟在池崢后出去了。
斯屹站在原地,臉上笑容漸漸淡下去,只剩死灰般的寂滅。
有人湊過來占便宜,在斯屹屁上了一把,笑著:“還玩嗎?哥哥跟你玩,輸了服。”
斯屹眼神一厲,抄起凳子對著那人腦袋便砸,嘭的一聲,直接見了。
Advertisement
“不怕死的盡管來,”斯屹重新穿上子,赤著上站在那里,眼神和語氣都是冷的:“我哥剛從大獄里出來,我不介意也進去蹲幾年。”
(2)
張齊從麻將室出來時,池崢已經上了車,在副駕駛上閉目養神。
張齊擰了下車鑰匙,道:“池哥,你別生氣,小屹的格你也是知道的。自從你……之后,他一個人在外面,過得不容易……”
池崢擺擺手,閉著眼睛道:“我明白。”
他怎麼會不明白,是他一手將斯屹養大,也是他一手將斯屹寵壞,那個孩子格里的所有東西,暴戾、倔強、沖、叛逆、,都是他給的。
兩個人明明只差了三歲,卻對彼此有著莫大的影響。
清難斷家務事,再是鐵子,也不好多說什麼,張齊發車子,道:“先回我那吧,洗個澡,睡一覺,一切又都是新的了。”
池崢依舊閉著眼睛,像是累極了,眉心皺痕明顯,道:“不去你那,去老屋。”
老屋在放馬營的小胡同里,一間平房,一個小院。院子里有葡萄架,夏天時,新綠的葉子覆滿視線,格外漂亮。葡萄架下原本有個小秋千,是他給斯屹準備的,糯米團子似的小東西坐在上面晃啊晃,笑聲清脆。
池崢站在院子里,看著早已枯死的葡萄藤,有一瞬間的心堵,像是通的脈都凍住了,運行不暢,幾乎無法呼吸。
張齊站在一旁尷尬地著手,道:“池哥,對不起啊,我實在不會打理這些長葉子的東西,一不留神,就……”
池崢沒說話,從口袋里拿出煙盒,張齊立即掏出打火機,遞了上去。
灰白的煙霧升騰起來,模糊了那張英俊的臉。
除了種的活都死了,其他倒是沒什麼變化,屋子里的家擺設和以前一樣,關公像前還有未燃盡的三支香。
這應該是張齊的功勞,自池崢獄,邊的人走的走,散的散,只有張齊堅持每星期來打掃一次,直到今天。
一切好像從未變過,可是時間已經向前走了六年,斯屹都已經二十三歲了。
池崢里里外外轉了一圈,總覺得了點什麼,看到桌子上那幾個空了的相框才想起來,照片,他和斯屹的合照,都不見了。
張齊不會他的東西,應該是斯屹搬出去時帶走的。
小崽子將自己的東西收得干干凈凈,連點念想都不給他留。
還真是有脾氣的。
張齊走進來,說以前的兄弟知道池哥出來了,想一塊聚一聚,給您接風。
池崢坐在臥室的木板床上,磕了磕煙灰,瞇著眼睛道:“不必了,讓大家好好過日子,以前那些荒唐事,都忘了吧。蹲大獄的滋味有多難,我知道。”
話雖這麼說,可風不能不接,張齊在枯死的葡萄藤旁支起了桌子,兩箱啤酒,幾碟小菜,他說,沒有外人,我陪池哥喝兩杯。
池崢笑著跟他了杯子。
張齊說大家也都還行,小六結婚了,大華在工地上,苦是苦點,但錢賺得足。冬瓜喝多酒跟人茬架,一刀捅在脈上,沒救過來。小甲魚跟著幾個南方人走了,沒了消息。還有大桶、胖子、苦力仔、小地圖、湯圓……
都是曾經跟著池崢在放馬營里耀武揚威的小兄弟,現在想想,池崢甚至記不清他們的樣子了。
“你呢?”池崢又點上一支煙,吐出一個不怎麼圓的煙圈,道:“說了半天別人,怎麼沒介紹介紹自己?”
“我也還,”張齊不好意思地抓抓頭發:“攢了點錢,弄了個小飯館,生意不好不壞,能糊口。”說到這,張齊突然頓了一下,然后語氣一轉,頗為驕傲:“咱們這些人里,要說出息,還是小屹。他現在是老師,在城西的那個重點中學,教化工,厲害吧!”
池崢想了想,兜頭給了張齊一掌:“那化學!文盲!”
張齊一拍大:“對!化學,初中化學!工作一年了,不錯的。沒想到吧,那個誰都管不服的小東西,為人師表了。”
這一點池崢的確沒想到,自從判刑獄,他單方面切斷了跟外界的一切聯系,不見故人,不理舊事。六年里,他不收斯屹匯的錢,不要他寄的東西,甚至不肯見他一面。
他把心呵護的寶貝獨自扔在外面,由他生,由他滅,由他慘烈破碎之后,再蘸著一點點把自己拼起來,重新找到活下去的勇氣。
這過程一定很苦,所以,怨不得斯屹恨他。
兩個大老爺們,一口煙一口酒,用往事下飯,到最后都醉了,互相攙扶著摔倒在臥室的木板床上。池崢強忍著頭疼找到兩條毯子,自己蓋一條,另一條扔在張齊上。
張鐵塔呼嚕打得山響,絮絮地說著夢話:“池哥能回來,真的太好了!太好了!不管我有什麼,都分你一半!我的命是池哥救的,我有什麼,都給你!”
這是他最忠心的兄弟,也是唯一一個肯留在他邊的人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6 章

碎玉投珠
古玩行沒一個缺心眼兒的。攻受都臭講究。 退一步兄友弟恭,進一步情有獨鐘,再進一步走完一生。白頭偕老he 丁漢白:“這行最喜歡的就是玉,料分三六九等,人也分龍鳳螻蟻,我既名漢白,自是配得起良玉。” 紀慎語:“師哥一向都是拔尖兒的。” 丁漢白:“既然拔尖兒,那配不配做你的良人?”(攻就是比較沒羞沒臊,非逼著人家跟他好) 張狂事兒多大少爺·特級鑒寶專家攻,雙商高長得美·古董制造達人受
25.7萬字8 3518 -
完結213 章
走紅后豪門大佬成了我粉頭
江放因體質弱從小被家人送去寺廟當和尚,後來被老和尚趕回家,碰巧練習生出道的弟弟正準備參加一檔綜藝,需要邀請一位親人參加。 看在錢的面子上江放答應參加,誰知弟弟自帶黑熱搜體質,兄弟倆參加綜藝的消息剛在網上傳開。 黑子:怎麼什麼低學歷的人都能上綜藝,碰瓷王江齊這次嫌一人不夠,打算帶著他哥組個碰瓷組合嗎? 江?人送外號高冷校草學神?放:? ? ? ? 你們怕是不知道什麼叫碰瓷,傷殘那種。 節目開拍後 “臥槽,怎麼沒人說江齊的哥哥長這樣,這顏值我能舔壞無數隻手機!” “是我眼花了?為什麼我會在一檔綜藝上看到我們學校的校草。” “說江放低學歷的人認真的嗎,燕大學神了解一下?” # 只想撈一筆項目啟動資金沒想過混娛樂圈的江放爆火後,收穫了土豪粉一枚和後台黑粉連發的99條恐嚇私信。 土豪程肆:等他再發一條。 江放:? 土豪程肆:湊個整送他上路。 江放:順便撒點紙錢,走得安詳一點 。 # 程肆的妹妹為某明星花百萬砸銷量驚動了程家,程父程母擔心女兒被騙,讓程肆幫忙照看。 程肆在監督的過程中,學會了簽到打榜,學會了給愛豆應援,學會了花錢砸銷量,還學會了監守自盜。 妹妹:說好監督我的呢,你怎麼就成了我愛豆的粉頭? 表面高冷學神實則壞心眼受X表面霸道總裁實則老幹部攻
48.7萬字8.18 9407 -
完結118 章
穿成炮灰O後他們獻上了膝蓋
樓停意外地穿到一本狗血ABO文中,他的身份竟然是十八線廢材Omega。 作為一個稱職的炮灰,他的人設既可憐又醜陋,是個被全網群嘲的黑料藝人。 當合約在身,被迫參加了一檔成名已久的藝人重回舞臺選秀的綜藝節目時,觀眾怒了。 “醜拒。” “這節目不行了,廢物來湊數?” “他出來我就跳進度!” 樓停出場,一身修身西裝,肩寬臀窄,完美比例一出場就讓剛剛還在摩拳擦掌準備彈幕刷屏的黑子愣住了。 黑子:“這人誰?長得還挺好看???” 節目導師:“這身衣服有點眼熟。” 表演時,樓停當場乾脆利落地來了一個高亢婉轉的海豚音,隨後音樂驟變,節奏分明的rap伴著爆點十足的舞蹈,在一眾目瞪口呆中樓停穩穩而立,像是矜貴的公子,樓停謙虛地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樓停。” 導師:“??剛剛那是什麼?” 黑子:“世界有點迷幻,我要讓我媽媽帶我走去家門去看看。” 總決賽後,樓停溫暖一笑:“這次來是因為合約在身,我其實不太適合唱歌的。” 觀眾:“您放下手中第一獎杯再說這話可能有點信服力。” 等到一年後,樓停站在百樹獎的頒獎舞臺上,舉著影帝獎杯,身負幾場票房過十幾億的電影男主後。 黑轉粉的粉絲們才明白:“這他媽……還真的不是唱
41.8萬字8.18 9114 -
完結104 章

我死對頭終于破產了
令紀燃不爽多年的死對頭破產了。 狐朋狗友問紀燃打算怎麼辦。 紀燃冷笑一聲——這他媽還用問?! 那當然是趁機折磨他、羞辱他、踐踏他啦 于是紀燃大手一揮,把卡往死對頭身上一丟,張狂地說要‘資助’他。 結果第二天,他一臉懵逼的坐在床頭,感受著身上的陣陣酸疼,想起昨晚受過的苦,挨過的‘打’和流過的淚…… 日你媽。 虧你媽大發了。 狗逼秦滿,我殺了你。 —— 【秦滿攻x紀燃受】 排雷:文盲式寫文、邏輯已進土立碑、放飛自我、無文筆可言、攻受都不是善茬。
30.3萬字8 2761 -
完結2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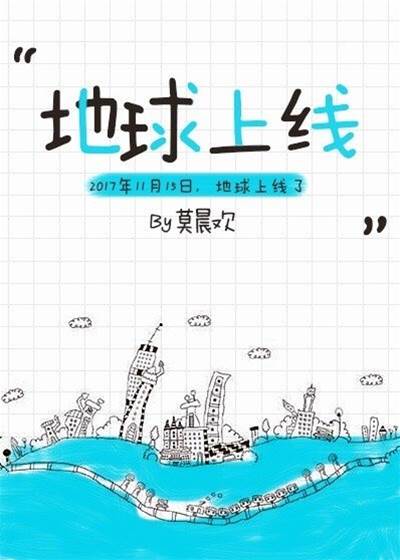
地球上線
半年前,數以萬計的黑色虛影巨塔出現在全球各地,懸浮城市上空。 化學家、物理學家、宗教……全部束手無策。 半年後,人們習慣了,不再關注它。 唐陌有一天看見一隻飛蟲撞上了虛影黑塔,沒有穿透過去。 第二天,一道兒童般清脆的聲音向全人類發佈公告—— 『叮咚!2017年11月15日,地球上線了。』 傅聞奪×唐陌 黑塔三大鐵律—— ①一切解釋歸黑塔所有。 ②6點-18點是遊戲時間。 ③請所有玩家努力攻塔。 內容標籤:強強 無限流 爽文 升級流
116.3萬字8 2267 -
完結75 章

別想掰彎我
顧寄青作為清大數學系公認的美人,一副純欲神顏勾得全校女生五迷三道,結果剛開學就坦言自己是個Gay,據說還掰彎了好幾個直男。周辭白作為清大建筑系公認的系草,憑借一米九的身高和爆棚的荷爾蒙氣息被全校女生譽為行走的大總攻,卻從開學第一天就恐同得明…
32萬字8 82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