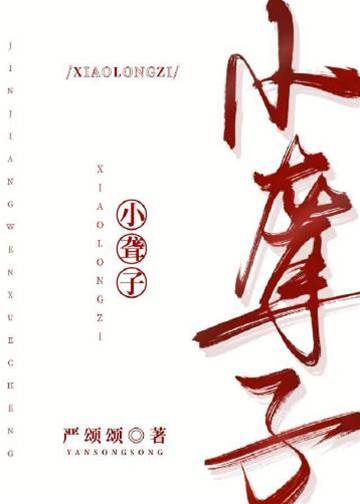《天界公務員》 248|太子殿下的奇妙記憶漂流 3
謝憐卻是肅然起敬,眼睛都亮了,抓著他紅的擺道:“不不不,三郎哥哥,你好生厲害!居然能練出這樣有自己靈識的法!”
那刀方才被三郎打了一掌,委委屈屈地皺起了眼,聽謝憐誇獎,眼珠又骨碌碌轉得意起來,想往他那邊蹭。三郎十分冷酷地又是一掌。
這下它可不幹了,“咚”的一下子倒在地上,滾來滾去滾來滾去,仿佛被大人打了就在地上打滾放聲大哭的小孩子。謝憐耳朵旁邊簡直像是能聽到它哇哇嚎啕的聲音似的,看得有點心疼,忙起道:“等等三郎!算了,你不要打它了,我想它只是一時頑皮,想來示好,不必如此苛責它啊。”
但一出水,這才記起自己水下的是赤|的,臉莫名又紅了,尷尬地沉了回去。三郎卻早已十分自然地轉過了,出去了。
謝憐匆匆爬出水換了新服,覺的料子十分細,終於不再被磨得難了,心中更為謝。出了屋子,來到會客的雅廳,三郎已在上座等著了。
不知如何他教訓那刀了,現在它老老實實佩在三郎腰間,不時,竟十分冷峻肅殺,全然想象不出方才那副在地上打滾撒賴的模樣。見謝憐來了,三郎笑道:“起來了?昨夜睡得可還好?”
Advertisement
謝憐如實答道:“前半夜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做夢……後半夜倒是睡得好了。”
三郎道:“是太累了吧。”
二人隨口說了幾句,小小切磋了幾回,這一天也差不多過去了。大概在那位花城有空之前,他們都會如此相下去。
可是,晚間,謝憐一個人躺在床上,又做了那令人燥|熱難安的夢。
他在夢裡被翻來覆去弄得忍無可忍,猛地醒來,又是一大汗淋漓,氣憤無奈,只得起出去,想走幾圈冷靜一下,卻忽然聽到遠遠另一側屋子裡傳出聲音。
那是三郎的主人間。屋子隔音甚佳,那聲音極小,但謝憐五絕靈,捕捉到了。他屏息凝神,無聲無息來到那屋子外。
過門,向裡去,只見三郎坐在屋中座上,手執一管紫毫,似乎在寫字,神是與面對他時截然不同的冷肅,一旁還有一個黑鬼面人,正彎著腰,低聲匯報。
不知怎麼回事,那鬼面人的存在實在很低,一不小心可能就沒注意到了。謝憐正要細聽,那人卻已經報完了,他只約聽到零散語句,“那怪作多時”“想來是接到祈願前去理,出了意外”“這是剛探查到的方位”什麼的。
Advertisement
他正慢慢梳理,只聽三郎道:“我現在要陪他,不開。明晚之前給我把那怪拿下送來。”
那鬼面人低聲道:“是。您要留它一口氣嗎?”
三郎擱了筆,看了一眼自己寫的東西,似乎不太滿意,一團,扔了,這才慢條斯理地道:“多留幾口,讓它把東西吐出來,再慢慢把它的狗頭碾碎。”
他說這話時的神和語氣,都令人不寒而栗。但謝憐居然並不怎麼反警惕。那鬼面人應聲便要離去,謝憐立即閃藏了回去。
回到自己的屋子,謝憐更睡不著了,來來去去走了幾回,心道:“三郎究竟是什麼人?他說的是什麼怪?”
聽起來,仿佛有什麼重要的東西被一個作為禍多時的怪吞了,三郎頗生氣。但因為眼下要陪他,才不開去打爛那怪的頭。
想到這裡,謝憐便覺十分不好意思。這位三郎,待他當真是赤誠至極。
忽然,他腦中靈一閃:他為什麼要這樣幹坐著?反正暫時見不到花城,他也一直想為三郎這位好哥哥做點什麼,不如,就去幫他把那怪擒來?
說走就走。謝憐打定主意,當即留書一封,寫下三郎哥哥莫要擔心,憐去去便回雲雲,飛一躍,悄無聲息地出了這座華麗的宅子。
猜你喜歡
-
完結73 章

月下安途
謝鐸和沈安途是Z市人盡皆知的死對頭,今天你搶我的地,明天我截你的生意,不是在干架,就是在干架的路上。 突然有一天,沈安途的私人飛機失事,謝鐸派人趁亂把他從現場帶走,囚禁了起來。沈安途醒后因傷失憶,為了試探真假,謝鐸自稱是沈安途的男友。 所有人都以為謝鐸在以此羞辱沈安途,只有謝鐸自己知道,沈安途這個“死對頭”其實是他求而不得多年的白月光。 謝鐸(強勢深情攻)X沈安途/沈凜(狡猾誘惑受) (雙向暗戀,雙向白月光,謊言里的真愛)
16.4萬字8 9514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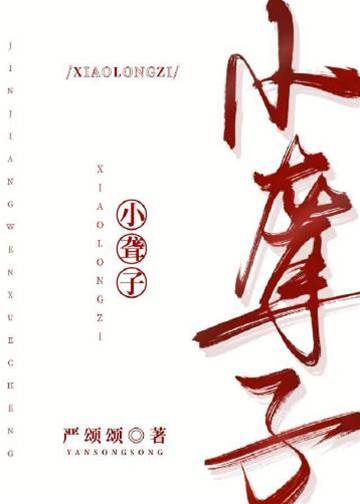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82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