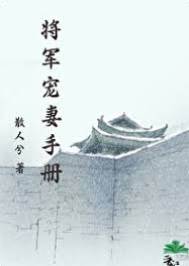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代妾》 131 虛情假意
131虛假意
章季軒並沒有把秋錦瑟說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話放在心上。
他已經有好些日子不曾來的初曉堂了。
他原本只是在園子裡散步,忽然聽見初曉堂這邊傳來琴聲,他這纔不由自主的走到了這裡。
屋的擺設和從前並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是多了一把古箏而已。
炭盆裡的炭已經漸漸熄滅,只剩下黑的一堆,再也發不出一點熱度。
屋裡和外面幾乎是一樣,除了能夠阻隔住那些凜冽的風之外,依然是冷的很,他見秋錦瑟爲了寒上依舊披著一件厚厚的披風,看的他不由得有些心酸。若不是因爲他,恐怕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份罪吧。
那日都怪他,若不是他輕信上晨月的話說和別的男子有染,他又豈會說出那樣難聽的話,害的在府裡備非議。
事後他讓江濤去查探並沒有發現秋錦瑟有什麼異常,他這才後悔莫及。
他原本思量著想到初曉堂來跟秋錦瑟道歉的,可是他站在垂花門外猶豫了很久。
想讓他說話,只怕他開不了口。
正在躊躇著要不要進去的時候,忽聞初曉堂傳來琴聲,他這纔不由自主的進了秋錦瑟的房間。
他聽到秋錦瑟說的那番話,心裡是五味雜陳,爲了能夠和重歸於好,他只得無視說的那番要趕走他的話。
一梅花的清香徐徐傳來,順著香氣尋去,他這才發覺原本放著瓷的地方不知何時被擺放了好幾瓶梅花。
他不在的這段時間裡,房間裡新添置的這些東西皆是他不曾知道的。
他暗自笑了笑,以前便跟他說過喜歡古箏和梅花的。
當初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秋錦瑟曾不止一次對他說,“梅花雖說獨樹一幟。可若是冬日裡沒有梅,這樣的冬日只會愈加的寒冷,若是能有梅花,人在到冷颼颼的地方纔能到一的溫暖,這樣看來梅花倒也不是一無是。更何況若是將含苞待放的梅花摘下曬乾,若是誰有咳疾,咽不適的話和蜂和臘一起熬湯水服下還能治療頑疾”。
Advertisement
當初聽到秋錦瑟這番說辭的時候,他擡手輕輕的颳了一下秀俏的鼻子。
搖晃著頭,輕巧的避開他的手指,嘟著說道:“不許刮我的鼻子。若是被你刮壞了你可賠不起。”
章季軒想到秋錦瑟仰著臉說話的樣子,忍不住笑了笑。
秋錦瑟見章季軒無端發笑,生氣的說道:“你若是想來看我笑話的。現在看也看了,笑也笑了,你若是沒什麼事的話,你還是請回吧,我這初曉堂陋不是你這富家子弟該來的地方。”
章季軒對秋錦瑟的話視而不聽。
他只是饒有興致的看著剛瓶的紅梅。自顧自的說道:“無意苦爭春,一任羣芳妒。 零落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唸完這幾句,章季軒拿起有紅梅的瓶子,放在鼻翼下聞了聞。
聽完章季軒唸的這首詞,啐了一口。纔不要和別的人爭一個男人,他以爲自己是誰,更何況他又如何當得起讓爭的對象。
秋錦瑟見章季軒竟然拿起心的紅梅。連忙起,作勢要奪。
著急的說道:“章季軒,既然你冤枉我,討厭我,本該見了我和我的東西躲得遠遠的。又何必去,難道你是想同上晨月一樣見不得我好。但凡是我看上眼的東西都要親手毀了嗎?章季軒你這樣做實在是太過分了。
章季軒被這一舉弄的是措手不及,他哪裡是想毀了的花瓶,他不過是看紅梅開的好,想仔細的看看而已,到底在想些什麼,怎會把他想的如此不堪。
他見秋錦瑟手去奪他手中的花瓶,他連忙將花瓶護在懷裡,若是這花瓶真的被他失手給摔碎了,只怕不但沒和解反而又添了新矛盾。這花瓶是護住了,只是秋錦瑟這一撲上來,腳下不穩,眼看著就倒下去,章季軒又連忙騰出一個手去扶。
Advertisement
秋錦瑟扭著子,姿勢難看的趴在章季軒的懷裡。
章季軒上半全部倚靠在架子上,左手託著倒在他懷裡的秋錦瑟,然而秋錦瑟上披著的披風領上茸茸的狐貍卻把他的鼻子弄的的,讓他有好幾次都有想打噴嚏的衝。
他極力的扭過臉,試圖躲避撲進鼻子的狐貍,可是試了幾次都不行。
他來回的扭,趴在他上的秋錦瑟也隨著搖搖晃晃,眼見著兩個人都有摔倒的危險。
章季軒握住秋錦瑟腰肢的左手有些痠痛漸漸的也沒了力氣,他只得將全的力量全部寄託在倚靠的那個架子上。
秋錦瑟饒是扭到了腳,只見疼的吸了一口氣,而後又緩緩的吐氣,就在這一呼一吸間,從秋錦瑟口中呼出的溫熱氣流全部噴在章季軒的臉上。
他聞著上傳來的那淡淡的清香,一時間竟有些想要把擁在懷裡,再也不放開的衝。
他努力控制住躁不安的緒,試圖將自己的心平靜下來,可是這樣的姿勢卻讓他更加難的。
爲了控制好平衡,他只得放下右手裡拿著的那隻有紅梅的花瓶。
他試圖將花瓶放在架在上,還未來得及將花瓶放穩,子失去平衡,隨著子不住的傾斜,只聽見“呼啦”一聲。架子倒在地上,架子上放著的那幾瓶梅花無一例外的全部碎了一地。
秋錦瑟狼狽的倒在地上,只覺得下的,並不覺得疼。
見紅梅碎落在地上,慌忙爬了過去,試圖把那些掉到地上的梅花給撿起來。
這些梅花可是頂著那些在邊指手畫腳人的流言蜚語好不容易摘回來的,如今竟被章季軒摔壞,難怪如此心疼。
Advertisement
憤恨的想:章季軒就是一個災星,只要他在的地方。一準要倒黴。
不過剛爬了兩步,只覺得下傳來一聲“哎吆”。
慌忙低下頭去看,這一看的臉騰地一下紅到了脖子。
只見的兩隻手正按在章季軒的前,膝蓋頂在他的小肚子上,而則正準備從他的頭頂爬過去。
剛纔他的那聲“哎吆”顯然是因爲剛纔無意間到了他最敏的地方。
這麼近的距離看著章季軒雖說並不是第一次,可是這樣的距離還是足夠讓臉紅,的心裡猶如小兔子一樣到竄,無法安靜下來。不知道是因爲在他的上爬著還是因爲別的什麼原因,總之好想此時能夠有個地好讓鑽進去。
著眼前這個自己又恨又的男子,秋錦瑟第一次覺得是那樣的不知所措。
不知道自己的雙手該放在哪裡。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才能掩蓋住那慌的心。
章季軒的目此刻正盯著的兩隆起的地方看個不停。
還未等秋錦瑟驚呼,就聽見一陣噼噼啪啪的腳步聲傳了進來。
“這是怎麼了?”息墨的聲音響徹在耳邊,不僅把正在愣神的秋錦瑟給驚醒了過來同時也驚醒了秋錦瑟下的章季軒。
息墨看見秋錦瑟和章季軒兩人竟然是這個姿勢。臉一紅,連忙扭過去,背對著他們,然後快速的朝門外移去。
秋錦瑟見息墨如此,知道是誤會他們了。連忙搖搖晃晃的起。
待秋錦瑟起後,章季軒一個鯉魚打神如常的站了起來。
秋錦瑟忍著腳踝傳來的疼痛,試圖一點一點的朝椅子移去。
章季軒見秋錦瑟如此艱難的樣子,連忙上前攙扶住。
Advertisement
這時候外間傳出息墨低聲說話的聲音:“你先別進去,爺和二正在裡面。”
春花的聲音跟著也傳了出來:“這還沒到晚上,們……不過這樣也好。這就說明爺還是在意二的。”
秋錦瑟聽到春花和息墨的這番對話,能覺到此刻的臉頰一定是滾燙滾燙的。
臉上猶如燒了一整宿的炭盆,火熱熱的。
章季軒聽到這話只想發笑。見秋錦瑟紅著一張臉,只得拼命忍住。
見章季軒要扶自己,再加上剛纔春花說的那番話,使勁一甩將章季軒握住的手給甩開。
章季軒被秋錦瑟這樣甩開後,並不急著上前去扶。他只是站在的後,看著一瘸一拐的朝著榻走去。
看著如此難的樣子。章季軒更加的心疼。
他大聲的說道:“來人。”
息墨聽到章季軒的說話聲,低著頭走了進來。
章季軒說道:“你去我房裡把跌打藥拿來。”
他見息墨還杵在那,不耐煩的說道:“你還杵在這幹什麼,還不快去。”
息墨立即退了下去,看來是誤會他們了,看著章季軒心急火燎的樣子,看來二又添新傷了。
秋錦瑟見章季軒站在自己面前,又看了看已經有些紅腫的腳踝,沒好氣的說道:“我讓你走,你沒聽到是不是,每次都是因爲你,若不是你我何苦會變現在這幅樣子。”
章季軒張了張口沒敢接話。
秋錦瑟瞥了他一眼,又繼續說道:“你走,你走啊,我不想再看到你。”
說到最後,有些歇斯底里。
章季軒依然站在那裡不爲所,見秋錦瑟不說話了,他才接過話茬道:“既然這事是因我而起,我會給你一個代。”
說完這話章季軒頭也不回的走了。
聽著章季軒離去的腳步聲,秋錦瑟頓時淚如雨下,不知道是不是因爲腳踝痛的緣故,纔會覺得委屈所以纔想哭。
猜你喜歡
-
完結2476 章
一世傾城:冷宮棄妃
那一夜,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澀,成為冷宮深處的悲傷漣漪...... 那一天,她跪在他的腳下苦苦哀求,她什麼都不要,只想要出宮,做個平凡女人... 幾個風神俊秀的天家皇子,一個心如止水的卑微宮女... 當他們遇上她,是一場金風玉露的相逢,還是一闕山河動蕩的哀歌......
600.3萬字7.94 728802 -
完結1946 章

農女雙雙的種田悠閒生活
老穆家人人欺負的傻子穆雙雙,突然有一天變了個樣!人不傻了,被人欺負也懂得還手了,潑在她身上的臟水,一點點的被還了回去。曾經有名的傻女人,突然變靈光了,變好看了,變有錢了,身邊還多了個人人羨慕的好相公,從此過上了悠閒自在的好日子!
341萬字8 118440 -
完結1858 章
王妃她不講武德
寧孤舟把劍架在棠妙心的脖子上:“你除了偷懷本王的崽,還有什麼事瞞著本王?”她拿出一大堆令牌:“玄門、鬼醫門、黑虎寨、聽風樓……隻有這些了!”話落,鄰國玉璽從她身上掉了下來,他:“……”她眼淚汪汪:“這些都是老東西們逼我繼承的!”眾大佬:“你再裝!”
326.8萬字8.18 263247 -
完結266 章

邪帝溺寵妖孽冷妻
前塵愛錯人,家族滅,自爆亡。今世重來,她要擦亮眼睛,右手靈氣,左手煉藥,她一路升級打怪,斗皇室,滅渣男,扶家族,憑借自己的能力傲世與這個以實力為尊的世界。 而她的身邊,也多了一個真正可以與她攜手并肩的妖孽男人,傾世風華只為她一人展顏,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只為護她亂世周全。
78.1萬字8 3278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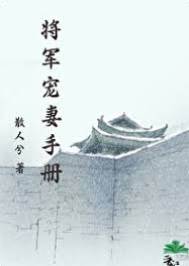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