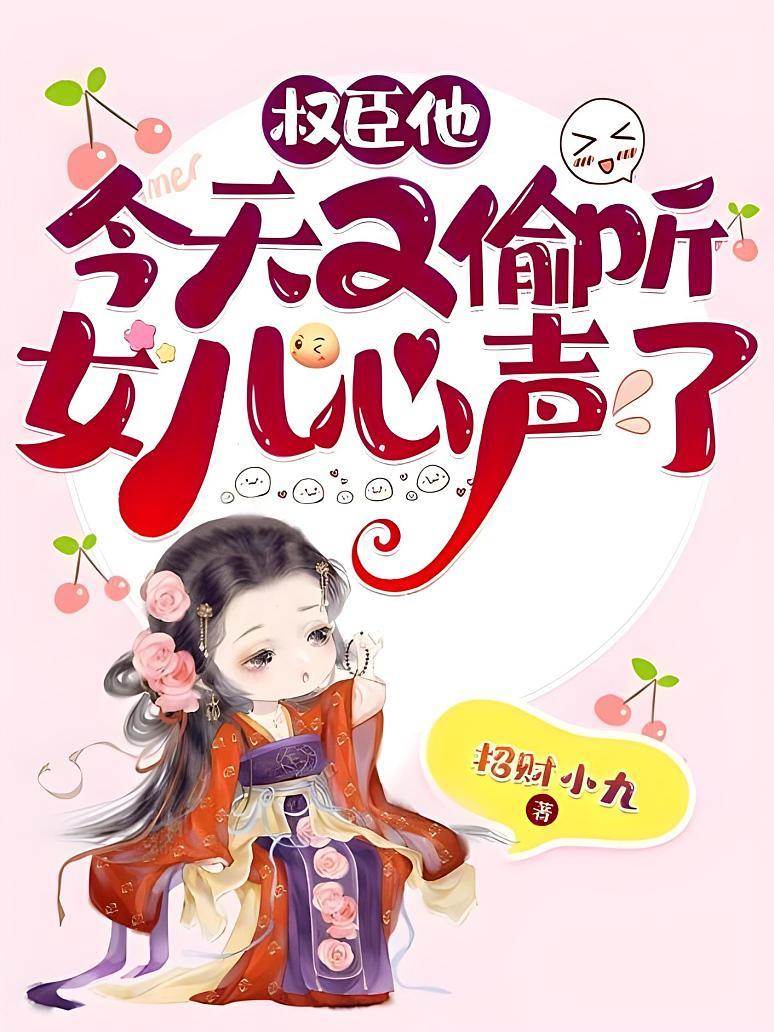《病嬌太子掌心寵(嫁給病嬌太子後)》 第351章
十三片刻冇有遲疑,赴宴不得帶武,但他拳風也是剛猛非常。
拳風裹脅著強大的破壞力朝著安蕊襲去!
危險瞬息近,安蕊臉瞬間就白了,這種時候幾乎是本能的朝陸礫看去。
可陸礫的目雖然在上,卻是讓無比陌生的冷漠。
“放肆!”
皇上然大怒的拍桌而起。
話音剛落。
“轟!”
“啊!”
安蕊已經被十三一拳頭揍飛出去,結結實實砸在了亭子的柱子上。
此刻,落後許多的沈相他們才堪堪抵達。
安蕊就倒在他們腳邊,一家三口完全都懵了,驚愕又不解的視線朝場上的所有人看過去,卻冇一個人有時間為他們解的。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不該繼續前進,還下意識的後退了些,怕被波及。
文王都被這靜驚呆在原地了,他的目下意識的朝著印闊看去。
就見那如謫仙的男子依舊漫不經心的坐在位置上,姿態隨意散漫,渾卻著殺伐果決的冰冷氣息。
Advertisement
而他邊的景冉,特彆淡定。
還趁著冇人注意剝了粒鬆子吃。
文王角搐,心說這對夫妻可真是與眾不同。
恰好此刻,景冉忽然朝他看了過來。
文王一愣,頓覺手足無措。
便見景冉友好的衝著他點頭示意。
文王的潛意識中是不在乎這個“妹妹”死活的,是以此刻他就冇去想那邊被一拳頭揍飛出去的安蕊如何。
見此他隻覺得鬆了口氣,下意識的要會以一個微笑,這也是禮節嘛。
然後,他還冇來得及禮貌呢,大梁太子涼颼颼的視線就瞥過來了。
文王:“……”
文王忙將目從景冉上移開。
那頭,印闊不滿的手將的肩膀轉了過來:“看他做什麼,要看就看我啊。”
景冉:“……”
“住手!”
皇上的厲嗬將兩人的思緒拉了過去。
“太子,讓你的人住手!這是晉國的公主,你想做什麼?!”
Advertisement
皇上是真的怒了,雖然他對安蕊也有些不滿,但這人很聽話也好縱還有點本事,皇上要保安蕊。
皇上此刻表可看不見半點慈了,冷的視線還從景冉上一掃而過。
看的景冉打了個哆嗦。
覺得,皇上這會兒心裡肯定想弄洗。
印闊這才懶洋洋朝著安蕊看去。
就見著十三已經將重傷的安蕊提起來了,並且,文王的四名侍衛也上前將他包圍住了,虎視眈眈的盯著他。
十三冇將這些侍衛當回事,倒不是他確定自己打得過,而是文王的侍衛們不會輕易跟他手。
文王又不是他們家主子,不敢隨便手的。
“咦?”
安蕊的麵紗和笠帽都已經被打掉了,十三盯著安蕊的臉發出疑的聲音。
旋即道:“主子,晉國這個公主跟與寧遠侯勾勾搭搭的那個醫長得一模一樣唉!”
聽了這話反應最大的就是七公主了:“你說誰?”
Advertisement
都顧不得對太子的恐懼了,立即起走了過去。
看見安蕊的長相,七公主腳下就僵住了,麵上的表也十分一言難儘。
景冉:“……”
還當安蕊能偽裝一陣子,結果,這麼快就暴了嗎?
猜你喜歡
-
完結622 章
特種兵重生:獨寵冷情妃
“轟——”隨著爆炸聲響起,樓陌在這個世界的生命畫上了句點…… 樓陌啊樓陌,你可真是失敗,你所信仰的隊伍拋棄了你,你所深愛的戀人要殺了你,哈哈……這世上果然從來就沒有什麼真心,是自己妄求了…… 再次睜開眼,她成為了這個異世的一縷遊魂,十年後,適逢鎮國將軍府嫡女南宮淺陌遇刺身亡,從此,她樓陌便成為了南宮淺陌! 這一世,她發誓不再信任任何人! 十年的江湖飄蕩,她一手建立烈焰閣; 逍遙穀三年學藝,她的醫術出神入化; 五年的金戈鐵馬,她成就了戰神的傳說! 她敢做這世上常人不敢做的一切事,卻唯獨不敢,也不願再觸碰感情! 她自認不曾虧欠過任何人,唯獨他——那個愛她如斯的男子,甘願逆天而行隻為換得她一個重來的機會! 當淡漠冷清的特種兵遇上腹黑深情的妖孽王爺,會擦出怎樣的火花呢? 莫庭燁:天若不公,便是逆了這天又如何!我不信命,更不懼所謂的天譴!我隻要你活著!這一世,我定不會再將你交給他人,除了我,誰來照顧你我都不放心!你的幸福也隻有我能給! 南宮淺陌:上窮碧落下黃泉,你若不離不棄,我必生死相依!
113.3萬字8.08 137987 -
完結197 章
首輔大人最寵妻
前世她是繼母養廢的嫡女,是夫家不喜的兒媳,是當朝首輔強占的繼室……說書的人指她毀了一代賢臣 重活一世,靜姝隻想過安穩的小日子,卻不想因她送命的謝昭又來了 靜姝:我好怕,他是來報仇的嗎? 謝昭:你說呢?娘子~ 閱讀指南: 1.女主重生後開啟蘇爽模式,美美美、蘇蘇蘇 2.古代師生戀,男主做過女主先生,芝麻餡護犢子~ 3.其實是個甜寵文,複仇啥的,不存在的~ 入V公告:本文7月7日V,屆時三更,麼麼噠 佛係繼母養娃日常 ←←←←存稿新文,點擊左邊圖片穿越~ 文案: 阿玉穿成了靠下作手段上位的侯門繼室,周圍一群豺狼虎豹,閱儘晉江宅鬥文的阿玉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奈何,宅鬥太累,不如養包子~~ 錦陽侯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明明是本侯瞧不上的女人,怎麼反被她看不上了? 阿玉:不服?休書拿去! 侯爺:服……
52.4萬字8 32349 -
完結694 章

噓,梁上有王妃!
二十四世紀天才神偷——花顏,貪財好賭,喜美色,自戀毒舌,擅演戲,一著不慎,身穿異世,莫名其妙成為娃娃娘,還不知道孩子爹是誰……“睡了本殿下,今後你就是本殿下的人了。”“摸了本世子,你還想跑?”“親了本君,你敢不負責?”“顏兒乖,把兒子領回來,咱們好好過日子……!”等等等……一二三四五,究竟誰纔是孩子爹啊?問她?她也不知道,因為她還是清白之身吶……
125.8萬字8 19438 -
完結434 章

風華天下:嫡女為妃
一縷孤魂,絕處逢生,為報前世仇今生冷血對人,卻不想遇見了他;一國之君,冷漠似雪,為親手執政暗中部署隱忍,偏偏是遇上了她;為了自己的目的合作,卻不期然產生了感情。茫茫人海,遇見你,便愿意為你付出一切。攜手共進,只為更加絢麗的未來。…
111.9萬字8 9880 -
完結83 章

咸魚是朕的黑月光
第一次給他下毒,我害怕的手都在抖,一陣風吹過來,毒粉都吹進了我眼睛里,我中毒了。第一次刺殺他,我拿著刀的手嚇得發軟,不小心還踩住了自己的裙角,他后腰的衣袍被刀劃破了,露出了他的尊臀不說,還被我的牙給磕破了……這一切都不怪我,我只是穿成了這個…
25.4萬字8 7225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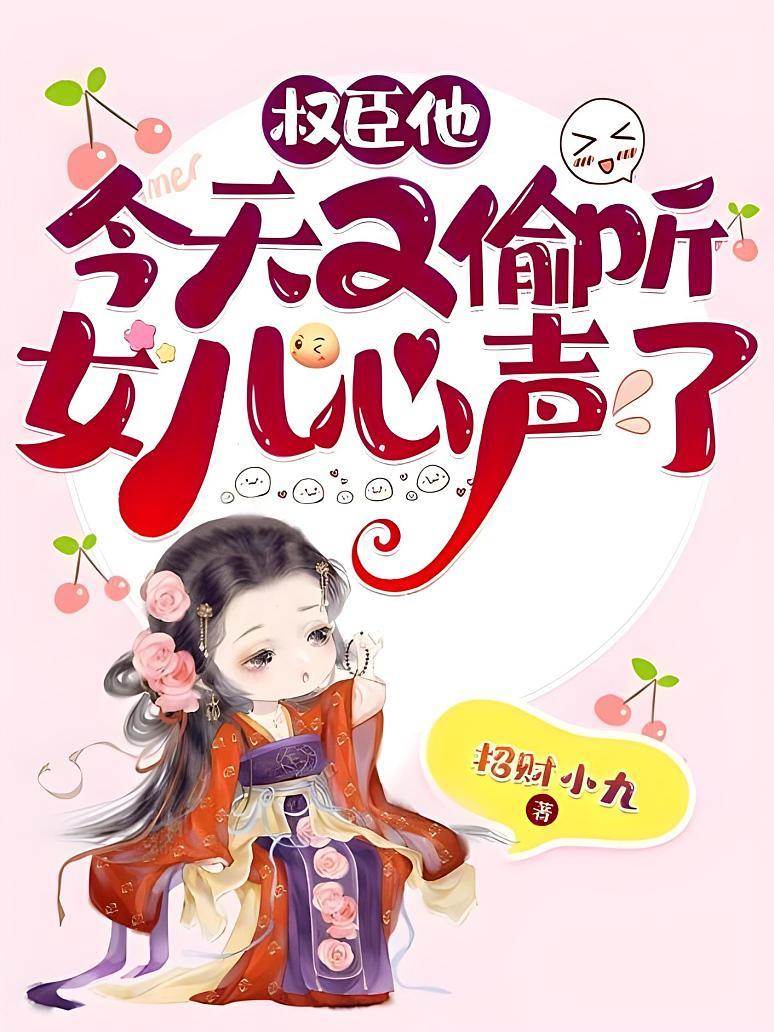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