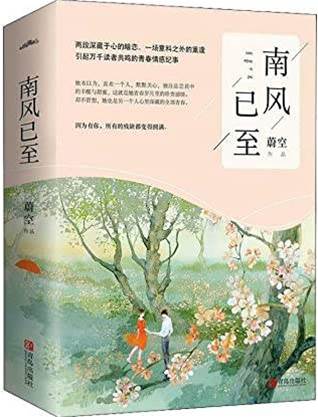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江醫生的心頭寶》 第61章沒錢,就一條命
很顯然,徐況傑他是醉了,說話的時候舌頭都是卷著的。
「不過他不煙不賭博倒是真的,嗬嗬……這貨除了對他老婆,就是自帶絕緣,其他人想導電也不行。」
「唉……」
一聽這話,賀淮更沮喪了。
「忠心耿耿。這麼完的男人,我更沒辦法挖牆腳了。」
「完個屁,他怕狗!」
徐況傑將馬天尼和瑪格麗特兩種尾酒混合著往肚子裡灌,已經上頭了。
「什麼??」
「我說他怕狗,小時候被狗咬過一次,留下影了,看見狗就跟孫子似的。」
「真的啊?他那麼怕狗啊?」
「切,你表哥我有騙過你的時候嗎?!」
然後賀淮便將這番話告訴了言念。
卻發現言念在愣神,不知道心裏麵在想什麼。
「言小念,你怎麼了?」
他出一隻手,在言念麵前打了個響指。
思緒回歸,言念搖搖頭,說沒什麼。
在的印象中,有個人似乎也怕狗,不過那人可不是江北淵。
再說了,那人又跟不,打從上初二之後,再也沒見過了!
Advertisement
「哎對了,趕明兒我要回孃家,花店你照看著!」
賀淮說好。
「那今晚上你又不回去了?」
言念點頭。
哼了一聲,勢必要將今天的flag進行到底。
「當然不回去!誰回去誰孫子!」
……
第二天一大早,言念就回孃家去了。
已經好久沒回家過了,沒想原來的家,已經被馬雪燕改造得不樣子。
門前擺著兩大棵發財樹,客廳還掛著竹子,一濃濃的迷信風。
言念將外套一,丟沙發上,嗅到一香味,環顧一圈,發現客廳的正前方竟然還擺著佛像,著香爐。
「至於嗎。」
你自己不努力,難道佛就能讓你賺錢啦?
馬雪燕聽到靜,從房間出來,一屁坐在言念旁邊,手,「錢呢?」
「沒有!」
「那要你帶回來的人呢?!」
言念:「分了!」
馬雪燕一陣氣惱,對著言唸的後背,一掌打下來。
「賺不到錢又找不到老公,我養你還有什麼用!」
「沒用,你乾脆殺了我吧。」
Advertisement
「死丫頭!今天又吃槍葯了是吧!」
說著,一掌又要揮過來。
這次被言念在半中央攔截住了。
「打打打,打了這麼多年,你沒完了是吧?」
「長本事了?我把你吃喝拉撒拉扯到現在,你眼裡有沒有我這個媽?」
「等一下,把我拉扯到大的,是我爸,我爸死了,你還是我媽嗎?!」
言念最後那句話幾乎是用吼的。
像是憋了很久、很久,怨氣和怒火一併跟著發出來。
說完鬆了手,別開臉。
眼圈紅紅的,抿著角,抿了好幾抿。
馬雪燕冷嗤一聲,「不管怎樣,就算你爸死了,我還是把你供到上學供到現在了,你現在參加工作了,就應該孝順我,回報我!」
「我說了,現在沒錢,就這一條命,你願意要你就拿去!」
說著乾脆轉過去,背對著馬雪燕。
今天回來,就是找罪的!
早知道,還不如沒有孃家!
「死丫頭!我看你回來存心氣我!」
正好言唸的後背對著,馬雪燕抬手一掌又要落下來。
Advertisement
這次,扣住手腕的,就不是言唸了。
「啊——」
一陣撕心裂肺的慘聲劃破長空。
言念愣了一秒,轉過來,對上的是卻是江北淵的臉。
他修長乾淨的骨節掐了馬雪燕的胳膊,周的戾氣在往外延。
從言念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江北淵額角凸起的青筋,那雙素來淡如寒煙的眸,此刻覆上了一層霾。
言念從未在江北淵的眼底看到過這種神。
猩紅,鋒銳,又深沉。
那種……近乎於想要毀滅一個人的狠。
「你再敢打一下試試?」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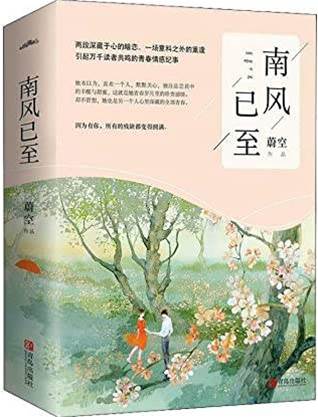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1080 章
婚亂流年
結婚紀念日,妻子晚歸,李澤發現了妻子身上的異常,種種證據表明,妻子可能已經……
191.5萬字8 10953 -
完結336 章
錯嫁后她成了第一財閥夫人
被渣爹后媽威脅,沈安安替姐姐嫁給了殘廢大佬——傅晉深。全城都等著看她鬧笑話,她卻一手爛牌打出王炸!不僅治好傅晉深,還替傅家拿下百億合作,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財閥夫人
64.8萬字8 53558 -
連載405 章

流產當天,我離婚了
“恭喜你,懷孕了!”她懷孕的當天,丈夫卻陪著另一個女人產檢。 暗戀十年,婚后兩年,宋辭以為滿腔深情,終會換來祁宴禮愛她。 然而當她躺在血泊里,聽著電話中傳來的丈夫和白月光的溫情交耳,才發現一切都只是自我感動。 這一次,她失望徹底,決心離婚。 可在她轉身后,男人卻將她抵在門板上,“祁太太,我沒簽字,你休想離開我!” 宋辭輕笑,“婚后分居兩年視同放棄夫妻關系,祁先生,我單身,請自重,遲來的深情比草賤。” 男人跪在她面前,紅了眼,“是我賤,宋辭,再嫁我一次。”
49.2萬字8.18 1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