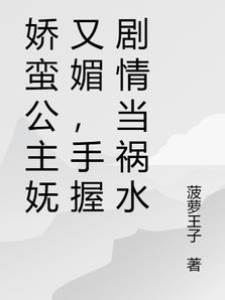《懷嬌》 第31章 第31章
夏日里的流螢不算稀奇,只是魏玠鮮在夜里外出,更不必說見過大片螢火浮的場景。
他不是年的稚子,更不是兒家,眼前的幽幽點并未給他帶來任何。
唯一不同的是薛鸝,時而冷漠尖銳,時而又溫馴脆弱,這樣變幻莫測的一個人,總是人捉不,分辨不出究竟有幾分真心,是否那些哄人的話不過是口腹劍的手段。
黑暗之中,魏玠能到有只溫熱的手在他的指尖,見他沒有排斥的意思,于是變本加厲地勾住他的一手指晃了晃,帶著點試探與討好的作,像是從前那只小鳥為討食輕啄他的手背。
“表哥總是獨自一人,守著這些古舊乏味的規矩,便不會到寂寞嗎?”薛鸝盡量讓自己的語氣中幾分幽怨,多幾分對魏玠的憐惜。
“守規矩不是什麼壞事,可以避免許多煩擾。”魏玠的話里沒有欺瞞的意思,他的確是如此想的。他做事向來盡全盡,并不為功名利祿,不過是他可以做到,而做到這些,能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煩擾,他從未因此而到寂寞。而薛鸝的靠近,他也并不厭煩。
得到魏玠的回答,薛鸝略有些意外。還以為魏玠必定要扯上許多圣人言,以此反駁所說的乏味古舊,捍衛魏氏引以為傲的禮法教條。
“人活在世,倘若只為規矩二字而活,的確能免去許多煩擾,卻也會為此錯過許多有趣之事不是嗎?”既然是人便會有瑕疵,世上沒有人能從生到死都一塵不染。“表哥在旁人眼中是楷模,是魏氏育出的無暇玉,在鸝娘心中卻只是護著我待我好的表哥。表哥不愿壞了規矩,必定心中沒有值得為此去做的人或事。可于我而言,表哥的品是好是壞,是否還是世人稱頌的佳公子,我都不在意。”
Advertisement
薛鸝握他微涼的手掌,細的手指如一尾小蛇溜進他的指,與他親地糾纏在一起。
“鸝娘對表哥的心意永不會變……世上人總講命數,興許你便是我的命數,我正是為你而來這世上走一遭呢。”薛鸝的聲音很輕,似一縷甜膩的香煙,緩慢地勾纏著他的心緒。
世上當真有獨屬他一人,無論世事變遷,都始終如一地陪在他邊的人嗎?
魏玠不想承認,可他的確為薛鸝的話容了。
為他而來,生死不論,眼里心里也只會有他。這樣的話從薛鸝口中說出,實在人不得不懷疑。
魏玠發出一聲輕而短促的低笑,薛鸝恍惚還以為是的錯覺,下一刻便到他微涼的掌心在了的頸側,而后正如一只麗的瓷般輕輕挲著的頸項。
“當真值得嗎?”他若是想要得到薛鸝,自然有千百種法子,可這麼做無疑是打破了他平衡安穩的現狀,為掀起一些不必要的風波。
薛鸝值得他這麼做嗎?
顯然薛鸝是誤會了魏玠話里的意思,以為這話是在問,立刻上魏玠的手,哄似地說:“世上沒有比表哥更值得的人了,只要表哥我憐我,即便要做妾做奴婢,我都心甘愿。”
薛鸝為了顯得自己是一片真心,不惜說出自己最為唾棄的話來,好讓魏玠莫要當是為了攀附他的權勢,想做魏氏日后的家主夫人。雖慕權勢,卻也有自知之明,倘若敢覬覦這個位子,必定有魏氏的人下手死,何必要給自己自找麻煩。
“死了也甘愿?”他笑道。
“那是自然。”薛鸝答得毫不猶豫。
流螢已經逐漸飛散開了,屋里僅剩幾點微弱的螢火。
Advertisement
他收回手,轉朝門口走去,很快便有人進屋將燭火一一點亮。
離黑暗后,薛鸝面對著眼含笑意的魏玠,想到自己方才說出的話,竟也忍不住生出點窘來。原來高高在上的魏玠,也會因為這種直白的甜言語而高興嗎?
他應當遇見過不狂蜂浪蝶的示,為何還能為的話容?
薛鸝心中疑卻又略有欣喜,畢竟撥的不是旁人,是被世人追捧奉若神明的魏玠,日后想起來也算一份值得夸耀的功績不是嗎?
“天已晚,你先宿在側房,明日一早命人送你回桃綺院,想必你也想好如何向姚夫人代了。”
“表哥早些歇息,那我先走了。”
“去吧。”
時辰確實不早了,薛鸝隨著梁晏在野地里胡鬧,一直到此刻才覺得疲倦,匆匆洗漱過后幾乎是倒頭便睡了過去。
玉衡居的侍們都是千挑萬選才能在此侍奉,因此即便是面對薛鸝,也沒有如其余人一般出輕鄙來。難得來了一次玉衡居,睡得實在不算舒坦,夜里因為蚊蟲叮咬幾次醒來,一直折騰到天微亮,索起洗漱,想要回到桃綺院應付姚靈慧。
薛鸝梳妝打扮過后,天仍是蒙蒙亮,便放輕步子去到了魏玠的臥房。
守在門外的侍衛是晉青,看到是后,低聲音提醒道:“公子尚在歇息。”
薛鸝心中猶豫了一番,正轉想走,門卻忽地被拉開了。
魏玠的穿得整齊,只有發略顯隨意地披散著。見到薛鸝眼下憔悴的青黑,說道:“夫子今日不會去書院,你回去后好好歇息。”
說完后,他略一頷首,又道:“先進來,我有東西給你。”
薛鸝還以為是魏玠后悔了,想要將那一箱子珠翠送與,誰知卻跟著魏玠走到了書案前。他出幾本書給,說道:“你上次看過的書上我做了批注,若有何不懂可以來問我。”
Advertisement
魏玠捕捉到了薛鸝眼中一閃而過的失,提醒:“鸝娘,你不能什麼都想要。”
一瞬間,薛鸝還以為他意有所指,臉稍稍一變,迅速出一抹笑,說道:“表哥說的話我聽不明白。”
魏玠臉上分明是溫和的笑意,一雙黑沉沉的眼卻無比漠然,看得薛鸝心臟猛地一。
正在此時,忽然響起一陣急促而雜的腳步聲,隨之而來的是人滿是憤怒的嘶啞喊。
“魏玠!是你告訴了魏恒,是你說出去的!你以為,你們父子算得上什麼好東西!”
薛鸝被這厲鬼似的喊聲嚇得一抖,聽到聲音近了,立刻慌地想要找個地方躲一躲,忙拍了拍魏玠,焦急道:“我要躲起來,不能旁人看見了。”
魏玠仍淡然地像個神像,從容不迫地走到藏書的大箱子前,示意薛鸝躲進去。
里面塞著各式書卷,有不是難得的善本,薛鸝這樣不好學的人踩上去都覺得心疼,躲進去后只敢小心翼翼地蜷著,好在剩余的空間夠多,不至于讓太難。
過微小的隙,薛鸝看到那個癲狂如野的人跌跌撞撞地闖,不等去撕咬魏玠,便被晉青輕而易舉地在了地上。
魏玠后退了一步,和氣道:“見過姑母。”
薛鸝心中一驚,不得不佩服起魏玠的鎮定,他的姑母像個瘋子似地沖進來辱罵他,他竟不憤怒不驚愕,還面不改地與行禮,當真還算是個人嗎?
魏翎的頭發已經散了,眼眶通紅,大口地著氣,字字泣地控訴:“我待你不薄,將你視如己出,為何要害我!為何!”
話未說完,另一人氣勢洶洶,闊步走房中。
“見過父親。”
Advertisement
薛鸝一聽魏恒也來了,不由慶幸自己及時躲了起來,若不然以魏恒的手段,得知蓄意勾引魏玠,便是不死也再難留在。
魏恒面凝重地掃了魏玠一眼,問道:“方才說了什麼?”
“姑母不過是訓斥了兒子幾句,并未說其他的話。”
“將魏翎足在寧安觀,沒有我下令,任何人不得去見。”魏恒睨了魏翎一眼,侍者們立刻上前要帶走。
魏翎如同被捉住的魚一般瘋狂扭掙扎,眼神宛如索命的惡鬼,死死地盯著魏恒,怒罵道:“魏恒!你這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是你毀了我!”
“憑什麼只準你齷齪,不許我有私,你養的好孽種!你這個禽跟……”
侍者們想去捂住的,卻不知這樣瘦弱的人被急了,一時間也難以被制住。魏恒一腳將魏翎踢倒,這一腳使了十足的力氣,讓的話戛然而止,半晌沒有過氣來,而后魏恒又快又狠地打了一耳。
打完之后連他的手都在火辣辣的疼,魏翎的臉上幾乎是立刻便浮現了幾指印,連話也說不出了。薛鸝躲在箱子里都覺得心驚跳,窺見魏恒的眼神后,更是屏住呼吸不敢有任何作。
魏恒的目比起魏翎的絕與憎惡,更像是一個冷漠暴戾的活閻羅,與從前溫善寬厚的模樣判若兩人,仿佛要立刻舉刀殺了自己的親妹妹一般。
魏翎似乎也終于到了一懼意,抖著沒有再發出聲音。
直到魏翎被捂著拖出去,魏恒才回過,冷漠道:“你姑母瘋了,此事已了,日后不必再管。”
自始至終,魏玠都泰然自若地站在一旁,期間只是微皺了下眉。他既不為魏翎字字泣似的哭喊容,也沒有因為魏恒暴戾的舉有一一毫驚愕。他站在那冷眼旁觀,似乎這些人不是他的父親與姑母,只是一些吵鬧著讓人心煩的蚊蟲。
守規矩不是壞事,的確可以避免許多煩擾,可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為會有私。
薛鸝看到他的反應后,心臟跳得極快,一下比一下重。
忽然覺得,魏氏眾人并非想的那般高潔。眼前正直儒雅的魏玠,似乎也有著說不出的古怪。
魏恒很快便離去了,魏玠朝著箱子走來,薛鸝卻下意識有些恐懼他的靠近。他揭開箱子,神自若道:“無事了,出來吧。”
仿佛方才的一切都未曾發生過。
薛鸝手腳有些發,不明白魏翎所說的齷齪與禽是怎麼回事,又為何要辱罵魏玠是孽種。魏恒正直仁厚,名遠揚,這些難聽的字眼如何能與他扯上干系?魏翎當真是瘋了不,可喪夫后回到魏府便深居簡出,好端端怎得就瘋了。
薛鸝越想越,甚至不敢去看魏玠的眼神。
“姑母病了。”魏玠簡短地解釋道。
薛鸝干地應了一句:“養一陣便會無事。”
還是無法將魏恒對魏翎手的那一幕從腦海中掃去,好一會兒了,才啞著嗓子問:“為何……為何要來尋你?”
魏玠面坦然,沒有毫瞞的意思。“姑母與魏弛私通,我稟告了父親。”
輕飄飄的一句話如同一聲驚雷,薛鸝呆愣在原地,驚愕到瞪大雙眼,又問了一遍:“與魏弛?”
私通并非大事,何況魏翎已經喪夫,不過是說出去有失面,卻也不至于到如此責罰。薛鸝本來對魏翎的遭遇頗為同,畢竟子要尋求快活,本并不是罪過,可……魏弛與不是姑侄嗎?
緩了緩,問道:“那……魏弛呢?”
“魏弛聲稱是姑母引在先,諒在他年紀尚輕,又是二房的嫡子,如今已關去祠堂罰。”魏玠說完后,又淡淡道:“意圖害你命的人正是姑母。”
“這……這與我何干?”薛鸝更疑了。
“當日在祠堂□□的男,正是姑母與魏弛。”魏玠平靜的語氣,說出的話卻足以讓薛鸝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聽魏翎的話,待魏玠應當極好,不曾想魏玠會不顧魏氏的面,不顧與往日的姑侄分,將與魏弛私通的事告知了魏恒,因此才會發瘋似地找上他。
好一會兒了,薛鸝才皺眉問他:“表哥既然想要避免煩擾之事?為何還要說出去。”
魏玠溫聲道:“你既屬于我,便不能由旁人害你命。”
猜你喜歡
-
完結4031 章

世子妃她是朵黑心蓮
前世,南宮玥是被自己坑死的。她出生名門,身份尊貴,得當世神醫傾囊相授,一身醫術冠絕天下。她傾盡一切,助他從一介皇子登上帝位,換來的卻是一旨滿門抄斬!她被囚冷宮,隱忍籌謀,最終親手覆滅了他的天下。一朝大仇得報,她含笑而終,卻未想,再睜眼,卻回到了九歲那一年。嫡女重生,這一世,她絕不容任何人欺她、辱她、輕她、踐她!
436.7萬字8.18 676395 -
完結654 章
震驚!太子會讀心后夜夜翻我牌子
太子蕭錦言是個講究人,對另一半要求很高,擁有讀心術后要求更高。奈何身邊美人無數,卻沒一個是他的菜,直到看見一條小咸魚,嘴甜身子軟,正合他胃口,“今晚你侍寢。”作為混吃混喝的小咸魚瑟瑟發抖:“殿下,我還沒長開呢。”*沈初微一朝穿回古代,成了太子爺不受寵的小妾,琴棋書畫一樣不會的她,以為是混吃混喝的開始,卻沒想到被高冷太子爺給盯上了。徐良媛:“沈初微,你最好有點自知之明,今晚可是我侍
149.2萬字8 67371 -
完結278 章

王妃又帶崽爬墻跑路了
【事業心女主+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男二上位】 一場意外穿越,唐雲瑾身懷六甲,被無情男人丟至冷院囚禁,承受著本不該承受的一切! 多年後再見,他奪她孩子,威逼壓迫,仍舊不肯放過她。 為了打翻身仗,唐雲瑾卧薪嘗膽,假意妥協,卻用芊芊素手行醫,名震京城! 當塵封多年的真相解開,他才知自己這些年錯的有多離譜,將她堵在牆角柔聲哄道:「本王什麼都給你,原諒本王好不好? “ 她卻用淬毒的匕首抵住他的喉嚨,冷冷一笑:”太遲了,王爺不如...... 以命相抵! “ 後來,她冷血冷心,得償所願,穿上鳳冠霞帔,另嫁他人......
100.6萬字8 20983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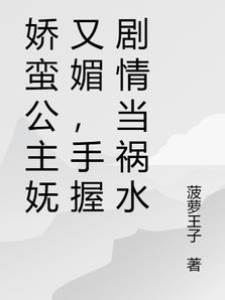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
完結172 章

沖喜王妃腰太細,病嬌王爺狠又毒
【1v1,雙潔雙強+爽文+寵妻無底線,女主人間清醒】寧家滿門覆滅,兩年后,寧二小姐奇跡生還歸京,卻嫁給未婚夫的皇叔,當了沖喜王妃。 皇叔垂死病中驚坐起:王妃唇太甜腰太軟,他怎麼能放任她去蠱惑別的男人? “兵權給我,王府給我。” 病嬌皇叔點頭,抱著她寬衣解帶:“都給你,本王也給你好不好?” “?” 給……給什麼? * 歸來的寧三月只想為寧家翻案,誓為枉死的人討回公道。 后來,寧三月多了一個目標:當好沖喜王妃,讓皇叔好好活著。
29.9萬字8 1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