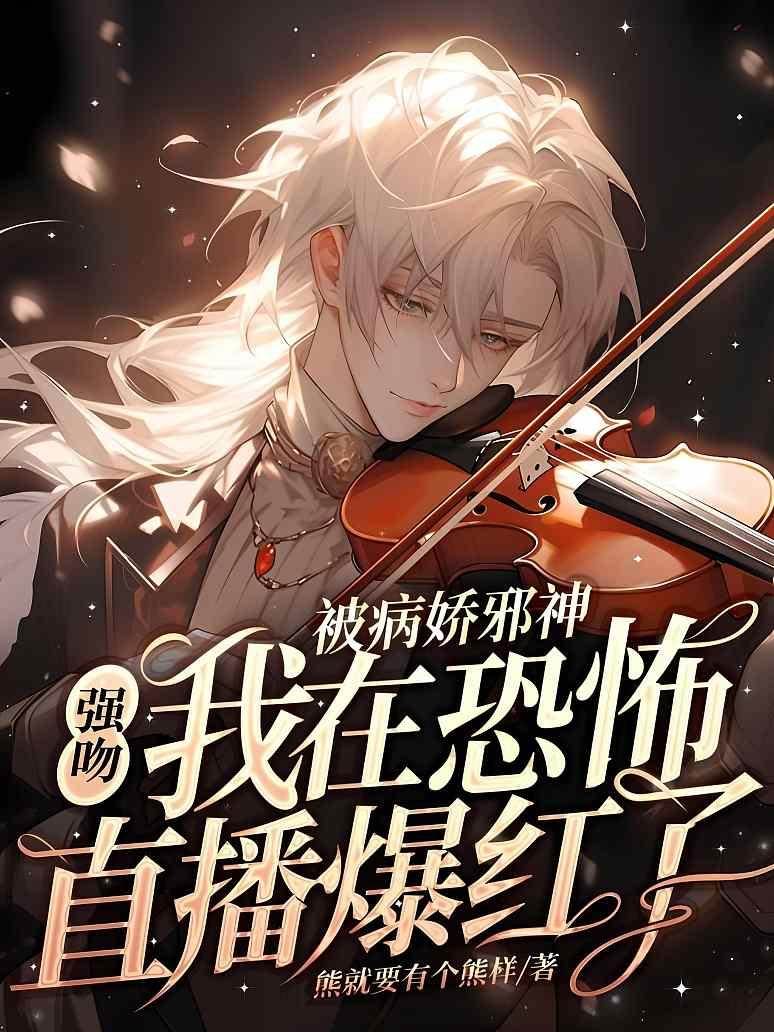《想他》 第49章 和他
清晨的第一縷從窗簾的隙中落在床角, 沈驚瓷醒的時候,太已經到過頭頂。
眼皮微,酸楚隨之而來, 還有傳來一種薄荷涼颼颼的覺。小小的難了聲,下意識的要蜷起, 作剛起了個頭, 就覺被人摁住膝蓋。
陳池馭低沉的嗓音模糊的出現耳邊,與指尖的清冽不同:“別。”
沈驚瓷惺忪的睡意散了大半,意識到是哪里傳來的怪異后驚慌的撐起手肘, 出口的聲音讓都驚訝, 又啞又,巍巍的著男人的名字:“陳池馭...”
陳池馭應了聲:“醒了啊。”
男人躬過來堵住的聲音,他里氣的開玩笑的說:“怎麼還這麼。”
沈驚瓷渾僵的想回,小姑娘一臉戒備和堅決的使勁搖頭,眼睛微微有些腫, 氤氳可憐的抬眼:“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臉埋進男人的脖頸,從手臂下面傳過去環著他凸起的肩胛骨, 快要被欺負哭了:“昨晚還沒好..漲, 難。”
陳池馭垂眸看到孩窩著的小腦袋,怎麼都不肯抬頭。瞬即一愣,又忍不住的失笑, 三手指在后頸上了, 俯頸低聲問:“還在還難?”
沈驚瓷耳朵都紅了, 外面天正明, 陳池馭的聲音滾燙炙熱, 趁機從被子中抓住男人的手, 一種黏膩的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沾上指尖,沈驚瓷心悸沒忍住的收力氣。
Advertisement
“你...你太過分了。”沈驚瓷像是了驚的貓,脊背弓起炸開,扔開陳池馭就往被子里,看著男人的眼神仿佛是他干了什麼驚天霹靂的事。
陳池馭看著沈驚瓷這一溜串的作,視線在自己被扔回來的手和沈驚瓷之間打量。頓了幾秒,生生氣笑。
他磨了磨后槽牙,揚眉去睨沈驚瓷:“我就這麼畜生?”
沈驚瓷躺在床上,裹得嚴嚴實實,只出一雙黑漆漆的眼睛,轉過來轉過去的躲閃著。
其實不敢說,覺得他昨晚真的好畜生。
“肚子里罵我呢?”男人冷笑,聲音還帶著涼意。
被說中心思的沈驚瓷一驚,男人已經下來。不過卻是拎這被角蓋上了的臉。
線一下子暗沉,聽到的聲音輕挑點名:“我要是個畜生,把門一關隨你怎麼。”
他一頓,接著又說:“你能有辦法?”
沈驚瓷還沒反應過來,他的手隔著被子搭在了脖頸的位置,冷森森的威脅:“撐開。”
下一涼,清新的空氣從豁口傳來。他的手指讓止不住的:“陳...”
他聲音低了低,阻止了那些七八糟的想法:“藥。”
沈驚瓷微怔,掙扎的作隨著空氣停滯,從被子中掙扎出來的臉更紅。
一床被子爛七八糟,他似乎嫌有點礙事,拉著腳腕拖到邊緣,被子翻上去,又了泛紅的地方。
Advertisement
沈驚瓷抱著被子不敢看,他的手好冰,應該是被冷水沖刷過,混著藥膏折磨的要死了,忍不住的哼出聲。
陳池馭肯定是聽見了,目上移,看到甕聲甕氣的糾結,還是想笑,小姑娘聲音都快低到沒邊了:“要不我自己來吧。”
他一本正經的往里,看不出毫的歪意:“你夠不到。”
沈驚瓷腰下意識的上拱,就知道他是故意的,哭腔著要踹他:“大騙子!!”
陳池馭眉宇懶散的低笑,也不阻止。
折騰了好久,沈驚瓷上出了一層薄汗,還有個齒印。是自己咬的。
陳池馭疼惜的挲了兩下,抱著人起來吃飯。
沈驚瓷氣哼哼的不搭理他,手搭上他肩膀的時候,才發現好像有什麼不對勁。
左手的手腕多了樣東西,一個很漂亮的滿圈飄花手鐲,沈驚瓷不會看翡翠,但一眼就覺得好喜歡。
靠在人上,驚愕的側臉去看陳池馭:“你給我戴的嗎?”
男人角弧度很淡,瞥了一眼微哼。走到餐桌把人放在椅子上,盤子放在手邊:“不喜歡?”
沈驚瓷手指勾著看,應聲回答:“喜歡。”
眉輕輕皺著,轉念想到什麼:“這個是不是好貴。”
陳池馭攪拌好粥,喂到邊:“啊,張。”
沈驚瓷像是一只小兔子一樣盯著他,陳池馭掃了眼,話到邊變了味兒:“是貴。”
Advertisement
沈驚瓷就知道陳池馭買的東西不會便宜,本不是能等價回送的,人有點小心翼翼的試探:“多貴。”
粥一勺一勺送到邊,沈驚瓷還要低頭去吃。
“貴到,口袋空了。”他掀起眼皮,一字一頓的開口補充:“全、家、、當。”
沈驚瓷啊了聲,要往下拽鐲子的作愣了愣,陳池馭接著揪了個吐司塞進的里,又懶散下來:“不用還,負責就行了。”
作者有話說:
您好,還是我敬的專審大人,國慶快樂,個藥而已,敏詞都刪過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91 章
顧少,你老婆又帶娃跑了
在雲城,無人敢惹第一權貴顧遇年,關於他的傳聞數不勝數。陌念攥著手裡剛拿的結婚證,看著面前英俊儒雅的男人。她憂心道:“他們說你花心?”顧遇年抱著老婆,嗓音溫柔,“我只對你花心思。”“他們說你心狠手辣?”“要是有誰欺負你,我就對誰心狠手辣。”“他們說你……”男人伸手,把小嬌妻壁咚在牆上,“寵你愛你疼你一切都聽你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還是你的。寶貝還有什麼問題嗎?”婚後。陌念才知道自己上了賊船。她偷偷的收拾東西,準備跑路。卻被全城追捕,最後被顧遇年堵在機場女洗手間。男人步步緊逼,“女人,懷著我的孩子,你還想上哪去?”陌念無話可說,半響憋出一句,“你說一年後我們離婚的!”男人腹黑一笑,“離婚協議書第4.11規定,最終解釋權歸甲方所有。
130.5萬字8 30545 -
完結978 章

孽火
繁華魔都,紙醉金迷。我在迷惘時遇到了他,他是金貴,是主宰,把我人生攪得風起云涌。我不信邪,不信命,卻在遍體鱗傷時信了他,自此之后,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253.1萬字8 16987 -
完結679 章

財閥大佬,您的夫人A炸了
【萌寶+馬甲+女強男強+打臉爽文】 正式見麵前: “找到那個女人,將她碎屍萬段!” “絕不允許她生下我的孩子,找到人,大小一個也不留!” 正式見麵後: “我媳婦隻是一個被無良父母拋棄的小可憐,你們都不要欺負她。” “我媳婦除了長的好看,其他什麼都不懂,誰都不許笑話她!” “我媳婦單純善良,連一隻小蟲子都不捨得踩死。” 眾人:大佬,求您說句人話吧!
124萬字8.25 732289 -
完結73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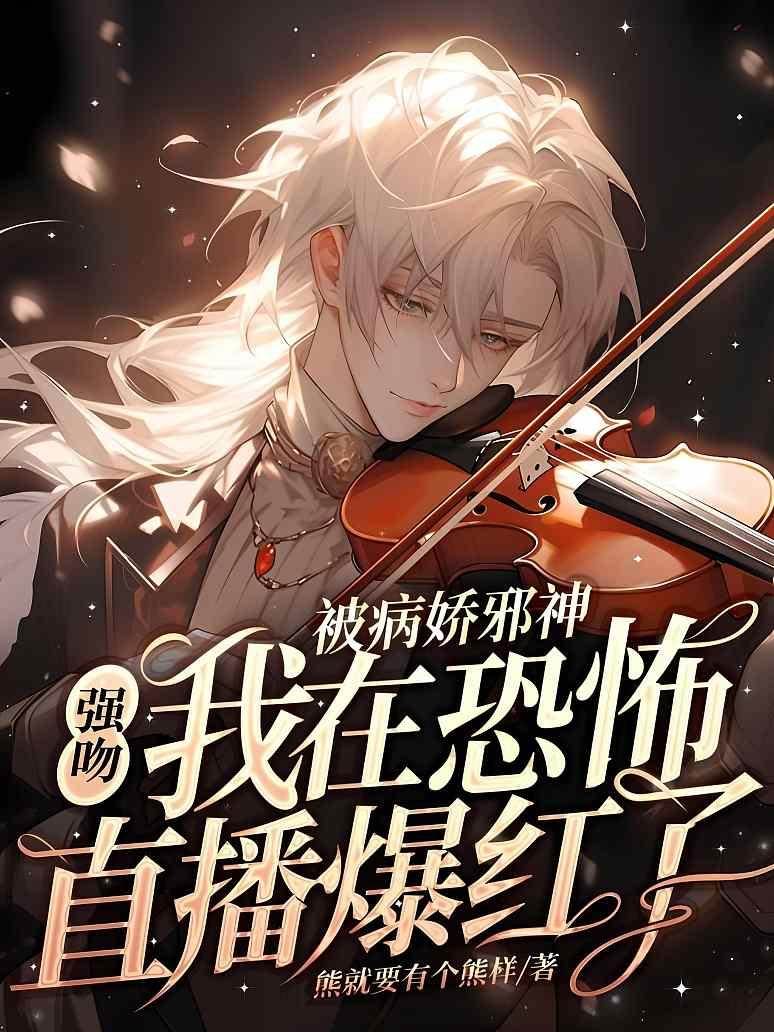
被病嬌邪神強吻!我在恐怖直播爆火了
桑榆穿越的第一天就被拉入一個詭異的直播間。為了活命,她被迫參加驚悚游戲。“叮,您的系統已上線”就在桑榆以為自己綁定了金手指時……系統:“叮,歡迎綁定戀愛腦攻略系統。”當別的玩家在驚悚游戲里刷進度,桑榆被迫刷病嬌鬼怪的好感度。當別的玩家遇到恐怖的鬼怪嚇得四處逃竄時……系統:“看到那個嚇人的怪物沒,沖上去,親他。”桑榆:“……”
123.3萬字8.1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