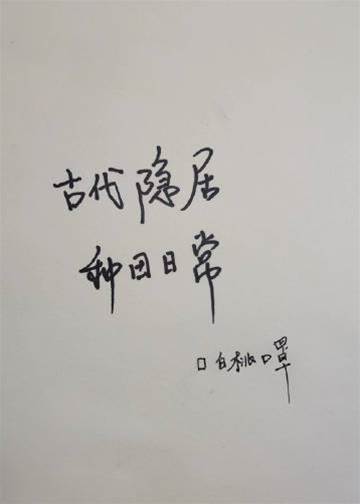《位極人臣后我回家了》 第58章 第58章
“姐姐、姐姐。”
常意放下手里的東西, 依著聲音的來源看過去。
桌子對面沒有人影,常意頓了下,往桌子底下看了一眼。
一個圓子般.可的小孩鉆了出來, 二話不說撲在了端坐著的子膝上。
“劉圓子。”
常意出一手指抵住他白白.的臉蛋,了一下,忍住笑意問道:“你怎麼進來的?”
小孩捂住自己的臉, 傻乎乎代;“姐姐, 我現在沈圓子啦。父皇說我沒事可以來這里看你,我就來了, 門口的人說我可以進的。”
當然了,他是未來的太子殿下,誰敢攔他。
看是假, 讓照顧孩子才是真。常意看著煥然一新的沈圓子, 在宮中養了幾日, 本來就可的小臉更加雕玉琢, 穿金戴銀的也不突兀。
皇帝給他擬了個正式的名字,名昭。
昭為明燦爛之意, 皇帝給他定了這個名字,也是心疼他丟的那幾年, 希他日后明正大,得親人護、萬人尊重。
但這個他原本用了幾年的名字,皇帝也并沒有否定。
常意拍了拍他的小手, 他上還沒養起來, 不難看出上的消瘦, 也心疼這個孩子,但除了給他原有的份和生活,總有人得教他怎麼人。
語氣嚴肅下來:“皇上日理萬機, 命我教你讀書。你現在是太子殿下,會有很多人盯著你的錯。以后不可我姐姐了,要老師,知道了嗎?”
沈圓子張了張,乖巧地說道:“老師。”
“嗯。”常意想到了什麼,了門口的侍進來,搬了張椅子放在旁邊。
“坐這兒。”拍了拍邊的椅子,讓他別失了份,繼續膩在膝上:“以后你便坐這里,不止我在的時候,其他人在樞機值班時,你也可以在這旁觀,學學東西。”
Advertisement
驀然想到沈厭的大字報,話停在邊:“若是沈大人值班,你可以不用來。”
沈圓子在手下不不愿地挪了挪子,說道:“我只想跟著姐……老師一個人學。”
他進了宮,發現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樣,能說話的只有一個皇帝爹爹,父皇雖然對他很好,但忙得團團轉,每次來看他也是出時間,臉上的疲憊讓他看了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的娘還沒醒過來,他常去看,可娘睡著,還沒回應過他。
他見了常意,忍不住就想湊上去多親近一會。
常意輕笑了一下:“貧,你識了幾個字了。”
沈圓子在劉兵足那個無賴家中是沒讀過書的,字也不識幾個,常意雖然是太子太師,也沒那個時間手把手地教他識字,太子行宮里自然有啟蒙的老師在教他。
常意問起來,沈圓子明顯有些慌了,磕磕地給背了幾篇榮朝給兒啟蒙的冊子。
常意一一聽了,發現他字雖然識的不多,但從學的這麼點時間上來看,沈圓子顯然是天資不錯的那一卦。
“學的不錯。”常意夸了他一句,還沒等他尾翹起來,誰知道是先禮后兵。反手從后邊的書架底層出一本書。
兩本。
三本。
……
十七本。
沈圓子目驚恐地看著桌子上碼放整齊的書冊,回了凳子上。
常意用書打發了他,繼續理桌子上的事務。
沈厭走進來,便看見常意手旁堆著的一堆冊子,這些書被打眼地堆一個塔狀的建筑,而中間的空隙里出一張白的小臉。
沈圓子此刻只覺得不管做什麼,都比起看這些枯燥無味的冊子有趣,一點點靜都能讓他轉移注意力。
他兩條小蹬蹬地跳下椅子,跑到沈厭面前。
Advertisement
他吧嗒了一下眼睛,仰起頭來看沈厭,好高呀,看起來還是那麼可怕。不過聽了常意的話,沈圓子知道了沈厭是大將軍,便不覺得他可怕了。
那些冊子比沈厭可怕多了。
沈圓子心有余悸。
沈厭淺淡的目始終落在常意上,稍稍移開,拂開下擺,半跪下說道:“太子殿下。”
沈圓子還有些不適應份的變化,有些不好意思地回頭看向常意。
常意已經放下了筆,一只手支著下,淡淡地看著他們兩個。
沈圓子連忙拽了拽沈厭的袖子,讓他起來。
常意說道:“正好,他也沒心思看書了。你帶他去獵場騎騎馬?”
小孩子本就敏銳,他覺到常意和沈厭之間的氣氛變了,變得好像有點微妙的不一樣。
但是什麼樣,他也說不出來。
沈厭坐到了桌子對面,落下目道:“讓張京帶他玩。”
在外頭候著的張京應了一聲。
沈圓子有些不樂意,但比起在書房里繼續讀到生無可,他還是選擇了出去玩。
小孩正是力充沛的時候,跟個小馬駒似得嘚嘚嘚跑了出去,留下書房里的兩個人。
常意用折子遮住半個臉,向他眨了眨眼睛,明知故問地說道:“沈大人是來做什麼的?今日又不是你值班,難不是來幫忙理奏折的嗎?”
若是別人幫忙還有幾分可信,讓沈厭來,怕不是要把這些冗詞贅句、廢話連篇的請安折子都打回去,讓寫的人滾蛋。
眼型姣好,眨眼時仿佛兩只蝴蝶在他口撲騰,激起一池的漣漪。
沈厭放在桌子上的手不自覺握了點,偏過頭不語。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來這,不知不覺地過來了。
除了這兒,他好像也沒別的地方可去,他只想去有的地方待著。
Advertisement
沒有戰場和敵人供他發泄滿腔無措的緒,他覺自己像一口被逐漸灌滿水的井,除了面前的這個人,裝不下任何東西。
只是看看就好。
有些東西沒有過還好,一旦過,就像滲進骨頭里染了癮,夢里都是被自己抱在懷里的暖意。只是看不見半天,他都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癮。
沈厭甚至連提都不敢提昨日半分,怕握在手里的種種只是他混淆了一場夢。
手腕上冰冷的拉回了一些他混沌的神智。
常意的指尖搭在他脈上,瞬間讓他冷靜下來。
常意說道:“你的脈有逆行之勢。”
沈厭迅速回手,端著說道:“沒有。”
常意蹙眉,手過去拉住他,果然脈象又恢復了正常,沒想到還能這樣耍賴,沉默了片刻:“記得喝藥。”
心里始終還記著沈厭的病。
沈厭發病只見過兩次,第一次是在長堰村山上的墓里,第二次就是在常家那口舊井之下。除此之外知道的,沈厭在這幾年中還發過幾次病,但機緣巧合被事絆住,沒見過他發病的模樣。
在經過常家那一.夜之前,常意還不知道那天在墓室里的小怪,原來是他發了病的樣子。
他怎麼會出現在墓室,又為何會發病,在山里看見了什麼,臉上的怪斑是怎麼消失的——常意一無所知。
沈厭不提,常意也沒想過他說出來,淡淡地斂下眉眼,又執筆批起了折子。
沈厭看不再看自己,冷清的眉眼染上了些許燥意。頓了一會,他放在桌子上的手移了一點,試探地了常意左手的指尖。
兩人皮間的溫度不同,即使是一點點若即若離的,異樣都分外明顯。
Advertisement
紙上流暢的墨跡停頓了一瞬,字形的末尾留下一個小點,又若無其事地寫了下去。
可人總是貪得無厭的,在戰場上所向披靡、能征慣戰的大將軍,在任何事上的野心與.都同樣昭然若揭。
那只比大的多的手和的手逐漸重合,骨節分明的手指的指,被他完全攏在手里。
沈厭的手清癯修長,仿佛鐵打的一般,上面長年持握劍爬滿的繭子糲地磨著的手,又又疼。
常意被他的作帶得右手也抖了一下,筆尖在空中劃出一小道弧線,從硯臺里濺出幾滴墨。
常意忍無可忍地蜷了蜷手,聲音里都帶著些惱意:“——沈大人,你收斂些。”
指尖輕,惹得沈厭抬眼,他手上繃著浮現出幾道青筋,一直繃到了小臂。他小心翼翼地松了些力道,但還是像叼到了骨頭的小狗,一點不舍得放手。
常意的手像一塊綢緞,里頭撐著些竹條,消瘦,但是棱角并不突出,著是的。沈厭握住了,又輕得好像什麼也沒有握住。
十指相扣,指間有些不屬于他的細小的疤痕磨蹭著他的繭子,是常意留在指間抹不去的傷口。
他傾了些子,在常意微微怔忪的眼神中低頭吻住了的指尖。
他的吻不帶任何.,只是極輕地落了下來。沈厭握著的手,從指尖再到指腹,順著的指骨一點點向下溫地親吻。
冰冷的在常意手指上分外清晰,或許是因為重新長過一回,手上的皮比別都要敏.許多,沈厭的每一次,都讓控制不住輕,不風的吻幾乎包裹了。
又熾熱的氣息,在皮上游走。
“沈厭!”常意聲線,連本來怪氣的沈大人都不喊了。閉上雙眼,不愿看他:“你能不能……別這麼放肆。”
回應的是更加纏.綿的作。
外頭突然傳來侍急急忙忙的拜見聲。
“寺卿大人,常領事在里邊呢……”
外頭的男聲應了一聲,敲了敲房門:“常大人,有事找。”
“進來。”
常意驀然睜開雙眼,聲音冷靜下來,回應道,正好和握著手的沈厭對上眼神,沈厭抬眼,似乎有些不滿,帶了幾分戾氣。
他本全,出些野般直截了當的貪婪和占有,和當初那個小怪沒什麼兩樣,也不知道他發病了沒有......常意不看他的眼神,抿著努力恢復原本若無其事的樣子。
封介走進屋子里,腳步頓了一下,眼神在沈厭臉上打了個圈,低聲咳了一下:“沈大人可真是滿腹經綸啊。”
他訕笑了一聲。也不知道他們倆干了什麼,若是知道沈厭也在,他必然要挑個其他時間過來。
他移開視線,開玩笑道:“莫不是剛剛把硯臺吃了。”
沈厭側了側臉,角邊沾了一些不明顯的墨痕,在他白發襯托下確實有些打眼。
他懶散地抬起手抹了下,那點墨的痕跡像子的口脂一般,被抹得無影無蹤了。
猜你喜歡
-
完結986 章

農門有喜無良夫君俏媳婦
東臨九公主天人之姿,才華驚艷,年僅十歲,盛名遠揚,東臨帝後視若珠寶,甚有傳位之意。東臨太子深感危機,趁著其十歲壽辰,逼宮造反弒君奪位。帝女臨危受命,帶先帝遺詔跟玉璽獨身逃亡,不料昏迷後被人販子以二兩價格賣給洛家當童養媳。聽聞她那位不曾謀麵的夫君,長得是兇神惡煞,可止小孩夜啼。本想卷鋪蓋逃路,誰知半路殺出個冷閻王說是她的相公,天天將她困在身旁,美其名曰,培養夫妻感情。很久以後,村中童謠這樣唱月雲兮哭唧唧,洛郎纔是小公舉。小農妻不可欺,夫婦二人永結心。
173.1萬字8.18 37020 -
完結426 章
生於望族
可憐朱門繡戶女,獨臥青燈古佛旁.生於望族,柔順了一輩子,只落得個青燈古佛、死於非命的下場.既然重生了,她就要堅強,徹底擺脫從前的噩夢!可是,上一世錯身而過的他,爲什麼總是出現在她的面前?
157.7萬字8 39181 -
完結1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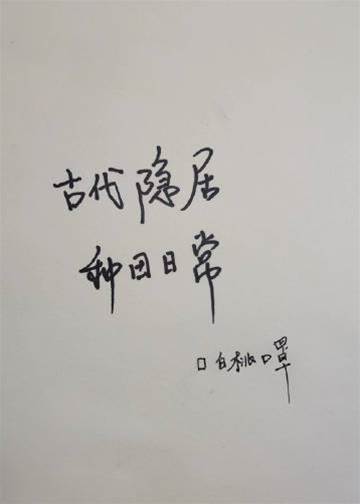
古代隱居種田日常
資深加班狗沈小茶在下班途中低血糖暈倒了,醒來發現自己竟穿進了古代某廢棄村莊。沒有雞鳴、狗吠、炊煙。只有廢田、斷壁、枯骨。和萬物可淘的淘寶系統。21世紀社恐女青年古代荒村歲月靜好隱居模式.歡樂上線。…
25.3萬字8 94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