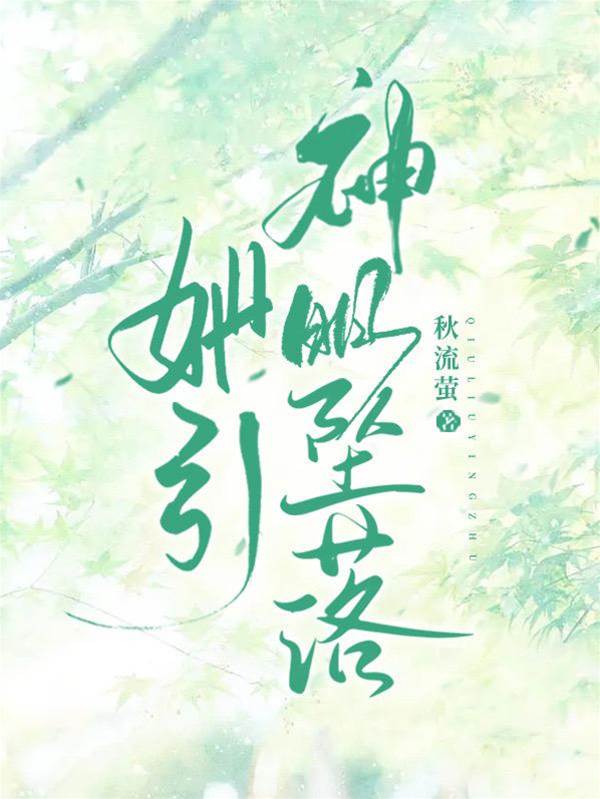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先婚后甜》 第91章 第 91 章
悅沒搭理江邵這句話,神平淡的想把手回來,江邵握著的手指了些,把滾燙的臉頰在手背上,抿著,眼睫微挑,眼底閃著晶亮的,滿懷希翼的凝視著。
看似小心翼翼討好,實則充滿侵略,只等著步他的圈套。
已經跟他說了分手,如果這會心,上了他的床,那還有什麼原則可言。
但面對如此‘虛弱可憐’的江邵,即便知道他多半是裝的,可他上燙人的溫度是真的,悅沒法對還發著燒的他冷言冷語,垂眸盯著他臉,站著沒,也沒說話。
算是無聲的拒絕。
江邵這回倒是沒有多做糾纏,放開手,老實的躺在床上,垂著眼皮,了干燥的,看起來虛弱不堪。
悅拿起杯子,轉過,去廚房,又倒了一杯水。
回到臥室,床上的男人已經闔上了眼,側躺著,呼吸聲很重,看起來很不舒服。
悅把手搭在他額頭上,又了一下,很燙,跟剛剛沒什麼差別。
悅去浴室用溫水打了條巾出來,給他了臉。
江邵眼睫微,不知是沒睡著,還是睡著后又被弄醒了,不過沒睜開眼,對的照顧很。
悅拿著巾的手落在他脖子上,目順著他的結向下掃了眼,有些糾結猶豫,以前發燒,江邵照顧,都會用巾一點點給拭,每次他完,高熱的確實會舒服很多。
可兩人現在的關系,給他似乎不太合適。
悅斟酌片刻,收回手里的巾,沒再繼續。
去浴室又擰了一條新巾,整齊的折疊幾層,拍了拍他肩膀,示意他平躺著,把巾放在他額頭。
他病懨懨的,雖吃了藥,但燒還沒退,悅沒急著走,拿手機坐到一旁的沙發上。
Advertisement
江邵是真的病了,沒多會就睡著了,翻了個,又變了側躺著,額頭上的巾落,悅腳步很輕的走過去,把巾拿起來,看他眉心輕蹙,似乎很不舒服。
藥才吃沒幾分鐘,沒那麼快發揮效果,悅沒再探他額頭的溫度,轉走出臥室,輕手輕腳關上門,給孫品鴻打電話。
“江邵晚上吃飯了嗎?”
孫品鴻:“沒吃,江總上午就開始發燒,午飯都沒吃。”
悅嗯了聲,說:“知道了。”
掛斷電話,悅去廚房,打開冰箱看了眼,干干凈凈,什麼菜都沒有。
生病的人一般都沒有胃口,兩頓飯沒吃,應該也不太能吃什麼飯,只能吃點清淡的。
悅從櫥柜里找到米,放到鍋里洗凈后,添了點水,上電煮粥。
從廚房里出來,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到手機上孫品鴻給發過來很長一串消息。
匯報了江邵最近一段時間的工作作息和飲食況,說的很詳細,像是回到了五年前。
那時候,住在國外的別墅里,江邵有工作,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在國外和一起的時間很,佯裝不滿他陪時間太,兩地分居,也不知道他每天去了哪里,萬一去找其他人也不知道。
作為一個被江邵養在籠子里的‘金雀’,說出這種拈酸吃醋的話,他免不了摟著甜言語的哄,說他心里眼里只有,其他人從不多看一眼,然后便是把到床上,力行的折騰一番,教訓不信任他。
過后他便讓孫品鴻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匯報給,工作的時候吃了什麼,工作到幾點,參加了什麼應酬,事無巨細。
這個習慣持續到回國,兩人鬧那樣,恩的假象不在,相互搶生意,孫品鴻自然沒有繼續把這些事告訴。
Advertisement
這會鍋里煮著做給他的粥,孫品鴻又把他的行程告訴,悅心復雜,有些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是在干什麼。
已經分手,他是死是活都跟沒關系了,江邵本就不愿意分手,只是用了點苦計,就真的跑了過來,等他病好后,肯定更不會愿意放手。
悅抬手按了按額頭,垂下眼睫,腦中想著和江邵的事,一團麻。
不知不覺,已經在客廳里坐了一個小時。
廚房里的粥早就煮好,悅推開臥室門,看見江邵大半個都在被子外面,額頭脖子上麻麻冒了一層汗。
悅走過去,幫他把被子蓋好,手掌上他額頭,溫度似乎比剛剛低了些。
應該是退燒藥起了效果,他上還在不停冒汗,前的服都汗了,他蹙著眉,抬手拽了下領,要踹被子。
還發著燒,可不能再著涼,悅按住他手,也不管他能不能聽見,湊到他耳邊,輕聲說了句,“別,把被子蓋好。”
話音落,江邵便不了。
這樣出汗,應該過不了多久就能退燒。
悅又去浴室拿巾給他手臉,目落在他已經,在皮上的白襯,沒再猶豫,手解開他襯上幾顆紐扣,出他健碩的膛。
悅拿著巾,了他膛上的汗。
夏天的時候,很多男人在外面都著膀子,勉強給他口,再往下,就不方便了。
剛完口,江邵突然睜開眼,抓住手腕,深不見底的眸像凝了團火似的看著,不等反應過來,便用力一拽,把拉到懷里,摟著腰,翻了個,把到下。
悅下意識掙扎著推他。
江邵按住腰,湊很近,低低的息,“別,你再,我要控制不住了。”
Advertisement
江邵嗓音發沉,說出的話熾熱又直白。
滾燙的氣息噴灑在臉頰,臉上也開始發熱,手指攥拳,抵在他肩膀,繃,不敢。
“你上服都汗了,我在給你汗,你快放開我,不要來,燒還沒退呢。”
江邵著腰,目灼熱的看著,聲音委屈的說:“我難。”
這個難,指的是什麼,自然不同于他賣慘時說的頭疼,悅懂。
“忍著。”
佯裝淡定的轉移他注意力,“廚房里有粥,你既然醒了,就過去吃一點。”
江邵低,若有似無的到,啞聲說:“不想吃粥,我想吃你。”
“不行。”悅毫不猶豫的拒絕他,“你發燒呢。”
“不發燒的時候就可以了嗎?”江邵故意曲解意思,含住耳朵,哄道:“發燒也沒關系,我好,你不用擔心我,讓我多,再出些汗,就好了。”
江邵在咬耳邊說流氓話,“試一次,好不好。”
悅瞪了他一眼,抬腳踹他,“滾開。”
江邵不在乎被踢,這一腳不痛不,摟更,上還是燙的,但毫無剛剛病懨懨的虛弱樣,力氣很大,他不主放開,本掙不開。
除了最開始跟他鬧得天崩地裂那會,之后悅很在這種況下跟他。
調整了下呼吸,眼睛著他,淡聲道:“江邵,你再這樣耍無賴,以后你就是燒死,我都不會再上你的門。”
江邵臉一僵,翻了個,從上下去,側抱著,額頭抵著額頭,蹭了蹭,道歉速度很快,“我錯了,你能來看我,我已經很開心了,你還給我,我太激了,沒忍住,悅悅,我真的你,每天都想你,我真的離不開你,你呢,明知道我是苦計,還過來照顧我,心里肯定有我吧。”
Advertisement
悅偏頭,避開他視線,推了推他肩膀,“你先喝點粥吧。”
“沒胃口。”江邵抱著,沒,目盯著,等回話。
悅:“我熬的,你真的不喝嗎?”
聽到悅說粥是熬的,江邵干脆利索的翻下床。
在床上躺了這麼久,突然站起來,一陣頭重腳輕,形晃了下,險些栽倒。
悅見狀,趕手扶他,讓他坐,“你別了,我去把粥端過來。”
江邵按了按太,嗯了一聲,腦子有些鈍疼發沉,江邵閉眼緩了緩,老實的坐在床邊。
悅盛了碗粥,端進臥室。
江邵喝完粥,又出了一汗,要去浴室洗澡。
悅怕他摔,不太放心,眼睛一直盯著他,言又止。
江邵拿了服,走到浴室門前,突然回頭看,眸中掀起一抹意味深長的笑,“你如果不放心,就跟我進去一起洗。”
悅白了他一眼,轉往外面走,“既然你沒什麼事了,我就回去了,你等會洗完澡,再用溫槍量一遍溫,廚房鍋里的粥是保溫的,你回頭了自己去盛,不要不吃飯,你之前答應過我,不會糟蹋自己的。”
說到這里,悅眉頭蹙起,“現在胃病越來越年輕化,得胃癌的人很多,你不要仗著自己好,不當回事,還有你這發燒,你……”
悅話還沒說完,便被他抱住,手臂橫過腰,下搭在肩膀上,小心翼翼的說:“今晚能不能不走,你剛剛答應過我,不走的。”
說了那麼多,他就聽見第一句了,高大的圈著,低沉的嗓音又開始發,“悅悅,別走,我想和你在一起,除了令你厭煩的糾纏你,我真的…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他偏頭,著脖頸,輕輕磨蹭。
太會賣慘了。
悅輕輕嘆了口氣,拍了拍他肩膀。
江邵頭從肩膀上抬起來,垂著眸,眼眶漉漉的,像個搖尾乞憐的小狗,可悅知道,這只是他示弱時的假象。
他哪里是狗,他分明就是一條大尾狼。
悅手,猛地揪住他領,冷聲道:“我不管你是用了什麼法子把自己折騰病的,你如果想跟我在一起,以后就得聽我的,我讓你吃飯就吃飯,讓你睡覺就睡覺,不許再用這樣的把戲。”
江邵心臟狂跳,驚喜道:“你這意思,你這意思……”
他歡喜的在上親了一下,“你這是不跟我分手了,是不是。”
悅沒好氣道:“我分得掉嗎,你干嘛……”
江邵把抱起來,抵在墻上,麻麻的吻落在脖頸上。
悅雙手摟著他脖子,仰著頭,被他吻得呼吸不穩,“江邵,你先放我下來,我還沒說完……”
江邵不聽說,急促的吻落在上,忙著宣布主權,“有什麼規矩你等會再說,先讓我親一會。”
“你說你怎麼這麼沒良心。”他自覺份不一樣了,語氣低沉的教訓,“你怎麼忍心跟我分手,以后不許再提分手的事。”
猜你喜歡
-
完結1091 章

失憶后我成了法醫大佬
十三年前全家慘遭滅門,蘇槿患上怪病,懼光、恐男癥,皮膚慘白近乎透明,她成了「吸血鬼」,選擇在深夜工作,與屍體為伴;他背景神秘,是現實版神探夏洛克,刑偵界之星,外形豐神俊朗,愛慕者無數,卻不近女色。第一次見面,他碰了她,女人當場窒息暈厥,揚言要把他送上解剖臺。第二次碰面,她手拿解剖刀對著他,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具屍體。一個只對屍體感興趣,一個只對查案情有獨鍾,直到未來的某天——單宸勛:你喜歡屍體,我可以每天躺在解剖臺任你處置。蘇槿:我對「活的」沒興趣……
196.7萬字8.18 22956 -
完結1233 章
七零年有點甜
何甜甜一直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的人。人到中年,卻發現一直生活充滿謊言的騙局里。重回七零年,何甜甜在小銀蛇的幫助下,開始新的人生。換一個角度,原來真相是這樣!這輩子,再也不做睜眼瞎了。這輩子,再也不要錯過辜負真心相待的青梅竹馬了,好好待他,信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215.3萬字8 54157 -
完結877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
生日那天,深愛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卻是一場復仇。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了記憶,再也不是從前了深愛霍雲霆,死活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這個婚離定了!” 夏初薇:“離婚?好,明天就去,誰不離誰是小狗。”第二天,夏初薇敲開霍雲霆的門。“霍先生,該去離婚了。” 霍先生:“汪!”所有人都知道她愛他至深,但唯有他,他愛她多次病入膏肓。
157.9萬字8 6044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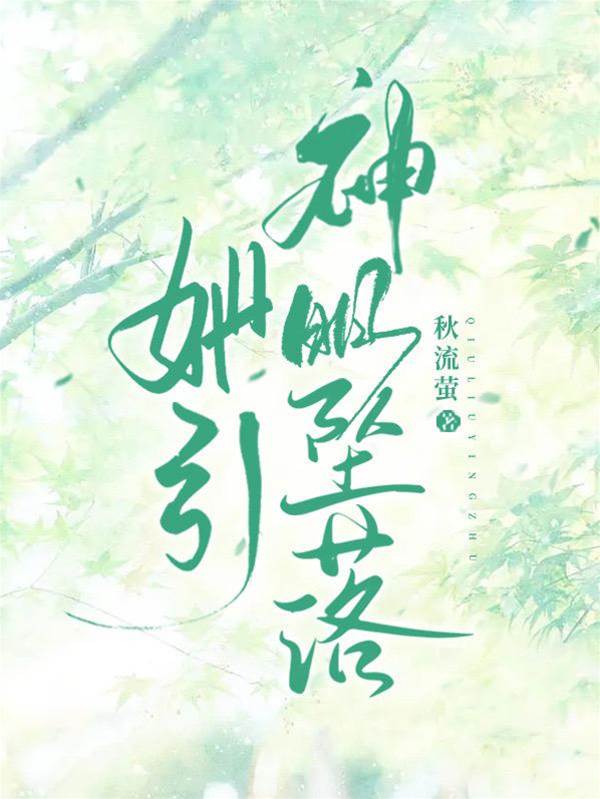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80 章

幸福不脫靶
他連吵架時擲出的話都如發口令般短促而有力:“不許大喊大叫!給你十秒時間調整自己,現在倒計時,十,九……” 她氣憤:“有沒有點兒時間觀念?需要調整十秒鐘那麼久?” 他是個很霸道的男人,對她裙子長度引來的較高回頭率頗有微詞:“你可真給我長臉!”見她呲牙笑得沒心沒肺,他板起來臉訓她:“下次再穿這麼短看我不關你禁閉。” 她撇嘴:“我是滿足你的虛榮心,搞得像是有損安定團結一樣。” 我們的小心願,幸福永不脫靶。
24.6萬字8 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