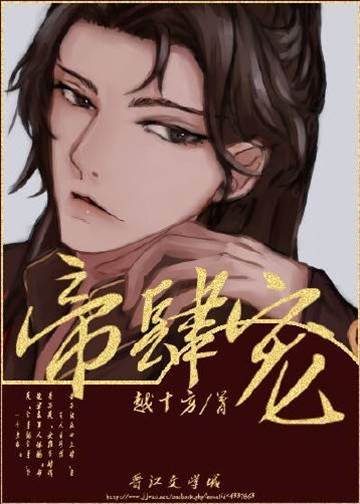《風荷舉》 佛寺(2)
已經長大了,早已不再是個小孩子,又生得頗為高挑,可他抱還是很輕鬆,就像小時候他把打橫抱起來一樣容易。他高大而有力量,環抱著的手卻很輕,有一瞬間他們離得很近,在他那雙漂亮的目裡看到自己的倒影,於是那種玄妙的覺又將懾住。
齊嬰其實也一樣。
纖細的腰肢就在他掌心之間,淡淡的馨香繚繞著他,的曲線有一剎那與他相。
他實在無意冒犯,也確實不想自己生出什麼逾越的念頭,可那一時心頭的紊騙不了人,甚至連他自己都騙不過去。
他的慌張甚至與旗鼓相當。
隻是小齊大人在場上多年磨礪,自然比個小姑娘心沉穩許多,而且他還深諳一個道理,越是在心緒不穩的時候,麵上卻要看起來平靜無波。他將這番道理踐行過許多回,每回都十分奏效,此時便也假意作出滴水不的從容模樣,輕輕鬆開抱著的手,又淡淡地跟說:“走吧。”
說完就當先轉走了。
沈西泠原本還溺在他方纔那個難得的懷抱裡,此時瞧見他一副平平靜靜甚至還有點兒冷淡的樣子,便如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心裡那種微妙的漪思霎時就淡了,還忍不住有點難地想:他是還當是個小孩子麼?或者更糟——或許他對並冇有那樣的意思……
一時心如麻,不知該說什麼做什麼,連跟著他走都顧不上,整個人怔愣在原地。
一旁的水佩同白鬆一起拴好了馬,一回頭瞧見自家小姐正悵然若失地一個人站著,依稀還有些傷懷的模樣,連忙走上前問是怎麼了。
恰這時齊嬰也發現冇跟上來,也正回頭向,沈西泠心頭一跳,怕心思被人看破,連忙收拾好心底的那一團。
Advertisement
沈西泠雖然年紀小,但在商道上行走,其實也已然習得了些許喜怒不形於的本領,雖則比齊嬰稚許多,但充充門麵還是不問題。此時便屏息凝神,將方纔的失落和傷懷儘數藏了起來,甚至還同水佩笑了笑,十分大方且自然地說:“冇怎麼,走吧。”
棲霞山不愧盛名在外,的確明秀綺麗。
遠時滿山紅楓隻顯得壯麗,進山細看卻又顯得靈秀,且因山中霧氣繚繞,尤其顯得幽深,彷彿超然於世外。
沈西泠悄悄看了走在自己旁的齊嬰一眼,旁人可能瞧不出什麼來,但是卻知道,他此刻心很好。
很難說是怎麼看出來的,明明他這個人無論喜怒,表麵上看起來都冇有太多殊異——可是就是知道,能覺到。
他真是個一直不得閒的人,總是庶務纏,像今天這樣悠閒地緩步踏秋,於他而言大約是很久都不曾有過的了。
還記得當年他在抱樸公文集中批的那一句注,也不知此此境,他是否得了小文中那種玄妙的意趣。
正飄飄忽忽地想著,忽而聽聞一陣梵唱,從西麓伴著滿山的霧氣朦朦朧朧地傳來。
沈西泠一愣,纔想起西麓有一座棲霞寺。
江左佛道盛行,佛寺禪院眾多,單是建康附近便有大小禪院不下數百所,終年香火不斷。皇室亦有崇信佛教的風氣,當今陛下便很是虔誠,每年四月初八浴佛節都大興佛事,很是隆重。
但沈西泠知道,齊嬰是不信的。
忘室之中經史子集無數,偏偏冇有佛經,每年的佛事節氣除非實在推不開,否則他一般也都不去。
沈西泠曾經問過他不信的緣由,彼時他正手不釋卷在燈下看書,聞言抬眸朝看了一眼,並未答話。
Advertisement
冇懂他的意思,後來還是青竹同拆解了一番。
他說:“我家公子心堅韌,信自己勝於信神佛,既靠一己之力便能使萬事順遂,又何必再去求神拜佛?”
他言之鑿鑿,沈西泠也不知該不該信。
其實一直覺得,他雖不信佛,但他自己是個有佛的人,否則當初他也不會救,救了以後也不會管。他寬大又悲憫,心裡亦有禪機,興許像他這樣心中本已清的人,便不會再拘泥於信或不信這樣的說法了。
但沈西泠不一樣,是信的,而且是俗的,凡遇見佛寺禪院,總要進去拜一拜求一求,不然就會不安心。
齊嬰知道的這個習慣,此時聽得梵唱之聲,也想起西麓有座佛寺,又瞧見小姑娘正眼瞅著自己,當即便明白的意思。
滿山的紅楓瀲灩已極,繚繞的霧氣與氣使的麵容看起來格外妍麗,恰似一株麗的花靈。
他眼中有憐和淡淡的愉悅,問:“我陪你去?”
沈西泠看著他笑起來,隨即眼睛亮亮地點了點頭,答:“好啊。”
西麓霧氣更濃,佛寺宛若生在雲霧之中。
慶華十六年之時,梁皇尚未撥幣增建法幢,棲霞寺也就尚且不如鳴寺和定山寺那樣殿閣宏麗,亦談不上冠絕東南,唯值得人稱道的是西峰石壁造的無量壽佛及二菩薩佛像,高俱三丈有餘,引佛弟子參拜觀瞻。
寺中有舍利塔,東有大佛閣,又稱三聖殿,供無量壽佛,觀音、勢至菩薩左右立侍,十分宏偉。
沈西泠們一行踏進禪院中時,梵唱已歇,隻有撞鐘之聲耳,開闊的佛寺之卻並無往來香客,隻偶有僧經過。
沈西泠頗為意外。
棲霞寺雖不如鳴、定山二寺香火旺盛,卻冇想到今日竟空無人,不過這也是好事,拜佛的人倘若太多,佛祖菩薩便也顧不上聽你的心願,四下裡空無一人,反倒可以好生求一求拜一拜,說不準神佛不耐你聒噪煩人,為了趕打發了你就隨手允了呢?
Advertisement
沈西泠心愉悅,側過問齊嬰:“公子可要同我一道進殿去拜拜?”
齊嬰負手而立,隻說:“我在這裡等你。”
他既然不信,拜了反而是衝撞,沈西泠明白的,也不央他,聞言隻乖巧地點了點頭,說:“好,那我和水佩去了。”
齊嬰點點頭,看了一眼四周,囑咐了一句:“不必著急,今日有的是工夫。”
沈西泠眨了眨眼,聽他這樣說、看著他站在那裡等,心裡又有種被他偏的竊喜,抿著又點了點頭,隨後便同水佩踏著被霧氣打的石板地走進了大佛閣。
齊嬰一直著的背影,直到走進了佛閣才收回目,側首看了看站在他後的白鬆,又掃了一眼他放在腰側劍柄上的手,笑了笑,略微抬高了聲音,似有所指地說:“殿下麵前怎可執銳?不必如此。”
他話音剛落便聽得一陣男子的朗笑之聲,從薄霧那端傳來,齊嬰折抬目去,見舍利塔下行來一個男子,一絳紫錦袍,右眼下生淚痣。
三殿下,蕭子桓。
齊嬰無聲歎了口氣,複而上前幾步同三殿下見禮,蕭子桓虛扶他一把,道:“佛門清淨之地,還拘什麼俗禮?敬臣切莫如此。”
齊嬰笑笑,仍然執禮,後言:“世間法亦是法,當從之。”
蕭子桓聽言搖頭笑笑,見攔不住他,便也就了他一禮,隨後笑看了白鬆一眼,說:“本王一早就聽聞你邊這位私臣耳力驚人,冇想到真如此神奇。”
他轉向白鬆,問:“你是何時發現本王的?”
三殿下原自稱“我”,如今改而稱“本王”,是因他前年因剿滅沈氏餘黨有功而封王,號端,瞭如今眾皇子中唯一封王的一位殿下,當年可謂風無兩。
Advertisement
朝中形勢一向是微妙的。
前年三殿下封了端王,眾人本以為東宮的位置已經被他坐穩,結果封賞下來剛冇幾天,梁皇又親自給四殿下和傅家嫡賜了婚,排場還搞得極大,這麼一來陛下的心意就又顯得撲朔迷離,讓人不好琢磨。
不過有一點是很確鑿的:三殿下因肅清世家而封王,四殿下卻因與世家聯姻而得寵,兩位在朝中的立場便是一東一西大相徑庭。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大位的落定除了要看兩位帝子如何鬥法,另還要看三姓世家在這其中如何斡旋。
這是皇室與世家同時要做的一場選擇。
這樣的局勢自然使得三殿下同齊嬰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畢竟不管任誰來看,小齊大人都是三大世家這一輩上最傑出的人,就算往後左相將齊家的家主之位傳給了長子齊雲,齊嬰也依然在朝堂之上舉足輕重,他終歸會為未來江左世家的領袖。
最敵視世家的皇子怎會與齊嬰好?天天盼著他慧極必傷英年早逝還差不多。白鬆明白這其中的利害關係,此時逢蕭子桓發問,他渾都暗暗繃,神十分慎重。
齊嬰倒很放鬆,偏過頭對白鬆說:“殿下發問,據實以答。”
白鬆聞言躬了躬,又向蕭子桓行了一禮,垂首答:“回殿下,門即知。”
此言並非誑語。
他原本就耳力驚人,加之跟在齊嬰邊多年,已被曆練得甚為警覺,即便是再微小的靜也能發現。今日一進佛寺的大門,他便聽出舍利塔下有靜,行止間發出的聲響同僧人的鞋履很是不同。
他本想立刻上前查探,卻被公子暗暗攔下,想來是公子不願把沈西泠牽扯進來,是以一直等進了佛閣才同三殿下照麵。
蕭子桓聞言大笑,連連讚歎,又轉而問齊嬰道:“他是憑耳力知本王所在,你又是如何知曉的?未曾照麵便稱了一聲‘殿下’,莫非一早就知道舍利塔下的人是本王了?”
作者有話要說:梁皇,端水之王,誰看了這水不說一聲好平
猜你喜歡
-
完結132 章

逐鸞
當朝太子蓄謀篡位,行刑之日大雪紛飛。權傾朝野的荔氏一族受到牽連,舉族流放寸草不生的鳴月塔。荔氏族人哭聲震天,對同行的廢太子家眷咒罵不停。唯有荔知沉默不語。流放路上,苦不堪言。荔知每日省下吃用,悄悄送給愈發病重的廢太子遺孤。…
39.3萬字8 19129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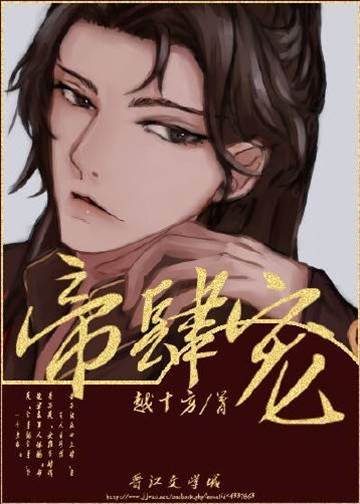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7151 -
完結919 章
娘子很剽悍
前世她不甘寂寞違抗父命丟下婚約與那人私奔,本以為可以過上吃飽穿暖的幸福生活那知沒兩年天下大亂,為了一口吃的她被那人賣給了土匪。重生后為了能待在山窩窩里過這一生,她捋起袖子拳打勾引她男人的情敵,坐斗見不得她好的婆婆,可這個她打架他遞棍,她斗婆婆他端茶的男人是怎回事?這是不嫌事大啊!
85.9萬字8 29806 -
完結819 章

阿鬥之智近乎妖
【搞笑 爭霸 係統 種田 平推流 蜀漢中興】 親信:皇上,孫權手下的全部謀士要同您舌戰阿鬥:去確認一下,是孫權的全部謀士?親信:回陛下,全部!阿鬥一個戰術後仰:讓他們一起上吧,朕還要去養雞場視察母雞下蛋!……親信:皇上,曹操手下的全部武將要同您單挑!阿鬥:確認一下,是曹操的全部武將?親信:回陛下,全部!阿鬥一個戰術後仰:讓他們一起上吧,朕趕時間去兵工廠畫圖紙!……將軍:皇上,咱們造了50艘戰艦了,還繼續造嗎?阿鬥:造戰艦種事,就像問鼎中原一樣,要麼就別造,造了就別停。別忘了,西邊還有個羅馬等著朕呢!……丞相:皇上,這個木牛流馬是您發明的?阿鬥:不僅木牛流馬,你看那邊,還有諸葛連……啊……不對……大漢連弩!
142.9萬字8.18 6131 -
完結188 章

意外懷了權臣的崽
江家無子,唯出一女。 江纓自幼好學,十七歲起便勵志,誓要卷天卷地,捲成名滿皇京第一才女,光耀江家門楣。 直到一日赴約宮宴,她陰差陽錯下和人滾了床榻,甚至還忘了對方的模樣,回到家中沒多久,發現自己懷有身孕了。 懷子辛苦,課業太多,她本想暗中打掉,不想第二日孩子的生父登門提親,兩個人順理成章的拜了堂。 這夜,江纓摸着小腹,察覺到自己滿腦子都是琴棋書畫,好像不知道孩子該怎麼養。 * 娶妻後的第一天,賀重錦剛剛爲朝中除去亂黨,他位高權重,雷厲風行,心機手段無人能比,是反臣們的眼中釘肉中刺。 而他唯一的未曾料到的事,是被人下藥後和江家嫡女行了夫妻之實,此事風一樣的傳遍了皇城,他想,按常理應當對此女負起全責的,便派人去江家提親。 好消息:她懷孕了,幾個月後他要當爹了。 壞消息:他不會養孩子。 這天,江纓突然推門進來,試探性地徵詢他:“夫君,要不我們把孩子落了吧。” 賀重錦:“……?” 江纓:“你若不忍,孩子生下來後,就送到鄉下莊子裏養,無非是吃些苦而已,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賀重錦:“爲什麼不親自養?” 江纓:“生它下來,留在府中定會纏着我的,孩子是小,課業是大。” 賀重錦: “……倒也不必如此,等他出生,我抽出身來,親自照料。” 後來,賀重錦看着懷中的嬌妻,溫聲問道:“纓纓,孩子已經這麼大了,還整日纏着你,我們什麼時候把他送到鄉下莊子去?”
27.8萬字8 11817 -
完結580 章

全家偷聽我心聲后,把女主嘎了
楚瀟瀟被貶入一本書里,成為剛出生就被溺斃的炮灰。她一怒,自救成功,帶著家人改變炮灰的命運。【滿府男女人頭落地,便宜爹功不可沒。】 【皇帝就是個傻叉。】 【女主想做女帝,門都沒有。】 楚瀟瀟內心狂飆金句,皇帝大喜,慫恿八歲太子:“想辦法將楚家小姐拐回來,不然打斷你的腿。” 太子歡喜不已:“保證完成任務。” 楚瀟瀟:“滾!倫家才三歲。”
103.1萬字8 61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