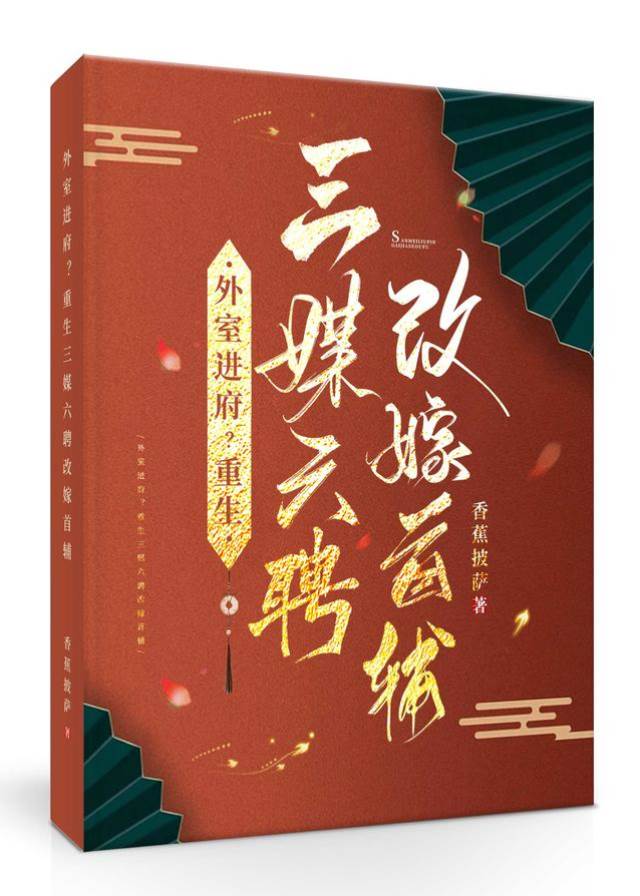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侍君側》 第67章 第 67 章
狩獵的后幾日,獵場收獲頗,但凡參與狩獵的無不是滿載而歸。
深夜篝火,婉淑儀因著孕沒再到場,伶玉理所應當地坐到了婉淑儀的位置上,正靠在帝王的右手邊。
那日帝王離帳到現在都沒與伶玉好聲好氣地說過幾句話,伶玉琢磨不皇上的心思,若是放在尋常人家有個大度的妾室,不知道高興什麼樣,怎麼到了皇上這,反而生起氣來了。
宋才人在宮中得意自是有的家室背景,自淮遠侯一倒,朝中武將以驃騎大將軍宋桐為首。宋桐一連數日狩了滿當當的獵。
李玄翊眼眸淡淡從側落座的子上掠開,視線掃向站著的幾員朝中武將,除卻陳鄲衛宴二人,就屬宋桐前的獵最多的,“這些日狩獵,驃騎將軍倒是收獲不。”
宋桐跪地俯首,“臣藝不,有愧皇上夸贊。”
有皇上這句話,宋才人坐在下首也與有榮焉,紅了紅臉,話道:“嬪妾兄長藝遠不如皇上的羽林衛,皇上快別夸了。”
這句話落,連帶著宋桐角都不了。他知自家妹妹子縱慣了,卻不想如今進了宮子還是這般。
宋桐恭敬地低著頭,未接一句話。
高座的帝王淡淡抿了口茶水,像并未聽見。
伶玉斂了斂眸,心底低低笑了下,宋才人這句話豈不是明擺著說宋桐武藝厲害,堪比皇上親選的羽林衛。能趾高氣揚這麼說的也就只有宋才人了。
因著沒人接話,宋才人后知后覺自己說了什麼,極不自然地咬了下瓣,閉了。
帝王倒底是賞了宋桐。
宋才人憋紅著臉,一回帳就將手中的茶碗摔了出去。
“賤人!”
又白白們看了笑話!
Advertisement
澮沅跪在一旁低著頭,“主子息怒,將軍拔得頭籌,皇上定然是高興的。”
“你當時為何不攔著我說出那句話!”宋才人狠狠瞪了眼澮沅,“蠢貨!”
澮沅早習慣了主子的脾氣,跪到地上連連叩了三下,“主子息怒。”
宋才人眉眼微冷,使勁抿了抿。
……
伶玉想明白了帝王為何冷臉,自然是要去哄一哄。
晚宴一散,天有些近黑了,帝王與幾位朝臣從湖邊回來,就看到了打馬疾馳過來的子。
伶玉手勒住韁繩,眉眼明如畫,低眼時在流水的月華下現出幾分溫。
翻下馬,一騎裝利落颯爽,抱拳屈膝跪地,正正經經對男人道:“屬下參見皇上。”
帝王眼眸瞇了瞇,冷冷嗤一聲,“起來,人看見像什麼話!”
伶玉眸子半嗔,“皇上就會說嬪妾,婉淑儀當初這樣皇上怎的不去說?”
哪能跟婉淑儀一樣。
李玄翊擰了下眉,卻是沒再開口,目在上掠了遍。
宮中人都是極會看眼,寵,尚局自是著,所有料子樣式都是上乘。
譬如眼前這騎裝,他一眼看出來這是西域進貢的緞子。宮中只有兩匹,一匹在皇后那,另一匹賞給了。
這子段好,穿什麼都有種獨有的余韻。伶玉好半天聽不見人說話,自顧起了,眼波猶如流,“皇上可要跟屬下共同騎馬出去轉轉?”
這聲“屬下”聽得男人眼眸一變,捻著玉戒的手指微微用了些力氣。
駿馬飛快,男人手抓著韁繩,懷中擁著子在林中疾馳。
伶玉彎了彎角,慵懶隨意地依偎到男人懷中,眼眸漸漸合了起來。
李玄翊到懷中子的靜,眼皮子低了低,慢慢松下手,駿馬從疾馳變了慢行。
Advertisement
此時天已黑,林中靜謐,借著月尚能視。
馬匹已走了老遠,城東獵場自元昭建朝就是皇帝狩獵之地,周圍防守森嚴,除去林中養的兔鹿,連只野鳥都難以飛進去。
李玄翊并未讓人跟著,只兩人在林中打馬而行。
懷中人的靜越來越小,直到最后地依偎到他懷中,似是真睡過去了。
有一陡坡,馬匹越時的作大了些,將懷中子顛醒。
伶玉睜開眼,馬背上睡覺極不舒服,咕噥兩聲,對著男人的脖頸吹了口熱氣,“皇上,屬下想回去了。”
夜深林寂,因著這聲屬下,男人結緩緩滾了下,此無人,他也不必再抑那些覺。
伶玉困得有些迷糊,巧的鼻尖蹭了蹭男人脖頸,撒般道:“皇上回不去好不好。”
李玄翊握韁繩的手收得愈發得,他沉著眸,故作無事地向后移了半寸,讓那子的徹底離開他的脖頸。
后陡然失重,伶玉不安分地向后錯,小手拄到男人上,尋找著支撐點。
胡的一番作,不想,一下住了男人的某。
與平常不同,這日的石更了幾分。
伶玉一瞬間就清醒了。
對著男人眨了眨眼,看清男人眼底的沉暗,原本想要收回的手又放了回去。
春日衫換得薄,一如初初侍寢時眼神懵懂無辜。
指尖輕著,“皇上……”
此話言又止。
李玄翊黑眸已經徹底暗下了。
為君多年,從未這般放肆過。
馬鞍雖是宮人挑細選的面料,但伶玉子養了多年本就貴,此時在馬鞍上極為不適,下蹭得生生磨出了。
借著月,男人見到那,幾乎失了所有往日克制。
Advertisement
兩人回去已是一個時辰后。
伶玉著雙下馬,玉足剛一落地就坐到了地上。
李玄翊睇著,子眼里已除了淚珠,“皇上,屬下起不來了。”
方才林中,男人啞聲對伶玉耳邊,不只讓稱了自己屬下。在這子面前,李玄翊總能放出男人所有的劣,在那胡作非為。
倒底是有憐惜,帝王彎下腰一手牽住伶玉的腕,另一手搭過的雙膝把人抱了起來。
“下次還敢不敢胡鬧了!”男人冷言冷語。
伶玉委屈,“嬪妾起初只是想與皇上單獨在一起走走。”
誰知后來就變了那樣。
李玄翊干咳一聲,這事確實怪他。
……
婉淑儀因著有孕連連去找皇上,終于將人惹得煩了。福如海也有些厭煩,這婉淑儀仗著懷了皇嗣,一日就要找三四回皇上,但凡皇上不在的帳子就要遣人來上一回。
如此這般,當福如海低著頭再進來時,李玄翊掀了掀眼皮子瞥見他就明白怎麼回事,“婉淑儀又子不適?”
好巧不巧,這日宸貴人也在,福如海訕笑,“皇上圣明。”
話落,伶玉噗嗤一笑,眼眸彎彎,像天上最明亮的月牙,“婉淑儀子不適怕是不適應城東獵場,不如皇上安排人將送回宮,應當就好了。”
福如海一噎,心道宸貴人這句話是把婉淑儀所有路都堵住了,若皇上當真聽了宸貴人的話,那婉淑儀這些心思可都白費了。
果然,帝王聽聞當真點了下頭,“婉淑儀既然子不適也不必留在城東了,安排個太醫隨行回宮。”
福如海汗,不知婉淑儀聽了不知氣什麼樣。
帳里空了人,伶玉在案旁伺候筆墨。
公文理完,帝王正習書練字。
Advertisement
李玄翊時曾師拜云中山人,謀略,詩賦,放眼京城,怕是當朝的文狀元都不能比。極后李玄翊鮮習字,只在幾日休沐時才書上一二。
伶玉在一旁研磨,不懂書畫,只明白好看二字,帝王手書確實與旁人不同,甚是好看。
筆落,伶玉立即亮了眸子,“皇上寫得真好!”
李玄翊眉梢挑了下,面上卻故作若無其事,極尚久,結他的人不,只是沒見到過連奉承都奉承得不走心的。
“寫一個字朕看看。”李玄翊將筆遞給伶玉。
伶玉接到手里,有點猶豫,讀書識字都是當初跟著上小姐上私塾時學的,只是堪學皮,字寫得甚是不好,怕惹得男人笑話。
“嬪妾想起來有事要忙……”說著將要放下筆,男人目涼涼地看向,
伶玉咬咬,“皇上可莫要笑話嬪妾。”
李玄翊朝宣紙抬了抬下。
意思了然。
伶玉磨磨蹭蹭地站到案后,素白的小手拿起筆時輕抖了下,黑的墨落到宣紙上暈染了一片。
微斂起眼,狼毫的尖兒沾了些墨水,在宣紙上輕輕落筆。
筆鋒輕盈細膩,若無骨,握住狼毫的手白皙,指尖纖細如蔥。
伶玉手書了兩字,是宮后改過
的名字。
李玄翊站在后,眸稍沉,這字中帶著一韌勁鋼骨,似是男人的手筆。
他記得,曾經住在上府一段時日,這些書字應是上行所教。
起初他以為不過是小小的宮,無依無靠,只能依賴他。后來他才知曉,有的遠遠比他想想得多,離開了自己,依舊能很好。
念此,李玄翊心中泛出一的波瀾異樣,眼眸倏忽冷了下來。
伶玉遲遲不見帝王開口,以為自己是哪又做錯了,正要說些什麼,男人忽然握住執筆的手,語氣不明,“字太丑,朕教你重新寫。”
伶玉眼看著自己費盡心思寫出的字被一團扔進了紙簍,頗為疼。
……
狩獵的最后一日,宮人拔了營帳準備回宮。
伶玉披著外衫站在帳外正照著暖,正巧看見遠過來的帝王。
聽說昨夜宋才人鬧了一夜,借著子不適的借口最終是把皇上等來了,不過一大早皇上一刻都沒留就出了帳,不知有多人背后笑話宋才人。
伶玉微福了下,角彎著,頗像天上月。
這宸貴人生個好模樣,不論怎樣都是耐看,放眼整個京城也沒人比得過。
福如海心底嘖嘖嘆,昨夜若是宸貴人請皇上過去,怕就是不一樣的結果。
李玄翊一早看見這子笑意盈盈的模樣不知為何擰了下眉,冷著臉點了下頭,一句話也沒多說。
伶玉對男人的冷臉到莫名其妙,微蹙了蹙眉心。
午時設宴,婉淑儀不在,伶玉照例坐到帝王側。
一番敬酒過后,宋桐主請纓進行一番劍舞,宋桐武藝頗為朝中武將敬服,此時不過幾招,已是想起一片贊喝,李玄翊眸淡淡,淺淺抿了口清茶。
“卿好武藝。”
宋桐赦然,拱手道:“臣一兩招數,獻丑了。”
末了,獻武的幾大臣皆得了賞。
幾巡酒水過后,獵場忽起了大風,刮得案上茶碟凌地掉了下去。
隨即耳邊一片混之聲,伶玉尚沒明白發生什麼,一抬眼只見一只箭矢遠遠飛來,
箭尖撕裂空氣,裹挾著凌厲的氣息。
這只箭矢是直沖著高位的帝王來,伶玉手攥,眼眸微,倏然間有了決斷。
想要帝王永遠的寵,永遠的憐惜,而今正是最好的機會。
敗在此一舉。
伶玉倏的站起,面發白,驚恐地喊了聲,“皇上小心!”
驀地,張開雙臂毫不猶豫地撲向了旁的帝王。
……
李玄翊從未有過現在這般的驚惶過,他抱著懷中的子,到那片烏黑的,手輕抖了下。
周圍仿佛被隔絕在外,今日這樁事是他早有預謀,那只利箭他有把握能躲得過去,偏偏這個子……毫不猶豫地護住了他。
倏然間帝王站起,拔的形稍有踉蹌,很快恢復過來淡然冷,只不過凌的腳步出賣了所有被悄然藏下的心緒。
“福如海!馬上讓所有隨行太醫都到大帳!”
在羽林衛羈押宋桐的那一刻,李玄翊咬牙道出了一句話,“留一口氣,給朕狠狠地打。”
李玄翊腳步越來越快,甚至聽不清后的人在說些什麼。流出的是黑的,箭上有毒,懷中的溫度越來越冷。他繃著下頜,嚨狠滾了下。
猜你喜歡
-
完結144 章
海棠閒妻
穿越了,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翻雲覆雨的本事,只想平平靜靜過她的懶日子,當個名符其實的閒妻.然而命運卻不給她這樣的機會,爲了兒子,爲了老公,閒妻也可以變成賢妻!家長裡短,親友是非,統統放馬過來,待我接招搞定,一切盡在掌握.
33.5萬字8 24418 -
完結528 章

快穿之太子再虐你一遍
天界的太子殿下生性風流,沾花惹草,天帝一怒之下,將他貶下凡塵,輪回九世,受斷情絕愛之苦。左司命表示:皇太子的命簿…難寫!可憐那小司靈被當作擋箭牌推了出去,夏顏歎息:“虐太子我不敢……”她隻能對自己下狠手,擋箭,跳崖,挖心,換眼……夏顏的原則就是虐他一千,自毀八百!回到天宮之後……夏顏可憐巴巴的說:“太子殿下看我這麽慘的份上,您饒了我吧!”太子:“嗬嗬,你拋棄了孤幾次?”眾人:太子不渣,他愛一個人能愛到骨子裏。
92.1萬字8 11419 -
完結227 章

戀愛腦暴君的白月光
“你爲什麼不對我笑了?” 想捧起她的嬌靨,細吻千萬遍。 天子忌憚謝家兵權,以郡主婚事遮掩栽贓謝家忤逆謀反,誅殺謝家滿門。 謝觀從屍身血海里爬出來,又揮兵而上,踏平皇宮飲恨。 從此再無鮮衣怒馬謝七郎,只有暴厲恣睢的新帝。 如今前朝郡主坐在輪椅上,被獻給新帝解恨。 謝觀睥着沈聆妤的腿,冷笑:“報應。” 人人都以爲她落在新帝手中必是被虐殺的下場,屬下諂媚提議:“剝了人皮給陛下做墊腳毯如何?” 謝觀掀了掀眼皮瞥過來,懶散帶笑:“你要剝皇后的人皮?” 沈聆妤對謝觀而言,是曾經的白月光,也是如今泣血的硃砂痣。 無人知曉,他曾站在陰影裏,瘋癡地愛着她。
35.1萬字8 491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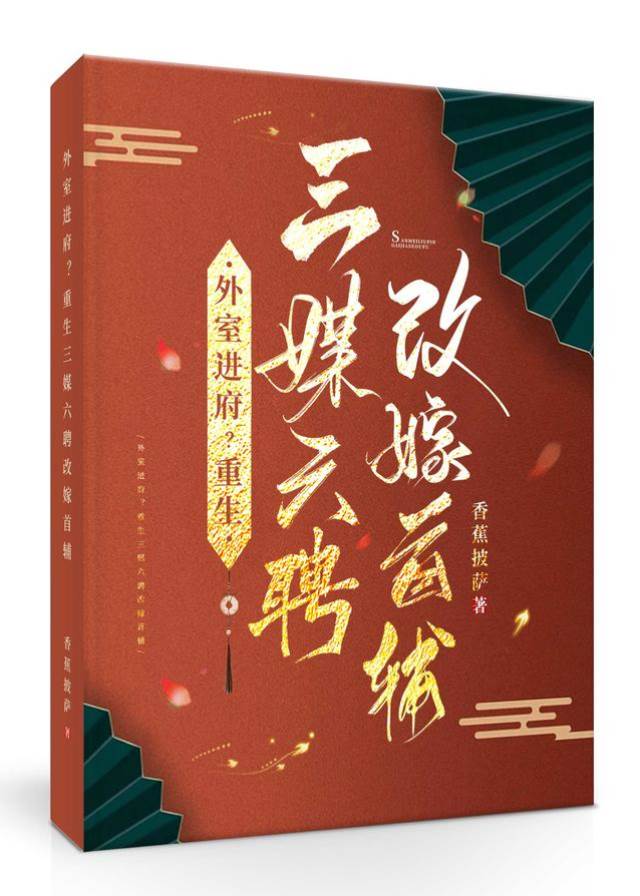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