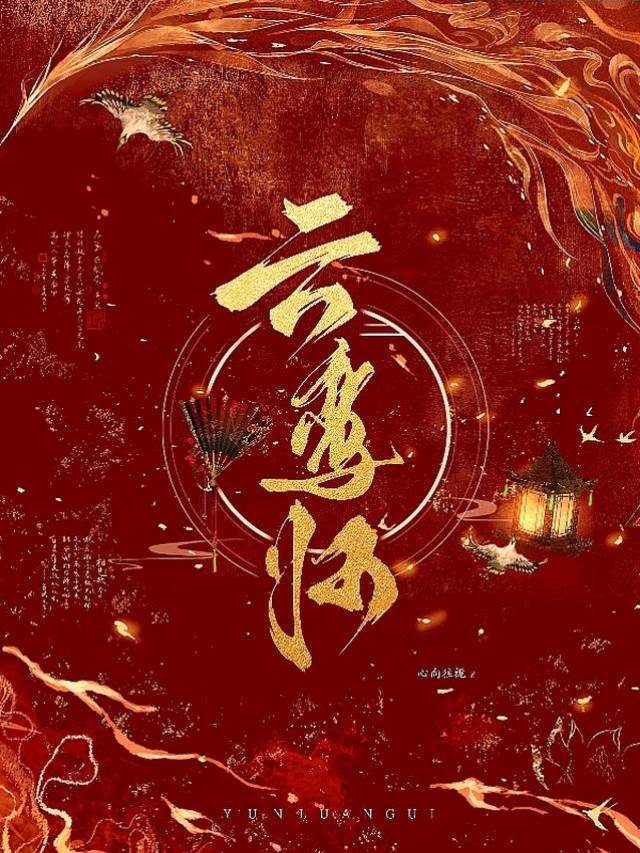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玲瓏四犯》 第45章 第 45 章
***
“要說那位金二娘子, 也是中人,原以為經柳氏這麼一鬧,親事終是要泡湯了, 沒想到金二娘子反倒放了話, 讓侯爺盡快下聘, 倘或敢反悔, 就要打到開國侯府上去。”
姚嬤嬤將聽來的消息一字不全告訴了云畔,彼時正在煎麥冬橘紅水,聽了姚嬤嬤的話,笑道:“好得很, 我果然沒有看錯人。”
檎丹道:“說真的,先前夫人讓嬤嬤遣人去知會那位彭家姑母, 奴婢心里還七上八下呢,擔心們萬一當真鬧到金家去,金二娘子一瞧門第爛了這樣,一口回絕了親事,那可怎麼好。”
云畔說:“我原也是在賭,賭人家有沒有整治妾室的決心, 沒的坑了人家一輩子。現在這樣就很好,我料準了柳氏不會坐以待斃, 只要找到金家門上, 就能試出金二娘子的手段。我這是給人家提個醒, 橫豎家有惡妾,要是不忌憚,狠殺柳氏一回好立威;要是猶豫, 那就說明人家瞧不上侯府, 也只能慨沒有緣分, 趁早再替爹爹下一個。”
姚嬤嬤捂著笑,“哎呀,卻是沒想到金二娘子有這樣雷霆手段,又是打又是捆的,把個柳氏弄得鎩羽而歸,也算替夫人出了一口惡氣。”
“人家是將門虎,不是尋常家子養在深閨的娘子,遇見了柳氏的下作手段也不怕。侯府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執掌門庭,否則再娶一個,反倒生出許多麻煩事來。”云畔說罷,忖了下又道,“回頭我的拜帖,再預備幾件點心送到將軍府上去,請娘子息怒,給娘子驚。”
這就是做人的周到之,這會兒熱絡相見是大忌,雖說那頭已經答應了親事,但還未定準,還未過門,公爵夫人的份在這里,不自矜自重,反失了分寸。古來繼母和繼子之間的關系也是難題,只求讓爹爹有個好著落,自己和繼母之間倒也不必十分親近,只要見了面客客氣氣地,就了。
Advertisement
姚嬤嬤領命出去承辦,到了門上,正遇見魏國公回來,忙呵腰了聲公爺。
李臣簡點了點頭,“夫人在里頭?”
姚嬤嬤說是,“正替公爺預備水呢。”
他聽了袍邁進去,穿過落地罩便見跽坐在涼簟上,面前的小火爐燒得熱氣蒸騰,開了竹筒的小蓋子,拿竹鑷子取奇楠勾加進沸水里去。見他回來了,站起了聲公爺,“我得了上好的化橘紅,煎水代茶飲,對公爺的子有益。”一面走過來,和聲道,“先換了裳吧,過會兒來喝,正相宜。”
李臣簡道好,不過不需手,只說:“你坐,我去換了就過來。”
云畔并不執著,說也好,讓平常侍奉他更的過去伺候,自己仍舊回矮桌前,將水濾出來倒進杯盞里,靜靜等著他回來。
午后的風輕輕吹,竹簾在檐下搖,日過細的間隙,在地上投下一棱一棱的影。
他很快便回來了,換了裳洗了臉,一掃疲倦,在對面坐下來。
牽袖往前推了推,“嘗嘗?”
他端起茶盞抿了一口,是奇楠混著橘紅的奇異香味。
曼聲道:“《素問·四氣調神論》中說春夏養,這個時候調養起來,等日后天涼,公爺的咳疾發作起來,就不會那麼利害了。”
他聽了淺淺出一點笑,“讓夫人費心了,不過這飲子,恐怕得過幾日才能再喝了。今日朝堂上,家又有兵馬調,我之前管轄的息州廂軍,要調三劃盧龍軍,我明日就得啟程去息州,這一去恐怕要十來日。”
云畔聽了,微微一怔,“要將息州廂軍劃盧龍軍?盧龍軍不是三位國公率領的……”
很聰明,已經悟出了兵權多番調背后的原因。三位國公家一個都不信任,幽州離上京很近,盧龍軍壯大起來,就能與侍衛司、殿前司、天德軍分庭抗禮,不論哪一方有異,盧龍軍都能以最快的速度進京勤王。
Advertisement
李臣簡臉上依舊淡淡的,垂著眼,為各自杯中添上水,低聲說:“我心里有數,夫人不必擔心。”
只要有他這一句,云畔就覺得自己確實是不需要瞎心的了。
男人宦海沉浮,朝中風向隨時會變,真要去擔心,那這輩子都得在戰戰兢兢中度過。家有他的平衡之道,當臣子的安分守常之余,未必沒有自己的退路和對策。李臣簡是個心中有丘壑的人,他不會同你代太多,因為多說無益,他只要讓放輕松心思,照樣過恬靜的閨中歲月,自己在外應付,就沒有后顧之憂了。
“回頭我替公爺收拾換洗的裳。”云畔悵然說,頓了頓又問,“是騎馬還是乘車呢?這麼長的路,馬背上顛簸只怕子不住。”
他聞言一笑,“我這子并不像外人謠傳的那麼弱,夫人應當知道的。”說罷又覺得自己輕浮了,忙又正了正臉,“盛夏時分沒有那麼嚴重,得等了秋,舊疾才會慢慢浮現出來。”
云畔還是面得很,聽他約打趣,臉上就浮起紅云來。只是不想讓他暗地里笑話,訕訕低下了頭,好半晌才道:“帶上辟邪和辟寒,有他們照顧,公爺在外也滋潤些。”
他道好,“我在息州任了五年團練使,那里一應都是現的。”
嗯了聲,又道:“要十來日呢,一下子去那麼久……”
新婚還沒滿一個月,這一去倒要去十日,他從微微嘆惋的語氣里發現了一點不舍,心里沒來由地一陣溫暖。以前好像從來沒有這樣過,雖說母親在他每次出門前也是千叮嚀萬囑咐,但那時年俠氣,躍馬揚鞭說走就走,似乎并沒有太多眷。如今了親,有了家累,也許這家累里僅僅只是多了這麼一位年輕的夫人,卻也讓人有些放不下,甚至生出一點惜別之來。
Advertisement
然而不便表達,也不知怎麼表達,他轉過頭看向窗外,檐下日大盛,假山都白得反,他說:“十日一下子就過去了,這期間夫人可以上舒國公府瞧瞧梅娘子,父親的新邸也得籌建,你在上京,或許不比我在息州輕省。”
倒也是,云畔笑起來,“我好像每日都很忙,鋪子已經打發人修繕了,五間門面呢,是刷墻就要好幾日。”
笑的時候,給人一種分外安定和舒稱的覺,小小了梨渦,彎彎的眉眼,他心里的霾也跟著散了一半,溫聲道:“息州最出名的就是石青和石綠,到時候我命人采買些,給你帶回來。”
說好,想了想又道:“化橘紅還是得常飲,回頭我包上一包給辟邪帶著,外頭煎水不方便,就和麥冬一起泡茶喝吧,滋味兒雖寡淡些,有藥就了。”
后來替他收拾要帶出門的東西,從裳到鞋子一應都準備得很妥帖,甚至多預備了幾雙足和兩頂發冠。
辟邪大包小包地將包袱放上馬背,心想這就是婚后出遠門的待遇啊,有位夫人仔細幫著料理,臨行還送到閥閱底下,再三再四地叮囑他們,一定要照顧好公爺。
李臣簡翻上馬,深深看了一眼,仰著臉著他,那清澈的眼波里倒映出他的影……他笑了笑,“回去吧!”看多了不免生出兒長,便毅然拔轉馬頭,揚鞭往直道上去了。
云畔目送他走遠,這炎熱的天氣,地面被熱浪席卷,空氣扭曲著,漾著,人像走在火堆上似的。
“息州離上京有兩百里遠呢……”喃喃地說。
小夫妻分離總不免生出愁緒,姚嬤嬤笑道:“一路上有好些茶寮,還有驛站,公爺累了自會歇息的,夫人不必擔心。”
Advertisement
云畔難為地笑了笑,“是我多慮了。”方轉返回府門。
送走了人,茫然也不知該做些什麼,呆坐了好半晌才想起來,爹爹的事是不是該去知會姨母一聲。聘禮讓柳氏預備,不知又會弄出什麼幺蛾子來,家中實在沒一個當事的人,終究還得自己過問。
只是如今出了閣,一舉一都得問過婆母和祖母的意思,便上茂園去,再請們的示下。
李臣簡出發前,來園子里請過安,兩位長輩念著他們小夫妻依依惜別有很多話要說,因此并未出來相送。送雖沒送,但也朝外張著,見云畔到了廊下,王妃便站起問:“忌浮出發了麼?”
云畔說是,“所需的東西都籌備好了,有辟邪和辟寒跟著,祖母和母親就放心吧。”
可是里說著,心里卻有些放不下,真是好奇怪,從來沒有這麼惦念過一個人,他才走,就盤算著該什麼時候回來了。
王妃瞧出眉間有愁,笑道:“他早年在軍中,一去就是七八個月,也是這麼過來的。后來因了一回傷,家恩準回上京來供職,如今偶而往息州去一次,幾日便回來了。”
云畔點了點頭,笑道:“我是瞧天太熱了,怕這樣大日頭底下奔波,萬一中了暑氣怎麼辦。”
小輩恩,總是長輩最樂于見到的,連太夫人也來寬,“男人家,多歷練歷練沒什麼。早年你外祖母還在大夏天點兵呢,李家的子孫沒有拈輕怕重的,這麼點苦都不了,將來還指他有大出息嗎。”
云畔和王妃都笑起來,王妃道:“他們小夫妻,婚后頭一回別離,難免要牽腸掛肚。”復又問云畔,“侯府里預備起來沒有?這事耽擱不得,過了這個村,可就沒這個店了。”
云畔說是,“我來正是要同祖母和母親商量,過會兒想去姨母家一趟,讓姨母幫著料理這件事。昨日我爹爹那妾室登了將軍府的門,胡攪蠻纏一氣,被金二娘子綁起來吊在了涼亭底下。本以為這門婚是不能了,沒想到金二娘子竟催促我爹爹過禮,我聽了,心里的大石頭才落了地。”
太夫人和王妃面面相覷,王妃道:“這妾室也太放肆了些,算哪塊名牌上的人,敢闖到人家門上去?”
太夫人哼了一聲,“這等市井潑婦,仗的就是不要臉,正經人家的姑娘怕了,可不就讓得了勢,縱是將來過門,主母也在手心里。”話又說回來,端的是敬佩金二娘子,“沒想到金至真的妹子竟有幾分俠義心腸,想是見侯爺太不容易了,反倒愿意過這個門,替侯府重整家業。”
云畔說是,“我心里也很激,早前很怕家中的況人家不了解,貿貿然婚拖累了人家。”
所以后來有意讓人把消息傳到那個妾室耳朵里,好讓上門去鬧,趁著未定親,金勝玉看清侯府現狀。
王妃那日說合回來,就聽吩咐陪房去知會什麼姑母,當時沒太在意,眼下前后一聯系,總算明白了的苦心。能全盤控,又不失善心,不會有意坑騙無辜的人趟渾水。這樁婚事到底是愿者上鉤,若是金勝玉不樂意,趁早,將來也不至于懊惱,怪人哄上當。
王妃如今對這媳婦是沒什麼挑揀的了,小小年紀心思縝,實在是家門之福。轉頭對太夫人道:“這種人難得,人家既發了話,要是再拖延,人說不誠心,倒不好了。”
太夫人也緩緩點頭,“那你就去吧,自己父親的事,自己不心,還有誰來替你心。如今金家和那小妾撕破了臉,再讓妾室預備君的聘禮,也著實不事。”
云畔站起納了個福,“那我就去了,多謝祖母和母親,我一定趕在夜前回來。”
王妃頷首,“若是有什麼要幫忙的,只管打發人回來傳話。”
猜你喜歡
-
完結480 章

穿書之沒人能比我更懂囂張
––伏?熬夜追劇看小說猝死了,她還記得她臨死前正在看一本小說〖廢材之逆天女戰神〗。––然后她就成了小說里和男女主作對的女反派百里伏?。––這女反派不一樣,她不嫉妒女主也不喜歡男主。她單純的就是看不慣男女主比她囂張,在她面前出風頭。––這個身世背景強大的女反派就這麼和男女主杠上了,劇情發展到中期被看不慣她的女主追隨者害死,在宗門試煉里被推進獸潮死在魔獸口中。––典型的出場華麗結局草率。––然而她穿成了百里伏?,大結局都沒有活到的百里伏?,所以葬身魔獸口腹的是她?噠咩!––系統告訴她,完成任務可以許諾...
86.1萬字8 11706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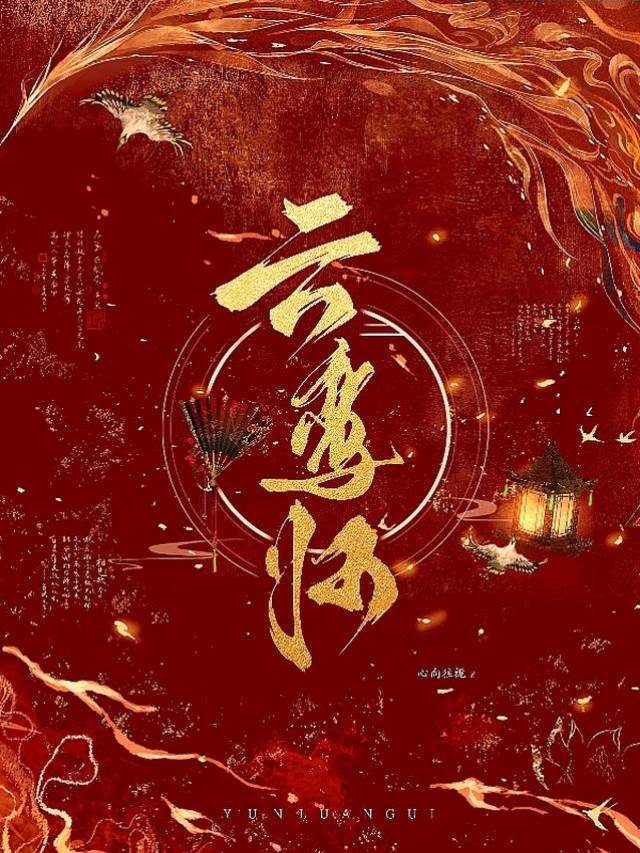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