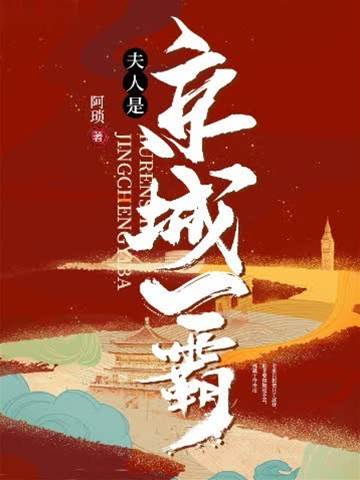《我家賢妻太薄情》 第110章 續章
開年之后,皇上立皇長孫為太子,并大赦天下。正逢清明,因這大赦,文武百沐休時間加長至七日,又是春暖花開,人人便計劃著外出踏春。
駱晉云自軍機閣回來,一把抱了在院子里喂金魚的寶珠,問道:“你娘呢?”
寶珠指了指正房,回答:“和姑,說話。”
駱晉云抱著寶珠進門去,駱家小姑姑果然和薛宜寧一起坐在里面,見了他,連忙起問候,然后笑道:“你們家寶珠,真是越長越好看呢,將來還不定是個怎樣的大人。”
駱晉云頗有些自得道:“那是自然。”
說完,用手背了兒的臉頰。他的手長年握刀槍,手背比手掌許多。
小姑姑笑言兩句便離開了,薛宜寧和他道:“真是的,哪有你這樣順桿爬的?你就說小時候好看,長大了也說不準。”
“那自然是更好看。”駱晉云大言不慚道,說完問寶珠:“寶珠說,咱們長大了是不是更好看?”
寶珠也不知聽明白了沒,就點點頭:“是。”
薛宜寧拿他沒辦法,無奈地笑。
駱晉云問:“姑姑找你做什麼?”
薛宜寧說道:“他們家二郎不是訂親麼,有些京里的禮數拿不準,所以來問問我。”
并非是京里的禮數拿不準,而是大戶人家的規矩不知道,所以才來問。嫁來駱家兩三年,便辦了栓兒的滿月酒、周歲禮,雖有不悉之,但好在沒有大錯,到駱晉雪出嫁這樣的大事,也一力辦下來了,讓駱家各房長輩心服口服,遇到拿不準的,也會來問。
駱晉云點點頭,帶著幾分喜道:“今日我與定遠侯比騎,贏了他家中那匹純白的蒙古馬,他說了,明日就讓人給我牽來,這馬便送給你了,清明帶你去東郊騎馬怎麼樣?”
Advertisement
“真的?”薛宜寧自是歡喜,純白的馬極其稀有,上次見到一匹白青雜的馬,都覺得風采驚人,若是純白的馬,那該是怎樣的超群出眾?
駱晉云道:“自然是真的,你不是一直想騎馬麼?”
薛宜寧還在高興著,卻不知想起了什麼,又蹙起了眉頭。
他問:“怎麼了?”
薛宜寧低聲道:“可我,月信已經晚了半個月了。”
“那……是很嚴重?”駱晉云擔心道:“找大夫來看看?”
薛宜寧知道他沒聽出來,無奈道:“我月信一向是準的,我怕是……有了。”
駱晉云一怔,這才反應過來,驚喜道:“那肯定是,那就別去騎馬了!”
說完一把放下寶珠,看著不知怎樣才好,想了想,將自己坐椅上的靠墊遞給,說道:“凳子,你靠著,要不然……去躺著?”
薛宜寧好笑地將靠墊給他扔回去:“躺什麼躺,這才什麼時候。”說完,又遲疑道:“再說,還不知道是不是呢。”
駱晉云卻早已揚著角,忍不住傾了小腹,篤定道:“自然是的,要不然還能是什麼?或者,明日找大夫來看看?”
薛宜寧搖搖頭,“不用,等一等再說,你先別說出去。”
駱晉云只是笑,似乎覺得太過謹慎。
等到晚上,他又將手探了過來,薛宜寧便說道:“還是小心些吧,下午你才說,肯定是有了。”
駱晉云一頓,隨后才在耳邊哄道:“我兒子生得結實,不會有妨礙的。”
“瞎說,下午還讓我去躺著呢。”回。
他雖是有些不愿,卻還是深吸一口氣,將手從襟拿了出來,只抱住。
問:“就算真有了,也不一定是兒子。”
Advertisement
“那便再生個珍珠,與寶珠做伴。”說完,他看著,認真道:“你別想那麼多,再有個像寶珠似的小兒,又有什麼不好?母親若念叨,自有我去應對,弟妹敢在你面前說三道四,你便罰月銀,不用顧忌母親。”
薛宜寧笑道:“知道了。”
說完,往他懷里靠了靠。
但凡是人,特別是像這樣,進門五年還沒有生下男孩的,難免有些力,有他這些話,的確能放松很多。
這一次清明,沒能出去騎馬,但薛宜寧確實得了匹渾雪白的駿馬,很是心,將它養在馬廄里,只恨眼下不敢騎。
半個月后,已有些害喜癥狀,便請來了大夫號脈,果真是喜脈。
駱晉云早有心理準備,但得知真是有喜了,便什麼都慎重起來,自己親自拿了后院的賬本,將金福院一個院子里的吃穿用度開銷從一個月三百兩提到了六百兩,比老夫人院里還多出二百兩,讓薛宜寧立刻就否決,只讓提到比老夫人院里差一些。
駱晉云無奈,便問:“我上次給你的俸銀呢?那是我自己的錢,總可以拿出來吧?”
薛宜寧一笑,抿抿:“那個,被我放起來了,你不是說,給我了就是我的麼,已經不算你的了。”
“意思是,你不拿出來?”他問。
點點頭。
說完笑道:“錢在我自己手上,還怕我不會買東西給自己麼,再說三百多兩的用度,也夠了。”
駱晉云無奈,因為他發現錢不在自己手上,就只能聽安排。
他懶得管錢,就將每月拿到的俸銀都給了,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要錢,還不給。
頓了半晌,他說道:“那你自己拿錢補自己,母親那里省慣了,你不用遷就。”
Advertisement
說道:“懷孕也不用吃得太好,之前的穩婆和我說了,就是寶珠出生瘦小,我生產才那麼順利,若是頓頓魚,多吃,那反而還不好。”
“是麼?”駱晉云不愿相信。
他聽說寶珠出生小得像只貓兒,便覺得是在孕期憂心勞力,大著肚子還要替駱晉雪安排婚事,這才沒養好,到這一胎,他在邊,絕不能再這樣,沒想到卻聽到這一番歪理。
見他似乎不信,薛宜寧回道:“當然是的,穩婆說,曾接生的一家做屠戶生意的,家中夫人懷孕后頓頓大魚大,后來臨盆時難產,大人小孩都沒救過來。”
駱晉云心中一怔,連忙答應愿意怎樣就怎樣,不再說這個話題,他不愿細想。
等到年底,將要臨盆的那個月,他便開始擔心起來。
可恰在這時,又按習俗,要搬離正房,去側房休養待產,不能與他待在同一間房了。
寶珠被娘帶著睡著西廂房,便搬去了東廂房,順便又將他放了些在和正堂,金福院如今人多,若他想清靜,去那里過夜也好。
結果他不知從哪兒拿出幾十兩私房錢來,塞給了老夫人派來金福院照料的媽媽,然后每日夜,先去正房歇下,等夜深,便過來側房睡。
有時他作輕,直到早上醒來才發現邊多了個人。
冬月底,薛宜寧順利分娩,產下一名男嬰。
長房嫡子,也是駱家下一任家主,份自是非同小可,孩子在夜里出生,老夫人天未亮,就親自到了金福院。
彼時駱晉云還在產房中待著,收了他錢的媽媽聽說老夫人來了,連忙就讓他先出去,怕被老夫人知道了責怪,他便替薛宜寧拉了被子,從床邊站起,薛宜寧倒一把拉住他,在他耳邊小聲道:“我不想讓孩子柱兒,不好聽。”
Advertisement
駱晉云笑了笑,朝道:“還記得這事呢,好好休息,能睡就睡會兒,我去去就來。”
他出去了,正房中傳來老夫人逗弄小孩子的聲音。
累了一夜,薛宜寧也確實困了,躺著躺著,便睡了過去。
再醒來時,駱晉云又在床邊,朝道:“醒了?”
產房怕風冷,封得嚴實,看不出外面天,問他:“什麼時候了?”
他回答:“是下午,孩子也睡了,就在隔壁,要看看麼?”
點點頭。
駱晉云起去隔壁將才出生的兒子抱了過來。
他雖已有了寶珠,卻從未抱過這麼小的嬰兒,樣子顯得格外小心。
到床邊,他將孩子輕輕放了下來,說道:“母親說,長得像我。”
薛宜寧笑:“母親覺得每個孩子都像你。”
說完問:“名定了嗎?”
駱晉云道:“沒有,母親如今不想孩子柱兒了,因冬天冷,孩子易生病,怕難養,所以要取個賤名,狗兒,我自然不能同意。還有什麼豬兒牛兒的,都不可能。”
薛宜寧笑,問他:“那你想什麼?我之前說的,你又不同意。”
駱晉云看著道:“不著急,等你休息好,我們一起慢慢想。”
說著,輕鬢邊的頭發,盯著不說話。
問:“怎麼了,這副樣子?”
頓了頓,他才說道:“我想問,你之前那避子的藥,在哪里弄的?”
薛宜寧不知道他怎麼提起這事,莫名道:“你說什麼呢!”
他連忙說道:“昨夜我守在產房外時,一直在想,如果這個孩子平安落地,我就再不要孩子了,所以就想,有沒有那種給男人喝的藥,不傷本,又能避子?”
薛宜寧被他逗笑:“別人都要百子千孫,你就要一個兒子?”
他沉聲道:“上天給我的夠多了,一兒一,足矣。”
因為心滿意足,所以不敢多要,怕上天怪自己太貪心。
知道他是因昨夜生產而心有余悸,笑道:“戰場上走出來的人,竟這麼膽怯,我才不要一兒一,我母親生了三個,婆婆也生了三個,我至也要三個吧?”
“你……”他無奈,“你心倒寬。”
“再說,萬一別人賣你藥時告訴你不傷本,結果傷了呢,你怎麼辦?”問。
駱晉云的臉頓時黑了下來,逗弄功,看著他笑得像個小姑娘。
猜你喜歡
-
完結45 章

繁花落盡暮白首
仙霧之下,九州之上。她身為九天神女,一血誅盡天下妖魔,一骨盪盡九州魑魅。但她身為天妃,卻被自己愛了千年的男人一休二棄三廢,直至魂消魄散。「帝旌,如有來生,願不識君……」
4.6萬字8 7157 -
完結572 章
回眸醫笑:逆天毒妃惹不起
她,二十一世紀頂級醫學女特工,一朝重生,卻成了大將軍府未婚先孕的廢物大小姐。渣爹不愛?渣姐陷害?沒關係,打到你們服為止!從此廢物變天才,絕世靈藥在手,逆天靈器隨身,還有個禦萬獸的萌娃相伴,風華絕代,震懾九荒,誰敢再欺她?可偏偏有人不怕死,還敢湊上來:「拐了本王的種,你還想跑哪裡去?」納尼?感情當年睡了她的就是他?某王爺十分無恥的將人帶上塌:「好事成雙,今夜我們再生個女兒給小白作伴。」
98.1萬字8.18 45505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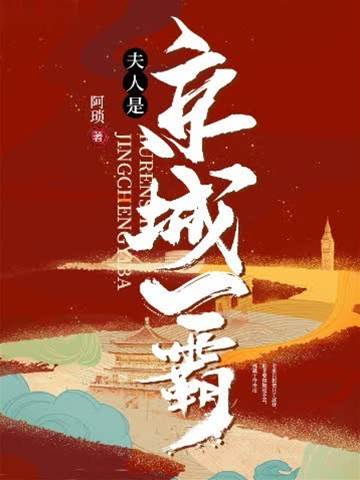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209 章

云鬢楚腰
陸則矜傲清貴,芝蘭玉樹,是全京城所有高門視作貴婿,卻又都鎩羽而歸的存在。父親是手握重兵的衛國公,母親是先帝唯一的嫡公主,舅舅是當今圣上,尚在襁褓中,便被立為世子。這樣的陸則,世間任何人或物,于他而言,都是唾手可得,但卻可有可無的。直到國公府…
68.7萬字8 26115 -
完結698 章

神醫娘親她特會講理
她來自中醫世家,穿越在成親夜,次日就被他丟去深山老林。四年里她生下孩子,成了江南首富,神秘神醫。四年里他出征在外,聲名鵲起,卻帶回一個女子。四年后,他讓人送她一張和離書。“和離書給她,讓她不用回來了。”不想她攜子歸來,找他分家產。他說:“讓出正妃之位,看在孩子的份上不和離。”“不稀罕,我只要家產”“我不立側妃不納妾。”她說:“和離吧,記得多分我家產”他大怒:“你閉嘴,我們之間只有死離,沒有和離。”
121.9萬字8 162108 -
完結184 章

紅酥手
蕭蔚看着爬到自己懷裏的女子無動於衷:餘姑娘,在下今晚還有公文要審,恐不能與你洞房了。 餘嫺抿了抿嘴脣:那明晚? 蕭蔚正襟危坐:明晚也審。 餘嫺歪頭:後夜呢? 蕭蔚:也要審。 餘嫺:再後夜? 蕭蔚:都要審。 餘嫺:我明白了。 蕭蔚:嗯……抱歉。 餘嫺笑吟吟:沒事。 蕭蔚疑惑:嗯? 餘嫺垂眸小聲道:白天? 蕭蔚:?(這姑娘腦子不好? 爲利益娶妻的腹黑純情男x爲真愛下嫁的天真軟萌妹 簡述版: 男主:對女主毫無愛意卻爲利益故作情深,作着作着走心了 女主:對男主頗有好感卻因人設假裝矜持,裝着裝着上癮了
29.2萬字8.18 42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