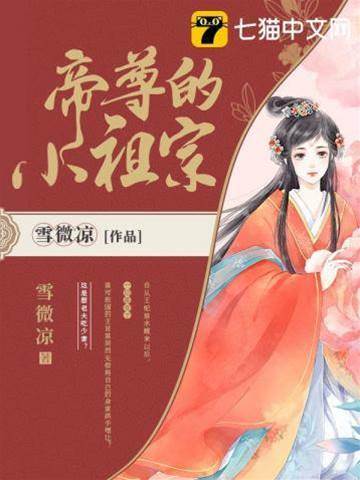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九盡春回,十里錦繡》 第三卷:君胡不歸 第312章 丞相府的秘密1
上靖羽獨自一人走在漆黑的江邊小道,神有些麻木,說得輕鬆說得何其鏗鏘有力。可是若真的眼睜睜看蕭東離死,捫心自問,自己做不到。
可若不說得這般決絕,一如今日般的糾纏,將會無止無休。
一個人走著,沒黑暗中。
站在那裡,著波粼粼的江水,神有些悵然的朝著江邊走去。心裡的不安,若堆砌的城牆,他一日不歸,一日難安。
「喂,江水太冷,死相太慘。」一雙手驟然扣住了的胳膊。
上靖羽一怔,瞬時回頭,黑暗中看不清千寂的表,卻能聽得出他腔調中的微。他拽進的胳膊,好似一鬆手,真的就會跳江自盡。
「你以為我會自盡?」啞然一笑,「他沒回來,我怎麼捨得死?不管發生什麼事,也不管二皇子會怎樣對付我們,我都要等著他回來。等不到他回來,我就去給他收。這是最壞的結果,再壞——又能壞到哪裡去呢?」
生在一起,死在一,此生何憾?
能覺到千寂的手,忽然加重了力道。
眉心微蹙,上靖羽吃痛的撣落他的手,「你放心,我會很好。既然你來了,那就送我回去吧,天太黑,我一個人回家有些害怕。」
千寂低低的應了一聲,跟在的後,往相府的方向走去。
蕭東銘知道不肯去二王府,所以選擇這樣一個地方想要談一談。卻忘了,他們之間,早已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
道不同不相為謀。
人不同不相為伍。
彩兒從天而降,定是素言實在沒辦法才放出了彩兒。彩兒因為有劇毒,尋常也不敢讓它隨意飛,萬一傷到人便不得了。是故回到東都,彩兒便被素言束住了翅膀放在袖子里隨帶著。
Advertisement
果不其然,不多時,素言便驅著馬車找了過來,見著上靖羽的一剎那,素言險些哭出來。
「小姐怎樣?傷著沒有?二皇子有沒有對你怎樣?」素言急忙拽著上靖羽四查看。
上靖羽一笑,扭頭瞧了一眼站在肩頭的彩兒,「我沒事。」
素言點了頭,這才如釋重負,「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有我在,誰敢傷?」千寂嗤鼻,「你未免也太小看我。」
「自我覺良好是不是?有本事你一開始就攔著二皇子,不就什麼事都沒了?」素言可是一肚子火,二皇子半路劫人真不地道。
「好了,回去吧!」上靖羽不想再計較追究。
素言點頭,小心的攙了上靖羽上車,臨走前沖著千寂扮了鬼臉,「你最好在二王府門前擺個算命攤,看你那樣子,就是個半道出家的主,做什麼都不靠譜。你要是能隨時準備攔住二皇子,我就激你,激涕零!」
千寂瞪了一眼,「你才算命。」
音落,素言已經驅車離去。
車,上靖羽淺淺一笑。
事實上,有些事不是你不想追究,就可以當做什麼都沒發生過的。因為很多事,發生了就是發生了,發生在不經意之間。
就好比蕭東銘的傷,是真的傷了。
上靖羽不知道的是,那一夜的二王府,請來了宮中醫會診。至於真實結果如何,就無人得知了。
宮裡宮外,對此諱莫如深。
護國將軍府,年玉瑩快速邁步,進了年世重的房間。卻見年世重正在執筆揮毫,也不知在寫些什麼,當下遲滯了一下。環顧四下,見著四下無人,這才道,「暮雲,二王府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案前的人徐徐抬頭,不冷不熱道,「消息倒是很靈通,可見你是上了心。」
Advertisement
「二皇子怎麼了?」年玉瑩問。
他緩步走下來,眼角眉梢微抬,「生外向,果然是真的。才這麼點功夫,就已經胳膊肘往外拐了?」
聞言,年玉瑩面一沉,「不是你非要讓我嫁給二皇子的嗎?」
「是啊,你不嫁給他,我這孩子如何能登上太子之位呢?」暮雲冷笑兩聲,「你瞧瞧外面的天。」
年玉瑩冷然,「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好端端的,關天什麼事?」
「風雲巨變,快要變天了。」暮雲輕嘆一聲。
音落,年玉瑩心頭一怔,「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很簡單,我會儘快上奏,讓你與二皇子完婚。為免夜長夢多,這段時間你就不要出門了。」暮雲雙手負后,立於窗下。
年玉瑩拂袖就走,想了想又頓住腳步,「我哥的後事,你是如何置的?」
「你想做什麼?」暮雲扭頭看,容平靜無奇。
「我就這麼個哥哥,就算他死了,我不能為他做什麼,清明將至,給他上柱香總是應該吧?」年玉瑩咬牙切齒,紅了眼眸。
暮雲輕笑兩聲,「人都死了,做給誰看?」
「做給老天爺看。」年玉瑩狠狠盯著他,「這世上,善惡有報。」
「你說我惡有惡報?」暮雲挑眉。
年玉瑩嗤笑兩聲,「天知道。」
暮雲點頭,「是啊,天知道。殺的人多了,也就麻木了。早就忘了所謂的善惡報應,想想那些年死在沙場上的軍士們,不也都是死得冤嗎?人活著,總希冀老天爺給個報應,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哥哥葬在哪?」年玉瑩哽咽了一下。
「隨手埋了,天知道在哪。」暮雲冷了聲音,「滾出去。」
年玉瑩咬,快步離開。
手,輕輕上自己的小腹。想著這些日子一來自己遭的凌.辱,想著後院那些姨娘的死狀,想著從前的將軍府,想著回不來的年世重。
Advertisement
眼淚不爭氣的滾落,這世上,如今唯一值得期許的,便是二王府。
只要嫁到二王府,藉助暮雲的手,扶植二皇子登位。到時候母憑子貴,等二皇子做了皇帝,一定可以讓二皇子殺了暮雲。
那麼這個孩子的,就會為永恆的,永遠都不會被人知道。
而到了那時,才算真正的周全。
暮雲站在窗前,心腹快速進門,「將軍。」
「二王府什麼況?」他問。
心腹道,「也不知是什麼況,只說昨夜有醫前往診治,不知是二皇子還是府中人。」
「昨晚,二皇子跟誰接過?」暮雲復問。
聽得這話,心腹似乎想起了什麼,「好似半道攔了一輛馬車,下來的是個子。因為隔得遠,屬下等不敢靠近,所以沒看太清。將軍吩咐過,盯二皇子,所以——誰也沒注意那名子。」
暮雲駭然蹙眉,「子?什麼樣的子?」
心腹不知該怎麼形容,只說了那子的高。
「穿素?」暮雲問。
心腹連連點頭,「姿曼妙,直接上了二王府的馬車,而後去了江邊與二皇子相見。」
「後來呢?」暮雲袖中握拳。
心腹想了想道,「後來好似不歡而散,該子自己走回去的,二皇子並未相送。屬下記得,此後二皇子便是被人攙出亭子,好似了傷,但隔得遠,倒也看不出有什麼外傷。只是覺得虛弱,是被托上馬車回府的。」
聞言,暮雲低笑兩聲,竟然帶著幾分冷的蔑笑,「那子慣來如此,下去吧,繼續盯著二王府就是。」
心腹頷首,隨即退下。
提筆新墨寫摺子,趁著邊關戰事未起,早點讓年玉瑩與二皇子完婚,這事早了早好。彷彿心不錯,暮雲面帶喜。
Advertisement
寫完了摺子,給底下人送宮闈,一眨眼誰都找不到暮雲去了何。
今日下著濛濛細雨,清明時節雨紛紛。
清明將至,雨也開始細細的下著。雨風微涼,撲面而來更是涼的心。
回到家,自然是第一時間去見父親上。
早前因為回來得急,又帶著郡主,上靖羽便讓管家帶了個信。管家道,相爺這段時日修養,整日在祠堂旁的小佛堂里禮佛,不見任何人。
「哎,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嗎?」蕭玥問,「畢竟,是我把你帶出去的,我該跟你爹解釋解釋才好。」
「我爹——早就明白我是將計就計,郡主放心就是,畢竟是父,他不會對我怎樣的。」上靖羽深吸一口氣,「你要是覺得無聊,可去街上逛逛。」
蕭玥點了頭,「那我出門逛一圈,你若有事,讓素言速速來找我。我是郡主,你爹不敢拿我怎樣。」
上靖羽含笑,「知道了,郡主。」
語罷,上靖羽小心的走進了祠堂。
祠堂靜悄悄的,除了指定的清掃奴僕,其他人是不許進的。因為下著雨,屋檐上的水滴吧嗒吧嗒的打在地上,撞出一朵朵沁涼的水花。
上靖羽拎著擺走在迴廊里,穿過長長的迴廊,走到了祠堂一側的小佛堂外頭。
佛堂里燃著長明燈,淡淡的檀香從門裡出來。因外頭的雨霧,香氣變得有些清涼,讓人無比心安。
深吸一口氣,上靖羽輕輕推開了門。
靜謐的佛堂,明燈因為風吹而左右搖曳。
關上門,腳步輕的走過去,佛龕前,跪坐著虔誠的教徒,輕輕誦讀著泛黃的經卷。他的聲音很輕,但很練,可見這卷經書,他已爛於心,早已讀過千百遍。
上靖羽愣在那裡,從不知道,爹也有如此靜心的時候。
摒棄一浮華之氣,就如尋常人一般,虔誠誦讀,長跪不起。
猜你喜歡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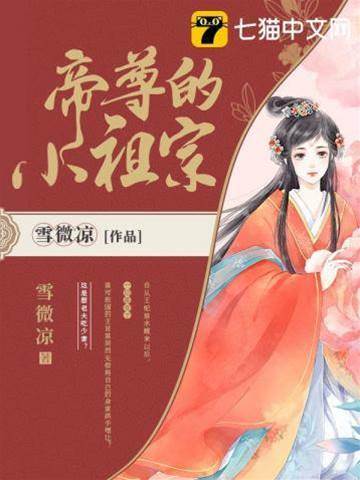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157 章

農家惡婦
何娇杏貌若春花,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女,一把怪力,堪比耕牛。男人家眼馋她的多,有胆去碰的一个没有。 别家姑娘打从十四五岁就有人上门说亲,她单到十八才等来个媒人,说的是河对面程来喜家三儿子——程家兴。 程家兴在周围这片也是名人。 生得一副俊模样,结果好吃懒做,是个闲能上山打鸟下河摸鱼的乡下混混。
48.4萬字8 8137 -
連載636 章

此夜逢君
繼母要把她送給七十歲的變態老侯爺,蘇禾當夜就爬上了世子的床。一夜春宵,世子惦上了嬌軟嫵媚的小人兒。寵她、慣她,夜夜纏綿,但隻讓她當個小通房。突有一日,小蘇禾揣著他的崽兒跑了!他咬牙切齒地追遍天下,這才發現她身邊竟然有了別的男人……怎麽辦?當然是抓回來,跪著求她騎自己肩上啊。
116.3萬字8.18 22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